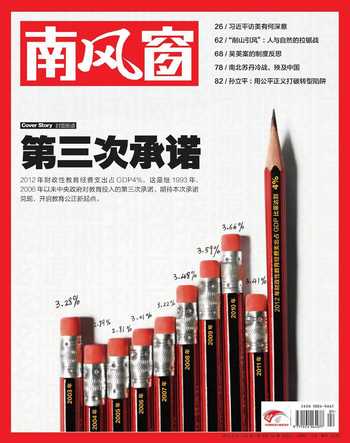9月的感伤注脚
刘怡
把麦克姆逊这本《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以及鲍勃·伍德沃德的《战时布什》放在一起比较是件有意思的事。《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这部半历史著作,为赖特赢得了2007年度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伍德沃德是“水门事件”的揭露者,以《战时布什》为起始的4部伍德沃德作品被认为忠实记录了小布什在“9·11”之后以单边主义姿态介入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而面对同一个已经被再三剖析的事件,麦克姆逊则选取了一个更加私人的角度,这也是此书题名中“个人回忆录”一词的由来。
“一个时代的终结”(Generation's End),更准确的译法是“一代人的终结”,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绪:当两极对抗的历史情境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消亡土崩瓦解之后,整整一代美国人在心理上进入了“准无政治状态”。经济上的攫取让位于“分配”,围绕这种分配勾画出全球化的蓝图;而伴随“敌人”在现实乃至概念中的消解,战争和对抗不复存在,政治变得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了。因此,尽管麦克姆逊本人在“9·11”之前已经为《纽约时报》采写和评论了10几年外交事务,倒也能坦承他对国际政治毫无概念。于是,当敌人、死亡以及战争的阴影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猛然“从天而降”时,这一代人被震惊、恐惧和迷惘包围了。麦克姆逊不得不向前国务卿舒尔茨—一位参加过二战、属于“最伟大一代”的长者——寻求精神和智识上的指导,而当舒尔茨也开不出妙方时,这位个人回忆者盯着电视里正在重新描述“敌人”与“政治”概念的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万念俱灰。
麦克姆逊本人后来宣称,“一代人的终结”意味着婴儿潮一代曾经拥有过的美国中心地位、绝对安全和稳定权力结构的丧失,但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未免延伸得太快了。当一位作者用了其作品超过1/3的篇幅仔细刻画自己直接而零散、有时近于意识流的心理狀态时,我们是看不到“权力丧失”这样高端的主题的。只是在不情愿地、甚至半强迫地接受了政治的回归和战争状态的出现之后,这位毫无安全感且不知所措的个人回忆者才逐渐转入对“终结”的观察和分析。
这种分析,我们其实是最熟悉也最乐意听到的—“布什总统的野心”使美国朝着帝国主义方向发展,由于美国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它的权威及合法性受到了广泛质疑。当麦克姆逊为之供职的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德梅洛在巴格达遇刺后,这位个人回忆者终于觉得自己“想通了”—布什的战争和布什的政治都是邪恶的,但“好时光已经回不去了”。
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麦克姆逊认为布什和他的班底实在太坏,于是美国终于不能回到无政治状态的天上,只能忧郁地坐在尘世感叹一代人的终结。布热津斯基会在感叹之余提醒美国人把握机会,在新一波的“全球政治觉醒”中把握重新掌舵的主动;当然,也有人会把麦克姆逊的感叹信以为真,一边激扬文字盘点美国的战略失误,一边做起“彼可取而代之”的鸯梦。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同样是以记者身份勾勒“9·11”,赖特端出了指向一个必然性事件的历史脉络,伍德沃德拼合了一项政策产生和发生效用的过程,而在麦克姆逊的个人回忆录里,如果不是“只有一片虚空神秘之所”,剩下的也仅是2001年9月的一项感伤注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