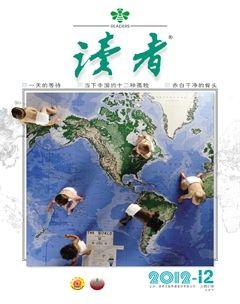意林
辨书记
柏杨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一本劣书,看来看去,能看得发疯。
《聊斋》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得道高僧,有一种辨识文学优劣的本领,他不是用眼看的,而是把文章烧成灰烬,用鼻子一嗅,就嗅出门道来啦。一位大作家,洋洋得意,把他的“流行性感冒”大作,火化給他嗅。该高僧不嗅则已,一嗅之后,就像有人在他鼻孔里灌了三斤芥末,先是打喷嚏,继而流鼻涕,接着牵肠动胃,大吐特吐,连肝脏都要吐出来,翻眼兼伸腿,性命攸关。
(艳波摘自《中外文摘》2012年第9期)
最后一个夜晚
柏邦妮
离开岛的最后一个傍晚,我走到海边,看见一个女生。她对我说:“彩虹!”我抬头一看,果然,在暴雨之后,天空出现了一小段四种颜色的彩虹。奇异的是,左边的天空是彩虹和蓝天,而右边的天空是落日和金云。它们共存于一个天空中。就像这个岛,存在着暴雨和晴天、富庶和贫穷、单调和丰富,如此种种。
这是旅行中最后的景象。
就像是我的人生。在极度的郁闷、挫折、黑暗、颓败之后,突然看见了极度的盛景。原来痛苦和美好、纠结和坦荡,都是共生共存的。
(未未摘自《青春美文》2012年第4期)
一旦上路,别有洞天
史铁生
别想把一切都弄清楚后,再去走路。比如路上有很多障碍,将其清理到你能走过去就好,无须全部清除干净。
鲁莽者要学会思考,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目的可求完美,举步之际则无须周全。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每一个答案都包含更多疑问;走路也如是,一步之后方见更多条路。更多条路,只能选择一条,又是不可能把每条都看清后再决定走哪一条。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过程重于目的。
当然,目的不可没有,但真正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而完善,唯可于过程中求得。
(生如夏花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4月10日)
送别
胡洪侠
要走了,父亲母亲送我到胡同口,还要往前送。我说:“你们回去吧,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父亲说:“走吧走吧。记着写信回来。”父亲停下了。母亲独自继续往前走。
自行车走出老远了,我回头,见母亲还在往前走。
我知道从此真的是出远门了:母亲送你有多远,你前面的路就有多远。
(如夏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照记@1963》一书)
同 胞
晚年的刘伯承拒看战争片,他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我就是从大堆大堆我们的兄弟、父老、亲人的尸体上爬过来的,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变 脸
刘 原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
(江欣摘自《南都周刊》,图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男人与女人》一书,〔阿根廷〕季 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