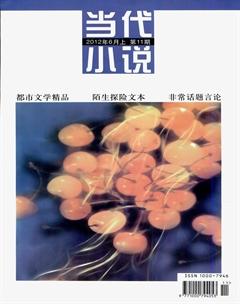外号
李玉刚
我叫炭核(读hu),他叫窑渣,是一对好兄弟,同属炭不完全燃烧物。因为我们经常到一家工厂门外的废物堆上捡炭核、窑渣,弄得满脸漆黑,村里人就给我们起了这么个外号,直到上学,我们才想起自己的名字。上学后,我俩依旧是“炭核”、“窑渣”地叫——顺溜。我们俩这么叫,别的同学也跟着叫,叫着叫着,我们又把名字忘了。
忘了就忘了吧,反正都是个代号,况且班里的同学都是有外号,没人在乎。
后来,我接父亲的班参加了工作,“炭核”就很少有人叫了。他依旧上学,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见了面,我们还是“炭核”、“窑渣”地叫,有时候还各上各的脸上摸一把,再叫,特亲切。
可巧了,他大学毕业竟然分到了我的单位,而且还分到一个车间一个班,我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炭核”、“窑渣”地叫上了,把同事叫得一愣一愣的,从此,我们就公开了外号。
大学生进步快,只两年,他就成了班长,我的直接领导。他当班长后,大家改了称呼,叫他班长。可他对大家说,都是兄弟,还是叫他“窑渣”吧。话是这么说,可是大家还是改了。我呢,两难,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了,叫他班长,好像疏远了,叫他窑渣吧,又感觉眼里没有他。我找到他,说,以后我不能叫你“窑渣”了,他嘿嘿一笑,说,你个炭核,怎么也变得这么俗了?
后来,“窑渣”逐渐被大家忘记了,而我的外号却叫开了。他还是无所顾忌叫我“炭核”,有时候还有意无意地批评我,让我叫他“窑渣”,可是我怎么也叫不出口。
又是两年时间,他成了车间主任。他成了车间主任,我就有了想法,虽然我的文凭低,可我也干了这么多年了,想弄个班长干干。我找到他,给他送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可以考虑,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叫他一声“窑渣”。我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有叫出来。他说不叫他“窑渣”,就不让我当这个班长。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叫我的外号,我不叫他的外号这不公平。我费了吃奶的劲,把原来叫得流水一样的“窑渣”两字从嘴里挤出来,不知是福是祸地回家了。回家后,老婆问我事情办的怎么样,我照实说了,老婆骂我脑子进水了,他让叫“窑渣”你就叫啊?
不过,在他的照顾下,我还真就当上了班长。从此,我心里坚定了一个信念,今后再也不叫他“窑渣”了。他还是叫我“炭核”,叫得我心里暖暖的。我当了班长没像他一样,别人依然叫我“炭核”,只是后面加上了职务——“炭核班长”,叫得我心里很别扭。
又两年时间,他提成了副厂长,我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只是偶尔到车间检查的时候,见到我会叫着我的外号问这问那,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后来老婆让我找他,想弄个车间主任什么的。我去了他家,见到他后,他叫我“炭核”,又让我叫他“窑渣”,结果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叫出来,被他批评了一顿,当车间主任的事也就黄了。
他的官越当越大,后来竟然成了县长。
他当了县长后,他的外号不知被谁挖掘出来,大家私下里都叫他“窑渣”县长,我的嘴也开了窍,谈起他来眉飞色舞,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光荣。不过我没有进步,依旧是“炭核”班长。我找过他,想让他关照一下,可是他每次都让我叫他“窑渣”,我实在是叫不出口,所以我再没能得到他的关照。我开始恨他,朋友之间说起他,我也是—脸的气愤,说他官大了,忘记了朋友,变心了,认钱不认人了。后来,关于他的传言越来越多,有说他黑脸包公的,有说他是黑心狼的,有说他收黑钱的。反正他就一个“特点”——黑!谁让他是“窑渣”呢?
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远,一年也见不了几回面,就是见了,我也是躲得远远的。有时候我想鼓足勇气,再见了他后叫他一声“窑渣”,管他高兴不高兴的。可是每次见了他被别人前呼后拥的样子,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心里的那点底气被击得粉碎。后来,也不想了,实在回避不了,见了面,还是身不由己地低三下四问候一声“县长好!”
时间像流水一样,转眼间,我们俩都退休了。知道他退休的消息后,我心里酸甜苦辣的,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同情,总之,心里不知道以后见了面叫什么好。反正这辈子他光叫我的外号,不公平。所以,我下定决心,决定今后再见了他也叫他“窑渣”,管他乐意不乐意呢。
这天,是他退休后他第一次没有人员陪同,自己轻车简从回老家转转。村里人还是把他当领导,一口一个县长地笑脸叫着。我听着就不怎么顺耳,在心里把他的外号重复练习着,准备脱口而出,还回这么多年他欠我的外号。
他依然那样,笑容可掬,见到我还是老样子,用手拍着我的肩膀,一口一个“炭核”地叫着。我憋红了脸,把几十年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还了他一下响雷般的称呼:“窑渣。”
我感觉到他的脸羞涩得像红云一样,手有些抖。突然,他伸开双臂,紧紧地抱着我,也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用他厚重的声音说,“你个‘炭核!”
我感觉到他眼里流出滚热的泪,打在我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