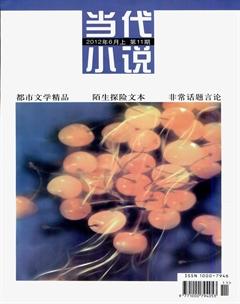博爱
邹洪英
辛茹有个儿子,儿子是三代单传,单传的儿子十八岁,十八岁的儿子读大一,读大一的儿子为了制止一次同学间的殴斗而被误伤身亡。
辛茹在整理儿子的床铺,她在儿子的枕头上发现一根寸长的短发,捡起来,捧在手心里,泪簌簌地流……辛茹的脚下踩了棉花包,身子晃了晃,跌坐在床上,手摸摸索索地掏出手机,哀痛像雾一样层层包裹了她,使她每日都习惯使然地拨打这个号码。尽管电话里由开始的“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再到后来“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这些她都充耳不闻,只要她按下键,她就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辛茹把手机贴着耳朵,头微微歪着,眼睛眯起来,开始了认真的谛听。过了一会儿,她的嘴蠕动起来,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嘿,这小子,又得了好多奖……“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校园十佳”……什么?歌咏还得了二等奖。就我儿那破嗓子还能拿个二等奖……还记学分(母亲神情流露出满足和欣慰,抬起手抹一把泪),1000米赛一等奖……还有两个奖项让给了别的同学,给别人一次机会……好!我儿子又长大了……儿子,你要照顾好自己,你是妈妈的最爱,你是妈妈的牵挂……
辛茹不由得站起身来,左手不经意地在床边的书桌上划拉了一下,她的手碰到一个硬硬的物件——儿子的照片,儿子正粲然地向她笑着,她的身子猛地抽了一下,手机落在地上,她伸手拿起照片,放到嘴边,哆哆嗦嗦的唇轻舔儿子的前额……她的喉咙像被钢钳卡住了,伤心、愤怒、惊惶、憎恨综合了这位单身妈妈的心。她的心被一块通红的烙铁烙焦了,想也没想,转过身“刷——!”的一声,把床单撕开,咬破手指,在撕下的床单上写道: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辛茹只有妹妹陪着,不见其他人。妹妹劝姐:“人死了不能复活,咱多要求些赔偿款,宽宽心。”辛茹的目光坚定,声音铿锵:“赔偿款一百万也不要,凶手必须枪毙!”
开庭了,辛茹抓起那个用血写下的条幅,要去法院。打开门,一位白发苍苍、面色灰黄的老奶奶扑通跪在她的面前,挡住她的去路。巨大的悲恸让这位老人失去了用语言表述自己的能力,哀求的眼里涌出两行浊泪……那双常年劳作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举起擦掉脸上的眼泪。
辛茹怔住了——你是谁?这是干什么?
老奶奶嗓子眼里发出颤颤的音:“饶了……我孙子吧,他才……十八岁。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我的命根子。我是……靠拣破烂儿……把他拉扯大……”
辛茹的身子开始抖动,条幅跌落在地上,人也跌落在地上。她用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汩汩地流,整个人都在颤栗。
“杀人犯”这个词原本应该距离她的孙子很远很远,可她的孙子,居然无所顾忌地选择了它。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留下一道灰色的尾巴,准备消失在天边了。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啮噬着这位老人的心?!此时,那个老奶奶的孙子仿佛就站在辛茹的面前,辛茹想对那个大男孩吼:你在做那些混蛋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那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奶奶,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吗?
作为一位母亲,辛茹无法漠视这位老人的眼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她无法形容,只感觉那眼神灼伤了她,使她心疼,她的心脏狂暴地企图挣脱胸肌的束缚,冲破宽阔坚硬的肋骨。她的双手按着胸口,抓着衣襟,她的脑海翻腾,翻腾。忽然间,有一种东西在心里涌动——就是把那个男孩枪毙了,我的儿子能活回来吗?我就不痛苦了吗?那个男孩死了,不又给他的亲人带来痛苦和灾难吗?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条生路,给自己留下自由……
辛茹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望着这位老奶奶,过了很久很久,她站起身来,向外走去,步履蹒跚地走上大街。天气很晴朗,阳光很明媚,街上很热闹,城市很繁华。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径直走进法院。走到法官面前,冲着法官凄然一笑,她说:我要撤诉。
法官紧锁眉头,盯着辛茹,辛茹一头白发,一袭黑衣。法官说:你再考虑考虑,要想好了。辛茹咬了咬嘴唇:我要撤诉。
法官站起身来,立正,双手拿起诉状,递给辛茹,然后向辛茹深深地鞠了个躬。
辛茹接过诉状,辛茹再笑笑,转身走出法院。
在儿子的碑前,辛茹点燃了诉状……那一缕青烟袅袅升起时,辛茹隐隐听到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