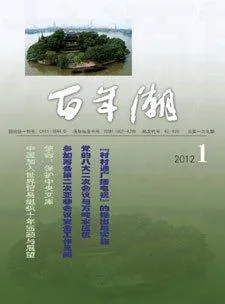革命曲折路 艰苦堪称奇



中央红军长征本为二万五千里,然而我因中途负伤离队,后随四方面军进入河西走廊,故多走了五千里。事非经过不知难,三万里长征路让我艰辛备尝,尤其是负伤离队和西路军这两段,更是九死一生,永远不能忘怀。
过草地负伤离队
1908年,我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贫农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书便中途辍学,当了7年多的裁缝。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兴国县委派人到我们老家一带秘密宣传革命,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下半年,我借当裁缝的便利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第二年加入共产党。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曾组织和领导过农民暴动,担任过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师政委、瑞金县委书记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李维汉决定让我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一路上我和邓小平轮流共骑一匹马,互相照顾。随后我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军从瑞金突围,途经广东南雄、湖南道县、广西全州等地,突破了粤、湘、桂军阀的围追堵截。我们工作部则一路打土豪、筹粮款,保证了大军的食宿。经过三个多月,我们终于到达贵州的遵义城。这之后,我又回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那时遵义有“红军之友社”,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学生。我们退出遵义时,许多男男女女跟我们走。我负责带队,给他们讲课。
我们在贵州转了三个月的圈子,和蒋介石部队周旋。1935年4月,我们从桐梓突围,直奔云南。到了云南,我们如入无人之境,纵横驰骋。后来因蒋介石部队大兵压境,红军又从四川迂回,渡过金沙江,飞越大渡河,到达四川西北地区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期间,我曾任干部团民运组长,该团政委是宋任穷,团长是陈赓。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合编成立了红军大学,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他领导下担任过地方工作组组长。
1935年六七月间,红军开始了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行军。当部队进入四川松潘毛儿盖草地时,不幸的日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左脚严重中毒。由于整天整晚不是工作便是行军,更可恨的是张国焘的反党反中央使我军行动更加紧张,这样一来,不到数天我的伤口大发作,不能行军,掉队了。
领导对我非常关怀,毛主席的马我骑过,刘少奇的马我也骑过不少次,王首道更是我的救命恩人。负伤后第一次难忘的遭遇,是有一天刘少奇叫我骑他的马走在前面,不料还未走二里路,就遇上敌人集中火力对我射击。幸亏只是牲口受伤,而我遇到了一位四方面军的战士,他将我背回了本队。
后来我的伤更加严重,有牲口也不能骑了,因此组织上给我一副担架。由于天天爬山涉水,脚夫不是这个跟不上,就是那个掉了队,四个脚夫只剩下两个,不是张三叫苦,便是李四叫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李维汉前来看过我一次。他说大夫对他说过,我的脚已经残废了,将来也不会走路了,没有长期休息,伤口不会好的。为了安全,组织上决定留我在老百姓家休息。后来李维汉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劝我好好休息,痊愈后去找陕北苏区,并寄大洋50元派蔡树藩同志送来。就这样,路过甘肃通渭时,组织上将我寄在了义岗镇娃子川陈得仓、陈珍仓的家里。
与组织失去联络的一年
留在甘肃通渭时,我的病情恶化了,全身瘦得只剩下几根骨头,胡子头发一样长,满身尽是虱子。安置我的同志对我说这家姓陈,因此我也改称姓陈,取名陈先桂,并拜陈得仓做父亲,组织上给我的50元大洋也全部交给了他。老农民见到钱非常高兴。不料,组织上将我安排到他家第七天的晚上,由义岗镇来了一个团丁,左手拿伞,右手提着马灯,到我的住房检查我。这位团丁似乎惊动了庄子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跑到我住房门口来,看我和这位团丁对话。这位团丁装模作样,脚刚踏到我房门口就问:“土匪”,你在红军干什么的,当什么官,哪里人,姓什么,伤口是什么枪、被谁打伤的?人们都瞪着两个眼珠子望着我。这时我躺在炕上,很难受,但还是强打精神应对。我说,我是红军后勤部当裁缝的工人,姓陈,江西人。我的伤口不是打仗受伤,是过草地中毒的。这位团丁说我胡说,并问我打算要死还是要活。我说死活随你的便吧,反正我病成这样,看你怎么办。他抬起头四周探望,结果拿走我一床红毯和一件毛线背心就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有来过。我想当地的老百姓说不定还能记得当时的情况。
我到娃子川陈家,一直同陈得仓夫妇一床睡。由于我伤口日渐恶化,到他家里约有两三个月之久都病得不能起床。接屎端尿、每天饮食全凭陈得仓的妻子和小孩们帮忙照顾。感动之下,我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都交给这位母亲,作为酬谢。
陈得仓是个中农,当时年约50岁,是个做木工的人。他有个弟弟叫陈珍仓。他兄弟俩上有母亲下有老婆和儿女,共十几口人吃饭,都是在家务农为生。这个庄子离通渭城60里,到义岗镇仅十来里,约十来户,都姓陈,都是忠厚善良的农民,没有一家是地主。他们都很拥护红军,经常将我军和国民党军对比,和甘肃马家军对比。他们看到红军路过甘肃公买公卖又不杀人,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好军队。这里群众条件很好,但治病的条件很差,没有钱也买不到药,不卫生让人吓得吐舌。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躺在床上让这位陈得仓摆弄。他用土办法,天天烧香,用艾叶灸、拔火罐,用尿洗伤口。
离开了部队,离开了亲人,一切都靠我这个孤苦伶仃的病人去和陌生人打交道。环境是陌生的,生活是艰苦的,病情是严重的,说话听不懂,风俗习惯差异很大,真是让人很痛苦。每当苦闷时,我总想着我家是贫农,我是工人,我无论如何是要革命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对我们有利。我还念着马克思说过的话,一个革命者,不但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我在这种困难环境下,该是自告奋勇去克服的时候了。就从这些基本道理出发,我克服困难,坚持养病,下决心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弄好关系。
真是谢天谢地,虽然终身成了残废,但在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久而久之我的伤口竟然逐渐好起来了(当然痊愈是在1936年八九月间)。大约到了1936年二三月间,我双手拄拐棍能去厕所大小便了。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下决心带病给娃子川百姓缝衣服度日。由于我会这门手艺,名声一下子传开了。为了把群众关系弄好,我在大多数人家做工都未拿过他们的工钱。不少周围百姓都派毛驴接我去缝衣,大约在娃子川缝衣服有一两个月之久,随后又到和娃子川相隔十里远的狮子川的张家和杨家河的杨家、王家等户缝了两三个月。因为我是红军寄下的南方人,再加上会缝衣服,所以在娃子川一带无形中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
大概是1936年春夏之交,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住在那儿消息不通,我和一个在通渭县读书的娃子川陈姓小学生交换条件,我替他缝了一套学生服,他替我要来一张《甘肃日报》。报载彭德怀率领陕北红军东渡黄河,占领山西临汾、洪洞等可喜的消息。我从这张报纸里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将报纸放在口袋里,每当苦闷时,总是偷偷地取出来看好几遍。
当我正在义岗镇王家替他女儿缝嫁妆时,我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路经此地,从此我就归队到红军三十一军了。我到军部时,遇到该军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他们告诉我说,路过杨家河、狮子川时,就有不少老百姓向他们反映娃子川有个缝衣的人是红军里的人,为此,他们曾找过我。
祁连山上打游击
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和我在江西万安、泰和一起工作过,彼此熟悉。他招待我吃了一餐饭,问了问我的情况,给了我一匹马,叫我和李聚奎在当天的头里走。我们走了不到几天,在一个夜里渡过了黄河,到了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就这样,我参加了西路军,调至政治部民运部工作。我积极请求恢复党籍,但因天天行军,直到1937年1月左右,在临泽县属的倪家营子战场上,经过西路军党委决定,恢复了我的党籍。经手人是张琴秋,时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西路军到了甘肃古浪、山丹、临泽、高台等地,遭遇到西北马步芳等部骑兵节节包围和严重的抵抗。我方死伤不少,残废伤号也天天加多。敌人还俘虏了我方不少的人。大约在1937年1月左右的一个晚上,马匪骑兵集中力量围攻我通向新疆要道的高台城驻军,董振堂率领的红军第五军团全军壮烈牺牲。
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加上严寒的气候、粮草的困难和饮水的缺少,艰苦程度和过雪山草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形势无法挽回的时候,西路军领导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委我为西路军直属残废营的政委。该营百来人,多是团、营、连的残废干部,也有个别当过师长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的喻杰当时在该营任教导员。
后来形势更加恶化了,上级决定主力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方向突围,而老弱病残一律留在祁连山上打游击,曾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就是当时在祁连山上的总领导人之一。当环境万分不利的时候,徐立清集合大家讲话,要我们化整为零,自由自愿地分散为小型队伍活动,当场每人发了不到一两重的大烟土。根据这个指示,我和喻杰重新调整了残废营,在自愿原则下重新组织了20人左右为一队。会议公推喻杰任队长,我为党支部书记。我们在祁连山上打了一个时期游击,做少数民族群众工作。这些民族很像是藏族,他们善良老实,从未和我们捣乱。
当马家军从四面向祁连山搜山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只能是突出敌人的包围。我们决定偷偷越过高台敌人的封锁线,经过内蒙古边境到我陕北根据地去。当天晚上,大多数人都顺利地渡过了黑河,到高台以东的东河岸来了。有一两个女同志,一个小同志,渡河后掉队了。我也差点掉队,因马失蹄,一家伙连人带马都滚到黑河的深水中去了。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手拉着牲口的尾巴才浮到河东岸,跟上队伍。当时气温大约在零下20度左右,皮帽皮衣、棉鞋棉裤全都浸得透湿,随即结成冰块,头发胡子也结成一串一串的白雪珠。光脚板走过河沿的砂子地,双脚冻得发紫,周身发抖。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条倒霉河,真冻得我好苦。喻杰等同志替我拾到几根柴禾烤烤,稍稍温暖了一下,大家又骑上饿瘦了的老马向内蒙古边沿沙漠地前进,找陕北根据地的希望可能实现了!
兵败被俘
天不遂人愿。当晚,高台城马步芳驻军就发觉了我们,马上派了一连骑兵追赶。在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两军相遇。敌人喊杀连天,刀光闪闪。在紧要关头,喻杰走在前头,取出自带的驳壳枪放了一梭子,带领我们突破了敌人这一次的包围。但我们整天整夜的行军,不但人饥饿疲乏到万分,就连靠着救命的牲口由于白天和夜里不停地行军得不到休息,也饿得大叫大嚷起来。我们这支队伍总共只有一两支破步枪,几发子弹,喻杰的那支驳壳枪子弹也打完了。我们陷在了弹尽、粮绝和人困马乏的沙漠里。马步芳的骑兵一直在我们屁股后头追赶,到第二天的上午又追上包围了我们。我们都被敌人俘虏了,当即被押送到高台县政府禁闭了一天。这大约是1937年3月左右。
被俘的当天晚上约12点左右,我们一个个睡得像死人一样时,突然来了两三个人,带着马灯叫我们集合站队,当场一个个地审问我们。我们事先互相商量过对付的办法,都一致回答是在后勤部休养的残废病号,也有个别的说是在后勤部当勤务的。当敌人问昨天谁打的枪时,喻杰说是因不慎枪走了火。第二天早上,敌人又让我们在县政府门口集合站队,送我们到张掖去。这时有个高台县的县长出来讲了几句话,主要说明送我们去张掖的理由。他还当场照例审问了我们一下,我们也按照前一天晚上说过的话答复了他。从高台到张掖大概花了三四天时间。我们这些人大多是残废病号,而我是当时残废比较严重的一个,不能徒步,挨过马家军士兵不少的打骂,到了实在无法走的时候,乘着老百姓的送粮大车,痛苦地到达张掖城。
到了张掖以后,我们被禁闭在喂骆驼的一个露天的大院子里,由民兵看守。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一批被俘虏的战士关在这里,加在一起约百来人,尽是些残废病号老老少少之类的人物。
我们在这个骆驼院子里住了15天左右,当刮风的时候,天上的雪花纷飞到我们身上。敌人只许我们每人每天喝两碗像水一样稀的小米粥。有些小青年饿得在地上滚。我也偷过老百姓喂牲口的马料充饥。饿到很厉害的时候,有张掖县的天主堂牧师前来施舍过两次,给了每人一个不到二两重的小麦面馍。牧师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向上帝祷告,在每个人的脸上画符。我们心里闷着笑。
我们到了张掖后,始终没有人检查和审问过我们。这是与国内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分不开的。这时候西安事变已经有好几个月时间了,国共内战基本停止了。我们时常听到一些马家军士兵和百姓说国共合作了,不打内战了,抗日了,你们的祖宗积德,南京有命令不杀你们了,等等。这些话我们半信半疑。在我们被俘之前,特别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杀过我们不少的人,但到了1937年二三月之后,没有听说过杀我们的人了。
辗转回延安
西路军几万人,除李先念率领几百人到达新疆以外,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只有极少数人化装逃回延安。比如,陈昌浩、徐向前在祁连山失败后,是化装成放羊的老百姓回到陕北的。李聚奎、朱良才也是化装讨饭回延安的。被俘虏的人,有一些经过中共中央交涉,先后送到延安,比如刘瑞龙、张琴秋、方强等同志,都是被俘后送回延安的。同我一起被俘的十几个人也先后回到了延安,当然具体方式各有不同。喻杰是被马家军动员去抬伤兵,回青海的路上逃回延安的。此外和我一起被俘,一起押在张掖县的程其兴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一机部工作,是和百来人一起由张掖送到兰州转送回延安的。我未听见和看见过马家军玩弄所谓自首叛变等鬼名堂。
当时,我们被关的地方常有一些马家军跑来找年轻小鬼当他们的勤务员,也有人来找我们的人去做工的,也有动员去抬他们的伤兵回青海的。后来,住的我们旁边的一位住家的马家军士兵,据说当过排长,请我去替他老婆缝衣服。因为我会这门手艺,在极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生活出路,和我一起被俘的同志都为我高兴,有些同志常跑进来向我要根火柴抽烟,有的向我要碗开水。过了大约三四天,一个晚上,我们的人跑进来告诉我说,他们明天一早就要整队集合,每个人各背15天的干粮,徒步押送到兰州去,问我去不去。听说这是南京的命令,要将我们解送到南京去。当时我的脚确实残废不能走路,故未跟他们一起走,仍留在这家缝衣。
缝了好几天衣服,我未得他一文钱,只请求他帮忙找到一家缝衣工厂。之后我就进这家工厂做工去了。这个厂子的招牌叫甘州东兴军服庄,就在张掖东大街,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叫乔东生私人开的厂子。这个厂子在张掖是手艺比较高明的,既能缝军衣,也能缝中衣、西服、便服,约有缝衣机七八架,工人一二十名。厂长乔东生,甘肃合州人,曾和杨仲贵师傅一块合作缝衣,后来他自己开办了这个厂子,聘请杨师傅当工头。杨师傅是四川人,思想很进步,天天都希望红军胜利,也很想跟我到陕北来。我临走时,他给过我路费。
由于西路军的失败,当时有不少我们的人流浪在河西走廊各个地方,特别在张掖更是充满街头,有的替人做工,有的挑担做小生意,也有的在街上讨饭度日。不少女同志当了别人的老婆,亦有些青年小鬼替马家军当勤务员的。谢觉哉的爱人王定国当时也在张掖。她在张掖天主教堂进步分子高院长那里住着,还来过我这家厂子缝过衣服,彼此见过面。我们的人告诉我说天主堂的高金城院长很进步,很同情我们。因此,我下工的时候常常偷偷地跑到他那里去活动。我同王定国就是在高院长家里第一次认识的。
考虑到甘肃河西一带有不少我们的干部流散在各地,高院长同情红军、共产党,表现十分进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就委托他设法输送我们的干部回延安来。当时谢觉哉同志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主持这项工作。王定国是在高院长那里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我也是通过高院长才到兰州办事处的。张掖很多人都知道这位高院长同情共产党。有一次我去找高院长,被乔东生发觉了,这位厂长连说带笑地说我是共产党,高院长也是共产党,宋庆龄、冯玉祥都是共产党,等等。由于高院长太红了,据谢觉哉后来告诉我,这位好人1938年2月不幸被敌人在一个夜里活埋了。1949年,我军解放张掖后,当地的人民为这位遇难烈士立了一块纪念碑。
大约是1937年九十月间,我离开工厂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王定国比我先走了几天,我后走几天,到了兰州办事处我们又见了面。当时朱良才在兰州办事处工作,他原先在红一方面军卫生部当过政委,后在西路军我们彼此认识。赴陕北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由朱良才当面交给我。朱良才找我谈了几句,委托我带着其他几位同志一同回延安。我们一行人由兰州办事处出发路经西安办事处,1937年冬胜利地回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从此结束了长征。我刚到延安的时候,就有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曾关切地问到我,“那个瑞金的县委书记来了吗?”1938年春毛主席到中央党校参加毕业典礼,我特意去毛主席住处看望。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长征是最难忘的一件大事。我曾赋诗一首,以志不忘,诗云:
长征史无前,吾行三万里;
革命曲折路,艰苦堪称奇。
挂彩留通渭,不意去河西;
国焘反中央,罪责难清洗。
山丹被敌困,枪炮加飞机;
浴血倪家营,高台苦战激。
撤退祁连山,冰雪无寒衣;
偷渡黑山河,落马险溺毙。
被俘落虎口,弹尽粮绝际;
患难同甘苦,喻杰在一起。
统战红旗展,绝路逢生机;
兰州遇谢老,败因深剖析。
辗转去延安,富春是上级;
走访王首道,难忘让马骑。
党校见罗迈,百感热泪起;
批判张国焘,上台言辞激。
感谢救命恩,晋见毛主席;
红军指战员,情谊多亲密。
往昔峥嵘事,代代莫忘记;
年老甘让贤,革命有后继。
民族大团结,四化齐努力;
中华得振兴,共同庆胜利。
(本文由胡嘉宾的子女,根据父亲1956年、1976年、1983年自传和1983年口述记录稿摘抄整理而成,有删节)
(责任编辑#8195;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