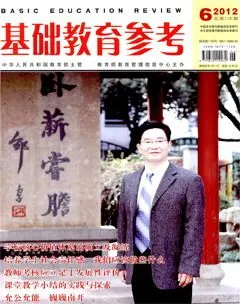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
这次北京师大附中以“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为中心议题的校长论坛召开得十分成功,众多校长都是基础教育界的“高手”。他们的发言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来中学教育生机勃勃的景象,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在大家的启发下,本人对基础教育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进行了一点思考,现将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创新人才培养”命题的历史演变
“创新人才培养”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命题,仅就我国近代史而言,康有为为了振兴中华,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大声疾呼:“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竭力强调培养“才智之民”的重要性。在当时,尽管不用“创新”二字,但被前人认定为的“才智之民”或“杰出人才”,都是做出了“前人未曾有,后人不可无”(顾炎武)事业的人,这不就是“创新”吗?这种人才,在西方国家往往称之为“天才”,他们对“天才”的培养和教育研究的历史,为期就更长远了。
那么,今天我国政府倡导培养创新人才,与历史上培养杰出人才的主张有何不同呢?简而言之,这一演变可以概括为,从培养少数学术性精英,到培养一大批杰出创新人才。
我国倡导培养“一大批杰出创新人才”,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其一,对“人”认识的科学有了飞速的发展。我国工程院韦钰院士多年来致力于脑、心智和教育交叉领域的研究,曾荣获国际大奖。近日来,她多次论及近三四十年间,对“人”认识的科学获得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脑科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以往人类历史研究成果的总和。脑科学的发展,有可能使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国际上对人才研究贡献卓著的有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始人加德纳。还有认知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等人。多元智能理论揭示一般人至少有八种智能,而且每个人的智能结构是独一无二的,连“同卵双胞胎”的智能结构都是不同的。这些智能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现象,甚至产生了所谓的“白痴学者”。新型的智能研究,有可能突破所谓天才儿童只占同龄人3%,5%的论断,各行各业都可以涌现创新人才,而不限于“学术精英”。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命题之前,加上“一大批”的要求,是有科学依据的。
其二,社会多元需求强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各行各业需要各色人才,而不仅仅需要学术性人才。恰恰新型的智能观认为判定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解决真实生活中个人所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创作或提供个人所属社会文化所看重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因此,学习成绩优异不应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唯一依据,而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才是现代杰出人才的重要特质,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多元创新人才的需要。
其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张扬个性、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来,人们都在谈论乔布斯的贡献,更加确信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乔布斯”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有不少人很不适应传统的、“制度化”学校的教育模式。这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培养创新人才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以上三方面的变化,令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人才”特质。从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看,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大多只是“潜人才”。例如,加德纳称之为“潜在的天才儿童”,这是有科学性的。由此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特长生”即“显人才”。实际上,未来的杰出创新人才未必是现在的特长生,现在的特长生也未必是未来的杰出创新人才。但是,这并不否定我们培养、呵护特长生。不过,应当认真考虑和研究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一是不同领域人才的成熟期(即具有公认特长的形成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音乐、体育等人才,可能早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可能成为特长生了,开设这类特长班当然很有意义。二是还应考虑创新人才的不同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探照灯式”的人才。比如钱学森先生就读北京师大附中时,兴趣就十分广泛,后来他曾多次更换研究的专业方向,而且表现都很出色,他就很像“探照灯式”的人才。北京师大附中另一位校友,大家熟知的于光远,也是多次转换研究方向的人才,似乎也属于“探照灯式”的人才。还有一种人才叫做“激光式”的人才,他们专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面,这种人大多属于我们常说的“偏才”,或者只在某方面表现出特别浓的兴趣、较少顾及其他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北京师大附中的校友张岱年先生,他在自传中曾写道:“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就看了许多哲学书籍,其中包括外文的哲学书,使我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人生和宇宙这样的大问题。”张先生27岁时就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奠定了他一生成为大师级人才的基石。
鉴于对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思考,似乎应当探讨两个相关的话题:一个是教育公平问题,一个是个性化教育问题。从政治经济、法律的角度说,教育公平具有均衡性,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但是,如果从教育的本真而言,教育面对的是有差异的、有不同个性的学生。因此,让具有不同智能结构和个性的人接受同一种教育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本质上则是最大的“不公平”。从教育的视角,我们追求的教育公平应当是使不同的学生接受“各得其所”的教育,即个性化的教育。这种教育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理想,使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关于如何发展学生的个性,根据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属于“潜人才”的特点,办实验班当然是可以的,但不是唯一的办法,而应把创新人才的培养融入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形式中去。近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在集体教育中发展个性”的策略,我认为,个性化的教育不一定都是个别化的教育。钱学森等杰出人才不都是在普通班级当中成长的吗?常规的普通班是个小社会,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化发展。这就是说,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杰出创新人才,不一定非办实验班不可,形式应当是多样的,班级授课制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补充和发展。
二、基于学校本位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三要素
在座的各位优秀校长所办学校大多为“幸福乐园”,极其丰富多彩。但是,凡事只有“简而易”。即“简约”才“易行”。面对培养创新人才出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校举措,我们似乎应当“聚焦”。而且,这种“丰富多彩”往往呈现出“同质性”,令人怀疑我们众多的优质学校已经出现了“高原现象”,需要有所突破。只有改变思维,我们才可能走出优质教育的“高原期”。就思维方法而言,应当倡导教育理性,回归教育本源。至于“基于学校本位”,那还需要破解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蔡晓东校长所说的、在高考指挥棒控制下培养创新人才的心理“纠结”,我们应当“聚焦”到在高考现行体制下,学校教育可行、而且必行的内容上来。据此,我试图集中阐述基于学校本位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三要素,即核心是人格,关键是教师,保障是教学。这三项内容是互相渗透的,是一个统一体的三个方面。
1.塑造健全人格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核心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斩钉截铁地指出:“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他是从科学史的视角高度评价了“人格”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在讨论创新人才培养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个性,似乎人格与个性有别。心理学界对人格的界定有很多说法,但是,严格意义的人格不等于人的伦理性,它可以包括个性,即“人格也称个性,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主体”。而且,人格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到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到一个人的能力道德,小到一个人的个性习惯,无所不包。——这就是刘沪校长倡导的“全人格教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个性寓于人格之中。全人格教育亦即个性化的教育,是创新人才赖以形成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此纪念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应当重温他成长的宝贵经验。钱老曾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但凡了解“血沃中华热土”和经历了共和国“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的人,都会为他的这番话动容!遗憾的是,我们的学生没有这样的经历,人格教育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志向。这就需要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世界的本质和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使他们的志向能够扎根于现时代。
2.教师的素养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
一是教师的境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吴颖民校长十分中肯地指出:“不敢拔尖的教师,定然培养不出拔尖的学生;缺乏创造性的教师,也难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学生。”清华附中的王殿军校长与之有同样的见解,他还进一步指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教师不会教和教不好。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什么样的教师足以担当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呢?这使我想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热爱是最好的导师,它永远超过责任心。”一般来说,一位老师有责任心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为何还不足以成为“导师”,还需要“热爱”呢?实践告诉人们,只有责任心的老师,他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循规蹈矩的,这虽然很好,但不一定有创造性。
那么,“热爱”又是什么呢?——热爱是一种境界。深厚的学养是它的根基,强烈的求知欲是它内在的动力,激情满怀的探索是它的外在表现。没有这种境界,是难以培养具有创新激情人才的。实践证明,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师需要有两个“热爱”:一是热爱学科知识;二是热爱学生。
老师只有发自内心地热爱所教学科知识,学科知识才能获得生命,使知识生活化,使哲理形象化。而只有“记问之学”的老师,课堂是“活”不起来的,学生是“乐”不起来的。仅仅能使学生“乐”是不够的,教师必须具有高屋建瓴的水平,能够抓住学科体系的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学科的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是具有领域性的)。具有这种境界的教师,都很重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例如,钱老曾回忆北京师大附中的数学老师,他说这位老师出五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
至于热爱学生,这更重要。对“导师”而言,他必须读懂每个学生。文学家冯骥才在《大度读人》中指出:“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读人比读其他文字写就的书更难。”读懂学生,“教”才能做到服务于学生的“学”,教育才能有实效。
二是教师队伍建设。在大力推行培养创新人才之际,几乎每所学校都在考虑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但是,基于学校本位的、最有效的教师队伍建设是什么呢?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因为,学生是教师最好的学校。只有拿到学生颁发的毕业证,教师的人生才算尘埃落定。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应当“以教人者教己”,这是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我们经常发现热爱学生的教师总是充满活力,甚至年老之后仍然“青春焕发”。这是由于贴近学生的教师将永葆“童心”,他们能够理解学生们拥有的、为成年人往往不具有的各种奇思妙想,也使自己成为一位呵护学生创新“基因”,即好奇心的良师益友。因此,北京四中的刘长铭校长常说:“名师是学生培养的!”
3.教学质量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保障
教学渗透在学校的一切活动之中,学生参与的任何学校活动都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主阵地当然是课堂教学。
优质学校不乏学养深厚的好教师。这些教师往往很会讲授。能够培养一大批崇拜自己的“粉丝”,学生虽然能够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但是无形之中却使灌输式教学长期占据课堂,学生的能力也难以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提高。优质学校特别是示范高中,应当着力将灌输式教学逐出课堂,把研究式教学引进课堂,努力探索和创建“轻负担、高质量的‘幸福课堂’”的教学模式,这是当务之急。
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对学生成长至关重要,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钱老在师大附中的学习情况,他说:“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他几乎每天中午吃了饭,就和同学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他不怕考试,也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对于这段启蒙教育,钱学森十分怀念,尽管他的成绩大多为80来分,却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发展,成功地使他由“潜人才”变成了杰出的“显人才”。减轻学生负担,使学生们获得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对培养创新人才是何等的重要!
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学习,对创新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来,我参与对一位七十九岁物理教师的经验总结。该教师培养了众多具有创造力的学生,这是因为她重视引导学生独立看书,让学生自行推导各种物理公式。学生回忆这种重新推导求证公式的过程使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当年发明这个公式的物理学家。从而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创造的愉悦。学生们还感到“学了物理就好像多了一双透视眼”,能够过滤出纷繁复杂生活现象“背后的物理意义”。这就使学生摆脱了强记知识的烦恼,进入了把握学科思维方法的境界,轻松而且更深刻地理解了知识,拥有了驾驭知识的能力。这无疑说明,探究式的教学模式足以将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在同一过程中解决!这位教师从不搞什么题海战术,使学生学习轻松而愉快。学生们则往往以研究的心态对待高考,破解难题的能力很强,致使物理高考的成绩一直位居前茅。
探究式的教学模式,能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上述这位教师培养的一位学生,近日写了一段高考纪实,他说:“高考场上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试卷很快就答完了,仔细检查后还有时间,于是就推敲起一道大题,发现该命题本身不够严密,在常规之外应该还有一个答案完全符合命题要求,尽管常识提醒我高考的答案应当具有唯一性,但我的自信心却支持我果断地把第二个答案也写到了试卷上,注明了我的分析,并声明两个答案如果有一个错了甘愿判我全错。当时的感觉就像大将军上了战场,只为真理而战。后果虽不得而知,不过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好一个“只为真理而战”!这不仅是科学的求真精神,也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节操和创新的胆识。显然,专注于引导学生押题、揣摩考官心理的“应试教育”,是造就不出这种人格健全的创新人才的。
钱老曾回忆,当时学生考试也不是提前要做大量准备的,完全就看平时的准备跟记忆,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反而容易让同学们瞧不起。诚如刘沪校长所言:“高考的优异成绩。应当是全人格教育的自然发展和必然结果。”
总之,新型教学模式追求的是“轻负担、高质量”,是知识与能力的统一、人文与科学相结合。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