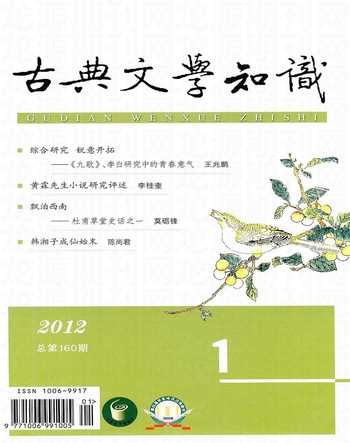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
王德华
《文选》卷四五“对问”类收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设论”类收录了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及班固《答宾戏》三篇。将《文选》“对问”、“设论”二体放在一起讨论,是基于二体的文体特征与价值具有三个方面相同性的考虑。其一,《文选》分称的“对问”、“设论”,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合称为“对问”。《文心雕龙·杂文》言: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数《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以上一段引文可以看出,刘勰“对问”体范围的界定与《文选》不同。刘勰将“对问”体溯源至宋玉《对楚王问》,并述其流,由此可见“对问”体是唐前文士经常创作的体类。刘勰所说的“对问”,从他提到的作品来看,实际上包含《文选》“对问”及“设论”两类。刘勰之所以将《文选》中的“设论”并人“对问”,盖因无论“对问”还是“设论”皆具有对答形式;另外,“对问”和“设论”具有共同的“发愤以表志”的创作心理背景以及“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态”的情感表达模式。若按此,屈原的《卜居》与《渔父》完全可以纳入“对问”体之中。可以说,刘勰所说的“对问”(为了称述方便,下文依刘勰所言,“对问”体包含了《文选》“对问”、“设论”两类)体实萌生于屈原,发展于宋玉,兴盛于两汉魏晋,是文人士大夫理想与现实对峙之时或政治边缘化之际抒发情志的重要载体。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其二,“对问”体具有赋体的文体特征,可以看作是赋体的特殊体类。刘勰将“对问”体与七体、连珠合称“杂文”,后人从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刘勰以篇名定体的局限,因对问、七体与连珠具有赋体的文体特征,如采用赋体托物言志与假象尽辞的表达方式、对答体形式以及韵散结合的语言句式,学界时而将这三类作品视作赋体,如周振甫云:“《杂文》讲了对问、七、连珠三种,实际上这三种都是辞赋。”(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对问”体赋具有了解创作主体情感与人生经历的史料价值。清刘熙载《艺概·赋概》言:“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人列传,所以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就《史记》、《汉书》来看,除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创作的散体大赋史书多有录载外,《文选》所收及刘勰所言“对问”体创作(包括萧统、刘勰未提到的屈原《渔父》)史书也多有收载,因而,刘熙载所言也揭示了“对问”体赋所具有的了解作者其人的史料价值。
就“对问”体创作的情感表达模式来看,刘勰所说的“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揭示了对问体创作主体的“身挫”、“时屯”的现实处境以及“凭乎道胜”、“寄于情泰”的自救解脱的途径。《文选》“对问”仅选的一篇宋玉《对楚王问》,刘勰认为“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是宋玉处于“负俗”之时,运用对问这种形式,“以申其志”之作。宋玉用曲高和寡作喻,又以凤凰与蕃篱之鹦、鲲鹏与尺泽之鲵再比,形象地说明了自己难为众人所理解的高行志节。全文托物言志,假象尽辞,表达了世俗与自己的人生境界的高下之别。如果说宋玉《高唐》、《神女》等赋确实因微讽而使其表现出“终莫敢直谏”的性格特点,那么宋玉《对楚王问》,面对楚王的质疑和世俗的“不誉”,仍能“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其“曲高和寡”的比喻,充分表现了宋玉“负俗”处境下孤高个性与对自我精神的持守,仍不失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的特立独行的风范。
屈宋“对问”体赋揭示的创作主体与政治权力中心疏离状态下对自我精神的持守与孤高的个性,在两汉以后却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处于怀才不遇情境下,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创作主体在持有一份精神自守的同时,更多地流露出一种精神上的自嘲与自解。这一变化始于东方朔的《答客难》。东方朔在未仕之前对自己才华高度自信,《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载:
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日:“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虑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此段东方朔所言,严可均《全汉文》卷二五题作《上书自荐》,可以看作是东方朔的自荐信。此封上书写于东方朔二十二岁时,即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东方朔生年有异说,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东方朔生”条]。书中不仅叙述了自己十三岁至十九岁时的博览群书的经历,对自己的外在相貌作了近似完美的自我画像,还交代了自己勇捷的能力与廉洁的品行,字里行间鼓荡着战国策士恃才傲物、舍我其谁、立取卿相之气。《汉书》本传载“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这种恃才干主的自信,在汉武帝即位之初,确实令武帝另眼相看,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奉禄薄,未得省见”。东方朔稍得亲近武帝之后,在武帝身旁常以诙谐直谏著称。如其劝谏汉武帝建造上林苑,陈言有三个罪状可问斩馆陶公主的男宠董偃等,故本传称其“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但是武帝一世,好大喜功,颇重实绩与实事,东方朔只能在汉武帝身边“诙啁”即戏谑逗乐而已,“不得大官”。战国时的立谈卿相之事,在武帝一代化为泡影。《汉书》本传载东方朔《答客难》创作背景云: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喻。从中可见,东方朔对自己与枚皋类似俳优的身份颇为不满,也试图有所改变。他的“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以及“言专商鞅、韩非之语”,并没有被采纳,主要是因东方朔“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的自我推许,以及“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的言语方式,所以“朔、(枚)皋不根持
论,上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恃才干主而“终不见用”,“用位卑以自慰喻”,这应是他创作《答客难》时的处境与心境。由此,《答客难》表达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东方朔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战国时代的策士有着相同之处,即是对功名的追求,因而《答客难》开篇借客之口诘问东方朔为何不能取得当世功名,正是东方朔自身求取功名而不得的内心愤懑的一种表达:
客难东方朔日:“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要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客所讲述的东方朔好学乐道、智能海内无双但“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的落差,也正是东方朔恃才“欲求试用”而“终不见用”现实反差的反映。客之诘问,其实正是东方朔一生汲汲以求而始终未能实现的,因而,所谓“设客难己”,无疑是借客之口,吐露了东方朔对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始终未能实现的牢骚与不平。
二是针对客“意者尚有遗行邪”的诘问,东方朔从“时异事异”的角度对当今立功之难的解释,包含着对一统政治压抑人才的批判,同时也表现了士人对一统专制虽有批判但却无奈接受的现实: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日:“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自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糜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日时异事异。”
以上回答,从“时异事异”的角度反映了东方朔对自己政治悲剧的清醒认识。从“时异”的角度来看,“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的战国时代已不复存在,自己所处的是“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的高度集权的时代。相应地,从“事异”上看,士已从战国时代的政治权力中心退居边缘,成为集权的工具,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才能的表现,完全取决于主上之好恶。故在东方朔看来,“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充分反映了统一时代,士作为社会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不自主性,这也是才高位卑的主要原因。所以马积高先生言:“作者之意,或者只在为自己的官卑辩护和抒发不受重用的哀愤,然而在客观上却深刻地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文士处境的差异,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任皇帝随意摆布的悲哀命运。”(《赋史》)而东方朔“时异事异”的解释,同时也包含对一统政治无奈接受的现实。东方朔对这种政治悲剧的思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人士大夫驰说政坛立取卿相时代的结束,也揭开了文士在中央集权之下政治悲剧的序幕。
其三,东方朔不仅借与客的对问,揭露了文士身处集权下的政治现实,同时还表明了修身自荣的自处之道。这种自处是一种儒家穷达出处之道,也是一种自慰自胜之道。东方朔针对客“意者尚有遗行邪”的疑问,批评了将功名未就与“遗行”即道德修养问题相互牵扯的看法。一方面指出君子“苟能修身,何患不荣”,认识到修身对君子获取功名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了理想的实现最终依赖于环境,即对当今处士修身不荣的外在环境的强调:“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这既是对宋玉曲高和寡解释的承继,同时因其对外在客观环境的强调,而多了一份精神上的自解自慰与自嘲,少了一份清高与孤傲。
东方朔之后,随着时代与社会思潮的变迁,文人士子用以自解自慰的思想武器时或不同,但是在创作主体与社会的碰撞与冲突中,凸现怀才不遇的牢骚与忧愤,展现创作主体自胜自救之道,则成了“对问”体创作的共同模式。如《汉书·杨雄传》载杨雄《解嘲》创作背景云: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创作《答宾戏》背景云:
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史书所载扬雄、班固“对问”体创作的缘由,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即“对问”体已成为创作主体处于政治边缘化时,表达自我内心情志与对社会看法的一种文学载体。只不过东方朔之后,由于两汉儒学的强化,“对问”体在揭示创作主体与现实对峙情形之后,在强调生不逢时的同时,主体的道德自慰与淡泊自守更加突出。如扬雄《解嘲》认为“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完全以世易时移的观点,从外部环境给自己找到淡泊自守的依据。班固的《答宾戏》,宾戏之词沿袭《解嘲》,嘲讽主人空以著述为业,不能建功立业,取名当世。主人的回答却是重在有感东方朔、扬雄生不逢时、世易时移的自嘲,从两个方面阐明了对功名的看法。首先是对战国时代李斯、韩非、吕不韦等人取当世功名的认识,班固一改东方朔、扬雄生不逢时的看法,从李斯等人“皆蹑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的先荣后枯的政治变故,认为战国时李斯等人追求的虚名伪功,非君子之法,孔孟不取,并批评宾戏之词是“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觌”不合时宜的观点。接着班固列举了“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的代表,立功者如傅说、姜子牙等;立言者如陆贾、董仲舒等;立德者如伯夷、孔子等,并认为这都是“王道之纲”与“圣哲之常”的表现。在班固看来,人生的价值在于修身、自守与体道,而不在于追求虚名,这就从东方朔、扬雄生不逢时的自嘲转向了坚定自我人生追求的心灵“自通”。当然,班固的“自通”也是建立在才高位卑处境下的一种思想上的超越,《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创作《宾戏》以“自通”的原因之一,就是“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即对才高位卑的不满。《文选》所载班固《答宾戏》创作背景(本自《汉书叙传》)与《后汉书》本传有异: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
《后汉书》本传所言已见上录,相较之下,两处所言同异有三:一,本传言“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流露出才术与名位不当的愤懑与牢骚,其愤世嫉俗的创作心理与东方朔、扬雄一致。《文选》只说“或讥以无功”,但“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描述,却冲淡了本传序愤世嫉俗的创作心理。二,二者皆言及有感东方朔、扬雄“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的论述,表明班固《宾戏》创作受到二人的影响,对二人的论述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三,本传只是简单地论及班固“作《宾戏》以自通焉”,而《文选》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班固的立场和观点,即“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两序同中有异,各有侧重,合而观之,能更加明确地了解班固创作《宾戏》的前因、所感及主要观点。可以说,班固的《宾戏》,也是出于对立功不成的不满,但篇中更多了对立言立德的崇尚,高扬了三不朽中的立德与立言的社会价值,使得立德立言不是作为立功失败后的心灵安慰,而是作为一种现世的价值存在而成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
我们可以看到,从东方朔到班固,两汉士人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即从东方朔最初的生不逢时的哀叹,到扬雄的抱玄自守,再到班固对以儒学立德立功的推崇与自守,文人士子在与政治的关合与疏离中,完成了由外在立功的挫败感而对现实进行嘲讽式的批判向以立德立言求得精神自胜自解的转换。两汉以后的“对问”体创作,大都未超离这一情感主题与表达模式。可见,古人三不朽的观念,虽然是太上立德,立德为先,而实际生活中却是注重事功。对于以道德自守或不善钻营的士大夫来说,“立功”往往成为一种奢望,总会导致立功无望下转向以立德或立言来排解内心的抑郁不平并以此得到精神上的自救。
可以说,《文选》所录“对问”、“设论”创作,运用主客对答形式,充分展现了士大夫对“立功”的渴望以及政治边缘化之后以立德立言自解的精神历程,表现出“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的复杂的情感状态。至于表现这种情感的话语方式、表现手法及讽世嫉俗的语体风格,我们将在下篇中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