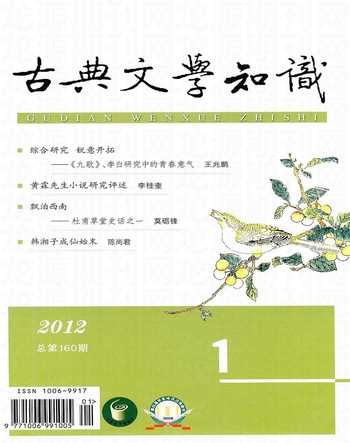陌上花开缓缓归
苏扬剑
熙宁六年(1073),苏轼年近不惑,任杭州通判已期年。钱塘自古繁华,比起十六年后顶着“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的官衔出任杭州知州来说,此時身为知州副手的苏轼“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作诗纪行。
《陌上花》为苏轼在临安提点時作,小序曰:“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日:c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临安是吴越王遗迹所在,九仙山,在临安县西,曾是葛洪、许迈炼丹之地。苏轼有《宿九仙山》一诗赞此间仙境堪比桃源,游山時闻乡里小儿唱歌谣,可能是因为用吴语歌唱,子瞻是外乡人听不太懂,觉得歌词鄙野就重新为之填词,另有记载此为“清平调”歌词。现在已无法闻得当時婉转动人的曲调,但是仅从“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句便能感知浓郁的相思之情。歌谣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吴越王妃每年寒食节都要回临安省亲,有一年直至春色将老、陌上花发,王妃还没有归来,吴越王钱鏐很是思念,便寄信呼唤王妃早日归来,信中的其他内容早已消散,唯有这九个字含蓄委婉,饱含深情,随時间沉淀留存下来。这里有对美的赞叹,还有在急景流年中心灵敏感的悸动,面对良辰美景、如花美眷而发自内心的怜爱。春天是一个生命力躁动勃发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开遍陇头陌上的鲜花,给心灵带来微妙的触动,枭雄如钱鏐者亦不能免。清代王士稹评价道:“二语艳称千古。”(《带经堂诗话》卷九)这种“艳”绝不是苏子所言的“鄙野”,是言辞的娓娓道来中感情的浓墨重彩。苏轼重新填词,把握住了情感的焦点。苏子游九仙山時正值农历八月,花开繁盛蝴蝶飞舞,借诗咏怀感慨钱鏐一世英豪,成就吴越王国,传国百年后终归降于宋。江山仍在物是人非,读此诗如闻其歌,使人凄然。生前的荣华富贵,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风流云散”(王粲《赠蔡子笃》);死后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边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晋书?张翰传》),一切尘世的虚名浮利都逃不过時间,远不如丈夫想念妻子酿成的一句话,反而流芳百世。
冷冰冰的史书中的吴越王钱鏐是一个“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旧五代史》卷一三三)的侠士,一个不受伪命、忠于朝廷的将领,一个穷奢豪享、妄自称王的狂人。传说钱鏐衣锦还乡時,尽造华屋、锦衣覆蔽,苏轼《锦溪》诗云:“楚人休笑沐猴冠,越俗徒夸翁子贤。五百年间异人出,尽将锦绣裹山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如今钱鏐大张旗鼓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却令其父避之不及并告诫说:“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而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苏子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多难,何尝不想宦途腾达、光耀门楣,无论多么蛮荒偏远的流放地,他都克己尽忠、不畏权奸为民请命,可惜终究“飘渺孤鸿影”而“有恨无人省”(《卜算子》)。
钱鏐出身贫寒,虽勇猛善战,但是读书不多。《全唐诗》卷八其小传云:“好吟咏,通图纬学,喜作正书。”载诗二篇: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
家山乡眷兮会時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读之颇有刘邦还乡作《大风歌》的豪情壮志。《湘山野录》记载当時父老不解此歌,王复以吴音歌云:“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依心子里。”虽不知是否确有雅风两版,但是改为俗语后多少有点苏轼所“鄙野”的味道,不过欢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遂为“狂童游女”传唱至今。
另一篇就更奇特了,名曰《没了期歌》,有一军士在公署的墙上题“没了期,没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管事者怒向武肃王禀报,王不仅不怒反而续诗云:
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须将一片地,付与有心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传语龙王并水府,钱塘借与筑钱城。
吴越王当朝時,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军中有怨发泄于壁,不料被王得知,“没了期”三句是钱鏐对军士的戏言,营造之事如春去冬来般正常,不必抱怨没完没了;后六句则是钱鏐忧国忧民的心声,人才难得,他知人善任,发掘出了贤人如高彦、罗隐,后者時为钱鏐参佐,好讥讽,与王唱和敢戏言钱鏐未发迹時“骑牛操挺之事,谬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旧五代史》);钱塘江海潮泛滥,钱谬建起“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旧五代史》)。王士稹又说:“武肃王目不知书,然其寄夫人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制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五代時列国,以文雅称者无如南唐、西蜀,非吴越所及,赖此一条,足以解嘲。”(《带经堂诗话》卷九)相比《全唐诗》著录的二篇诗作而言,便知神韵派王渔洋对“陌上花开”句的如此高评并不为过。
苏轼对武肃王似心存一份惺惺相惜之情。熙宁十年十月戊子(二十六日),杭州知州赵抃请求朝廷为吴越国王钱鏐建表忠观,早已离开杭州改知徐州的苏轼作《表忠观碑》,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栾。岁時归休,以燕父老。……
一气呵成,读来酣畅淋漓,吴越王之忠勇尽得彰显。吴子良谓只“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四句,“便见钱鏐忠勇英烈之气,闪烁乾坤”(《林下偶谈》卷三)。《表忠观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上。明代王世贞从书法角度跋曰:“《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人《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铭词是苏诗之佳者。”(《弁州四部稿》卷一三六)“罗池”指苏轼另一幅石刻真迹《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代表了苏子书法艺术的两种风格。
婉润可爱的还有前文所述的《陌上花》。“‘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并不佳,而音节夷宕可爱。东坡‘陌上花开蝴蝶飞即此派也”(施补华《岘慵说诗》)。苏子“不经意”地作诗成就了此类诗的清新可人,余音袅袅。苏轼另有《江城子》也用“陌上花”的故事,“……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词前序云:“陈直方妾嵇,钱塘人也。丐新词为作此。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余尝作数绝以纪其事矣。”可知《江城子》词作于《陌上花》三绝句之后,且不仅九仙山里人传唱“陌上花”歌谣,钱塘地区可谓人尽皆唱。《青泥莲花记》卷七记载“子瞻因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可惜,陈直
方的缓缓曲只能对着新冢而唱,唤不回阴阳相隔的妻子。
苏轼以前,使用“陌上花”一词的诗作不多,然自苏轼作《陌上花》三首绝句后,其妙笔一挥忽如一夜春风,吹得“陌上花”开遍诗坛,和作不断。其学生晁补之连和八首,小序云“事见苏先生诗”。前四首云:
郊外金瓶步帐随,道边游女看王妃。内官走马传书报,陌上花开缓缓归。
朝云暮雨山头宅,暖日睛风陌上花。绛幕何妨行缓缓,送春归尽妾还家。
娘子歌传乐府悲,当年陌上看芳菲。曼声更缓何妨缓,莫似东风火急归。
荆王梦罢已春归,陌上花随暮雨飞。却唤江船人不识,杜秋红泪满罗衣。
(《鸡肋集》卷第二十)
晁补之诗文词俱佳,尤乐府诗备受历代文士赏识,和苏诗文颇多。组诗围绕王妃归省的主题,反复吟咏,游女恋乡思君的矛盾心情缓缓铺叙于笔端,王士稹赞日:“工妙不减苏轼之作,勘称双绝。”(《香祖笔记》卷十二)“二公诗皆绝唱,人乐府即《小秦王调》也。”(《带经堂诗话》卷九)
宋人王庭珪《题罗畴老家明妃辞汉图》云:“陌上花开大堤暖,细雨春风归缓缓。宁从禁御落风沙,长路漫漫碧云断。”(《两宋名贤小集》卷一九五《庐溪逸稿》)明妃一去不返,飘零孤寂真如陌上花一般随风逝去,不知归期。此处的“陌上花”与钱鏐盼王妃归来本事无关,运用在另一位王妃身上,更添凄苦哀婉。类似的借花咏史的还有金代赵秉文的《杨妃墓》:“灼灼陌上花,青青路傍草。人心任荣悴,过眼无丑好。马嵬三尺坟,西出剑门道。……”(《滏水集》卷第六)。元代方回有“……钱王陌上花犹好,苏小门前柳未残。革故鼎新谁料得,举安天下胜偏安。”将陌上花、门前柳等自然景物融入到熙宁年间新政的政治背景中,让人不禁怀想改革中苏轼等志士的经历遭遇(《用夹谷子括吴山晚眺韵十首》其七,《桐江续集》卷二十一)。南宋遗民诗人谢翱不仅评价苏轼《表忠观碑》,自己也有《吴越王妃归朝》组诗,其二云:“宴罢朝辞生局促,诏赐离宫作汤沐。先王蒸尝泽有差,上恩许歌陌上花。”其诗前小序:“妃以开宝九年三月随王入朝”(《唏发集》卷一),开宝年已入赵宋,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俶当朝,也是吴越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君王,此“吴越王妃”非彼“吴越王妃”,谢翱所吟钱鏐孙钱俶纳土归宋事,“上恩许歌陌上花”透露出降服者哀伤的心态,如今的“陌上花”不再有曾经先祖歌咏時的心安,而是一丝对故国、已逝家园的祭奠。
至此,可发现苏子笔下的“陌上花”酿化成为一种特定的意向,指向游子的内心,表达一份归来兮的愿望或者是欲归而不得的怅惘抑或是归去来兮的自问,如:
忆昔东坡老,曾吟陌上花。我今归故里,卉木正光华。(宋?姜特立《归乡》,《梅山续稿》卷十五)
鸣鸠肯停唤,谁测阴晴验。欲问陌上花,花枝无绝艳。(宋?董嗣杲《雨饮无肴》,《庐山集》卷二)
笔者按:苏轼吟唱“陌上花”時未至黄州,尚无东坡之号,但是苏子的盛名似乎“剥夺”了钱鏐的原创权。吴越王写信時值暮春,花期已至,姜特立“归乡”時“卉木正光华”,一派欣欣向荣,烘托诗人激动的心情。董嗣杲在雨日独酌,寂寥难耐,身边似无“卷帘人”,“欲问陌上花”,却发现花枝头连花也凋零,不再依旧。
万古声名供敝帚,九州意气付浮查。同来蓬沓于潜女,一笑长歌陌上花。(宋?洪咨夔《还自益昌道得张伯修诗次韵》,《平斋文集》卷第三)
路旁柳如此,陌上花依然。数年束强项。一日舒联拳。(略)(宋?洪咨夔《山行纪事》,小序云:“至节后两日,侍老人访岳林精舍,晚过真君观,小饮还宿澄维那房,厥明登九仙山,晚取道陌上花里而归。”)
笔者按:洪咨夔两首气势磅礴,满纸老当益壮、伏枥千里而壮志未酬的感慨,陌上花于豪迈的情怀之中更显婀娜、衬托英雄心中的柔情。后首称此里名为“陌上花里”,苏诗中未明言,不知此名盛于钱铿还是苏子?
清人诗歌继承多开创少,在读史、读前人诗作的同時将题材、素材重复吟唱,咏史意味浓厚。如李兆洛《吴越王衣锦还乡图》诗云:“芒砀歌风亦有台,酒酣清泪欲沾衣。何如陌上花开日,一曲春风缓缓归。”(《养一斋集》诗集卷二)汪由敦《表忠观》诗云:“陌上花开缓缓归,歌声已断昔人非。青萍无复村农荐,芳草空留羽士悲。”(《松泉集》诗集卷二)有趣的是清代大藏书家劳格的《访宋钱氏书藏歌》,劳格家中藏书丰富,自题藏书室名“丹铅精舍”,为清代著名藏书楼之一,本诗大约是劳格收到一种钱氏宋本,兴致而发所题。全诗七言三十二句,述眉山东坡及吴越王钱鏐的故事:“情迁事往移心神,陌上花开又晚春。善本流传何可见,铁券玉册问渔人。”“书城墨妙已千古,韵事今犹播艺林。”(《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八)。可谓化古典入新题。清代女诗人辈出,不让须眉。常熟闺塾师归懋仪,与著名女诗人席佩兰为闺中畏友,其《钱塘弩》盛赞武素王之英勇如滚滚江涛:“陌上花开春复春,钿车零落埋香尘。至今江口寒潮急,犹似当年射弩声。”(《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八十六)气壮山河又细腻温婉。胶州才女柯劭慧是近代著名学者柯劭忞的妹妹,其《拟古》“朝采陌上花,夕玩庭中月。赏心亦何常,遇物即迁别”(《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八十九),超凡脱俗。
苏子曾云:“诗要须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吴越王吟咏“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创造了一个文学素材,经过苏轼的改编,化俗为雅,成就了一代文学经典。苏子作诗用典不拘来历,歌谣亦能人诗,曾经的“下里巴人”经其提点化身“邻家罗敷”为众所知,否则这朵曼妙的“陌上花”可能会寂寞地独自绽放。“陌上花”成为后代骚人墨客的文学典故,意象重塑而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