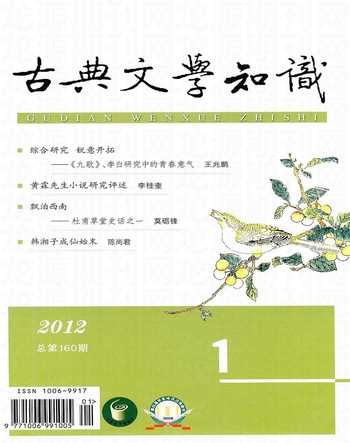南社巨子高旭的曲折人生
樊庆彦
南社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自始至终与当时的革命斗争有密切关系,它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斗争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南社成员中,高旭(1877-1925)作为与柳亚子、陈去病并驾齐驱的三位发起人之一,其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而他的人生道路同样最为曲折。
青少年时期(1877-1904)
高旭,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等。1877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日)未时诞生于江苏省金山县张堰镇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幼而丧母,由其父高炜养大。高旭“生而歧嶷,七岁就傅”,“敏而好学,晨夕攻读,自经史词章,以及百家诸子,罔不参稽博考”(高鏐《高天梅先生行述》),旧学基础极为深厚,以能诗名噪乡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翌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年轻的高旭义愤填膺,感受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作《咏史诗》百篇以抒怀。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又给了高旭极大的鼓舞,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开始由单纯的爱国热情转而倾向于维新,呼吁“驱策同向庄严涂,激起黄民热血濡”(《自题诗魂》)。虽然维新变法仅仅经历了百日的辉煌,但康梁则被当作救世英雄,成为万众瞩目、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欢迎。高旭更是对率领众举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膜拜有加,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1900年唐才常、林圭、秦力山领导的自立军武汉起事还未发动便被清朝当局血腥镇压的事实,使高旭深受刺激,悲痛万分,写有“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口发愿建新邦”之句,对六君子和唐才常深悼的同时,也感受到在中国维新的艰难,曾经想去遁世,学过一段佛,自改名慧云,也写过一些禅理诗,抒发心中的忧闷,“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但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援佛入儒的进取哲学思想的影响,和他本身即以“政治家兼哲学家”自期的愿望,反倒使他把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佛学的“无我”思想统一起来,从而更加积极入世,关注社会。随着梁启超在海外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以后,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仍积极在维新派的舆论主阵地上为之摇旗呐喊,渴望“文明运启兮日当中,扼腕发愤兮思大同”(《唤国魂》)。但秦力山事败“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黄中黄译《孙逸仙》),康有为的形象开始在高旭的心目中黯淡下来。
甲午战争后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和反,洋教等斗争继续发展,但随着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联合清剿下遭到失败,高旭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明朗,在与友人顾九烟的唱和诗中借“咏梅”抒发自己的反清意向。1903年是中国思想界转变的关键年头。此时的维新派已经变质为忠实的保皇派,成为阻碍革命进展的绊脚石。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失败后,爱国志士们在革命党人极具感染力的爱国革命宣传下,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更加清醒,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出保皇党以人革命党者,不可以千数计”(《民报》第五期)。高旭更加认识到,单单依靠打着维新旗号的康梁保皇派是无法挽救国家的,他的立场开始转变,与康梁划清了界限:“君自为君我为我,不相菲薄不相师。”(《读(南海政见书>》)逐渐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11月,他与叔父高燮、弟高增等在家乡张堰镇创办了《觉民》月刊,自任主编。“大声疾呼,思改新中国”,号召全国人民都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苟有热血人,安忍坐视祖国之沦亡而不为援手,使重见天日耶!”(《(觉民)发刊词》)而且在这个刊物中,高旭开始发表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的诗歌,可以说是他思想的又一进步。
而清廷经过庚子事变的浩劫,被迫实行“新政”,对舆论控制相对松动,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迅速活跃起来,大量爱国团体和进步报刊借机蓬勃发展起来。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林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它与属下的爱国学社、《苏报》三位一体,很快构成了上海革命宣传的中心,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加入革命。“苏报案”后,中国教育会虽形困顿,但其余绪相沿,仍有可观者在,报刊中《警钟日报》和《中国白话报》最值得重视,两者都是鲜明的革命刊物,这对高旭有着极大的诱惑。1904年初,他频繁地赴上海,经常出入《警钟日报》社,和陈去病、刘师培、林獬等论交,参与撰文。他把康梁维新派讥之为“进退失据空彷徨”的奴隶,声称要“仗义逐胡虏,正气壮山河”,呼吁要“洗旧腥膻”、“建新国”。他又接触到王夫之的《黄书》、刘师培的《攘书》、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章士钊的《孙逸仙》等书,为之题诗,鼓吹民族革命,明确地形成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
同盟会和健行公学时期(1904-1907)
20世纪初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也推动了出国留学的热潮。高旭正是受这一潮流的影响,于1904年秋,东渡日本留学。而当时的东京,已是我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外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心。高旭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开始系统学习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对西方思想了解较深的人,思想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单纯的华夷之辨,进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他提倡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也要吸收外来文化,以促进果实之变化(《学术沿革之概论》)。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把中国问题,放在整个东方和世界的范围中去观察、理解、考虑、反应,触及到了近代中国问题的实质,由此对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产生的怒火也更强烈,呼唤反抗也更猛烈。这是高旭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优势,也是后来南社其他成员所未能做到的。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横滨,立即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其间高旭也前去谒见,与孙中山、宋教仁等谈排满之策,令高旭非常兴奋。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邀集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华侨代表70多人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高旭参加并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为会员。8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高旭被推举为江苏省分会长,专司本省留学界之人会事务。此时,高旭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成为了一个纯正的革命党人。为配合革命活动,1905年9月,高旭在东京创办了《醒狮》月刊,以为业已休刊的《觉民》和《江苏》之继,撰稿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宣传家,所刊作品篇篇充满强烈的革命思想。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之前,《醒狮》可以说是最具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个刊物。年
末,东京留学界掀起大风潮,为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取缔清留学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全体罢课,继而停学,最后全体归国。高旭也在年末回到上海。
1906年初,同盟会因蔡元培准备出国留学,党务不能有所进展,遂合上海、江苏二分会为一,派高旭为分会长。为安顿留日归国学生,高旭与各省归国学生代表一起创办了中国公学。1906年春天,在上海西门宁康里另行组建健行公学,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1905年柳亚子曾在家乡吴江同里组织学生自治会,创刊油印的《复报》周刊。此时,柳亚子趁机将《复报》与同里自治会均移至健行公学。将同里自治会改称青年自治会,推高旭为会长。改《复报》周刊为月刊,改油印为铅印。由高旭函托田桐在日本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高旭、田桐、柳亚子一同参加编辑工作。因与《醒狮》栏目相近,“出版后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期)。高旭遂将《醒狮》停刊,专一发行《复报》。《复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相呼应,成为“《民报》的小卫星”(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而当时东京出版的其他革命刊物如《洞庭波》、《鹃声》、《寒帜》等,也都以健行公学为聚散地。半年之中,健行公学成为上海革命气氛最浓的学校,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
在健行公学的后面,有其教员夏昕渠的一所住宅,榜其门日“夏寓”,实为同盟会江苏支部的秘密机关。上海地区的许多革命会议,都是由高旭在这里主持召开的。自1906年秋起,健行公学、“夏寓”、《复报》都逐渐受到清政府的注意。10月,柳亚子避回黎里,陈陶遗复东渡日本。1907年1月,因叛徒出卖,高旭被指名查捕。“月明分外终成夜,花放无多又被风”(《四鼓未寝,忧从中来,披衣挑灯,写成一律》),不得已,高旭忍痛关闭“夏寓”,解散公学,隐居家乡金山,暂避矰缴。不久又创办了钦明女校,与妻子何亚希同任教职。但当时的健行公学已经为后来的南社聚集起了重要的力量。后来南社成立后,健行公学的大部分教师成为其主要组成人员。
南社筹备和成立初期(1907-1911)
高旭避居家乡韬光养晦期间,或与柳亚子函寄诗词唱和,或赴上海与老友相聚,以遣忧怀。1907年4月清明节,他与陈去病等5人游览苏州虎丘,凭吊明末抗清将领张国维祠,不仅涌生重振几、复余绪之志,诗酒流连,三日而返,成《吴门纪游》,这成为后来南社在虎丘张国维祠成立的先兆。
同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牺牲,陈去病拟于沪为之召开追悼会,未成,计议组织神交社。29日,他在《神州日报》上刊出《神交社雅集小启》,公开发出倡议,宣布立社,对一直禁止文人结社的清政府发出了挑战。而且参加这次集会的18个人,后来差不多都入了南社,可看作是南社的预备会。对于这次雅集,高旭和柳亚子是热情支持的。虽然8月15日的成立会他们二人均没有参加,但都著文作诗以和之。柳亚子后来认为,高旭诗中“说道‘几复风流赖总持,是已经走上发起南社的道路了”(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
1908年1月5日,刘师培、何震夫妇由日本回沪,由陈去病出面,邀之与高旭、柳亚子、沈道非相聚。又七日,陈去病再邀刘氏夫妇与高旭、柳亚子等11人在国华楼小酌。席上有结社之约,即名南社。此后高旭便利用他办健行公学时建立的联系,积极与人联络,相约共同“支撑东南文史局”。但2月25日,陈去病因有秋社之结,而为清廷注意,只得远走汕头。他在5月《有怀刘三、钝剑、安如并念西狩、无畏》中还说高旭:“其二有渐离,生来耻帝秦。报仇志不遂,往往多哀呻。要我结南社,谓可张一军。”年底陈去病回沪后又生腿疾,直到第二年6月才愈,在苏州为张氏西席,高旭又驰函相问讯,有结南社之请。1909年9月7日,回国被捕的陈陶遗出狱,往访柳亚子,二人相偕往访时已迁居留溪的高旭。“三人相见,狂喜大醉,痛饮三日。以相聚之难,相约以神交社雅集的方式,发起南社雅集于陈去病之所在苏州,并一访张东阳祠,以重振当年几社、复社之余绪”。“留溪别后,即分头行动并通知所联系的社员”(郭长海编撰《高旭集·高旭年谱》)。9月28日(农历中秋),其间高旭曾于上海邀周祥骏,杭州邀邹天一入社,并赋诗日:“南社从此添健将,匣中宝剑气纵横。”
大概因为高旭在当时是同盟会的领导人,与陈去病和柳亚子相比,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而且当时发起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作犄角的”(柳亚子《南社纪略·新南社的始末》),南社是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而成立的。1909年10月17日,高旭首先在《民吁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南社启》,宣称“欲唤起国魂”乃“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要求“同情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肯定了明亡后复社诸人在东南倡义抗清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了他们醉心科举、标榜门户的恶习,表示要“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这是南社的第一号公告。因此,蒋慎吾在《南社纪念会之史的回溯》中认为:“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南社所发的《南社启》”,“右项宣言有高氏署名,分明是他个人的口气。”故他亦将高旭列于首位:“原来,南社系高旭、陈去病、柳亚子三氏发起。”(柳亚子《南社纪略·附录》)而柳亚子认为:“天梅杜门家居,一隐三年,不免静极思动。我们三个书呆子(指陈、高、柳三人),函牍往来,诗词倡和,酝酿复酝酿,动荡复动荡,直到一九。九年,南社的名词,便以我们三个人的努力,正式出现于世界。”(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诸种事实表明,高旭在南社成立过程中应有首倡之功。11月13日,南社成员齐集17人,又外来宾张采甄、张季龙叔侄二人,仿照复社旧例,沿着前年高旭等人吴门之游的路线,出阊门,乘舟山塘,拜五人墓,游虎丘,于张东阳祠雅集,饮酒赋诗,会后,刻有《吴门游草》,南社这一革命的文学团体遂告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神交社的成立和南社的成立,高旭都没有参加。他当时声名很大,是苏沪地区革命党领导人,健行公学的创办人,罗致党人,无虑百数。“清廷震恐,隐若敌国,大吏承旨,屡被名捕”(高鏐《高天梅先生行述》),处在清廷的严密监视之下。秋瑾事件之后,“缇骑四出何披猖”,“瓜蔓子抄酷若何”,他只能“杜门凄绝落叶黄”,“避世空山寻薜萝”(《悲秋四章》),无法参加神交社的雅集,自是情理中的事。后来高旭也曾向柳亚子剖白心迹:“君真知我应能谅,事有难言且闭门。”(《寄汉碧》)而虎丘雅集时又传言说有危险,且高旭实因儿子生病由不得己,“败人佳兴豚儿病”,也只得“杜门避矰缴不来”,“待我明春虎阜游”(《和哲夫<重九)见怀韵》)。为兑现他的承诺,1910年秋(重阳),高旭携妻子何亚希,并约叔父高燮、友人蔡哲夫等人到南京共作白门之游,抒发故国之思,并将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革命情绪,一一形诸诗词之中,显示出高旭思想的更加激进、成熟。
辛亥革命时期(1911-1925)
武昌起义爆发后,高旭在家中闻之万分欣喜:“日吉早时论北伐,
便应一战决戎华”,“跃马挥戈竞何意?埋胡紫塞慰天心”(《闻武汉义军起,喜集钱蒙叟<投笔集>句,得十章》)。同时在《天铎报》上公开指出:“最足为共和新中国之梗者,实袁世凯也。”(《擒贼先擒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高旭备受鼓舞,作《元旦》诗以贺,并为孙中山献上《进步歌》。但由革命造成的发皇气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这年春天,高旭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6月16日,他又被选为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部长。这年底,他又与孙中山会面,并即席赋诗三首呈之。高旭感到大展抱负的时刻已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思想家自居。次年3月,同其他议员一道,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但“新朝甲子旧神州”,“失笑衣冠尽沐猴”(《元旦》)。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称帝登基。气愤之余,高旭离京南下。此时他又重温旧课,以参禅来求得心灵的平静:“闭户参禅心不动,中原豺虎任纵横。”(《次韵,答陈匪石》)“读破《楞严》静闭门,只求无怨亦无恩。”(《钝根函询近状,并告方为亡友宁太一辑武昌狱中诗,仍以题辞见示,次韵奉和》)
1916年,高旭二次进京,以图有所抱负。但此时南社内部因思想艺术分歧,加之组织松散,也是内讧连连。高旭经过与柳亚子两度失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环境中,高旭的思想又随之发生了变化,与其早期的激进思想截然不同,开始怀疑南社的战斗作用,对于文坛上的各种派别也都表示了宽容谅解的态度,逐渐向清朝遗老靠拢,成为一个两面人物:一方面,与南社旧友诗酒唱和,另一方面,却又和当时名声很坏的艳体诗人易顺鼎品伶唱和,撰写“金粉文字”,甚至结交当时革命派痛斥的同光体诗人郑孝胥,“又为凄咽清苦之音”(高鏐《高天梅先生行述》)。对于北洋军阀政府,他也并非毫无认识,但又恋栈其中。不过此时的国会两院也只是个摆设之物,高旭再次受挫。终于,国会两院又被北洋军阀解散了事,高旭无奈只得再次离京。
1917年、1918年和1921年,高旭曾三度南下广州。此时南方局势与北方无甚区别,亦是战乱频仍,军阀各自为政。在北京时期受晚清遗老的思想诱导,使他更加向往歌舞升平的环境,过分追求安定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消极,导致他早期受到的佛学消极避世、清静无为的思想影响再度萌发,促使了其思想上乃至生活上的消极,“不如去做糟丘长,大厦原非一木支”。这个时期个人生活与境遇上亦不十分得意,“杨君咽冰、孙君仲瑛、蔡君哲夫均任秘书之职,而陈君佩忍新自汕头来,亦任参院秘书”,看到自己的朋友都有了发挥个人才能之处,自己出来之时,也曾抱有“安得长剑依崆峒,扫尽豺狼四海一”的雄心,可是壮志难酬,依然自衣一袭,未免有长铗之叹,他有了“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的投闲置散的感觉。
1922年6月,黎元洪复任总统,9月,高旭又赴京。此时的高旭经过闭门家居的反思,思想有所转变。先后发表短评、论评百余篇,监督批评北洋政府。1923年夏,直系军阀曹锟的野心已经日益显露,高旭又随一些议员南下离京。但9月参众两院开会,高旭却又进京出席。10月,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五千元的高价贿买议员五百余人。名单被人揭发,公诸报端,人称“猪榜”,受贿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高旭等19名南社重要成员赫然在列。大江南北,舆论大哗,南社声誉由此受到很大损害。柳亚子立即驰电相责高旭:“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廿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名南社旧友在《民国日报》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指责高旭等19人“贿选祸国,辱及南社,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并望社中同志随时随地“发表同一之态度,为中华民国稍留正气”。天下戟指以向,高旭也无法安其心,只得蛰居北京以避人见。
高旭由南社发起人一举而成为南社的罪人。1923年5月,柳亚子等发起新南社,陈去病、朱少屏、马君武等南社旧友纷纷加入,而高旭已不予其列。高旭与南社的关系也宣告结束。1924年5月1日,高旭从弟、高燮长子高圭在《新黎里》上对高旭等19人再次予以抨击。1924年冬,高旭抱病南归,返回金山。他“性本好饮,至是,益颓然自放。每酒酣耳热,抚今吊古,长歌当哭,夜以继日”。他对其子说:“此生终不能俟河之清,亦欲求千日之醉耳!”(高鏐《高天梅先生行述》)归里不到一年,即在“日夕痛饮”中,于1925年旧历七月初七之夕,悒郁而终,年仅49岁。南社同人胡石予挽之日:“死有传书成学早,生逢乱世惜君深。”郑逸梅认为此联:“寓贬意于哀悼中,甚为得体。”(郑逸梅:《南社丛谈》)
高旭的一生,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常有的历程。如孙中山所说:这些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是一个“极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舍身任事者三四百人,“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孙中山《致陈楚楠函》)。他们“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带有类似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资产阶级伟人时所指出的某些时代特征:视野开阔,热情奔放,勇于行动,无论参加革命、脱离革命或反对革命,都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为捍卫自己的旗帜而斗争。虽然他们由于民族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能从中产生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也还缺少“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但是,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相比,和他们的上代人相比,他们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性格方面已开始表现出崭新的特征。他们是新的一代。
诚然,高旭处于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社会思潮波推浪涌,朝晴夕雨,其间人物,往往变幻莫测。兰成萧艾,荃蕙化茅,诸如此类的事,屡见不鲜。但他们的缺点与错误,挫折与失败,乃至他们后来所走的不同道路,甚至他们对自己当初理想的背叛,等等,都无法掩盖他们在这一伟大时代中所闪射出的夺目光辉。因此,1929年,陈去病重新发表《高柳两君子传》,加按语说:“两君为吾江苏革命先进,诚实忠肯,眼中罕觏,虽计虑出处时或不同,而略迹原心,不无可谅。顾皆不获于时,侘傺以老,此可谓伤心痛哭而弗能己已也。”(《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五期)对高旭来说,这大概是比较公允的盖棺之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