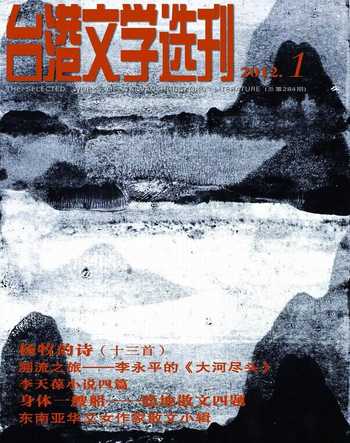罗愁绮恨话南洋
王德威(美国)
马华文学的发展从来是华语语系文学的异数。尽管客观环境有种种不利因素,时至今日,也已经形成开枝散叶的局面。不论是定居大马或是移民海外,马华作家钻研各样题材,营造独特风格,颇能与其他华语语境——台湾、大陆、香港、美加华人社群等——的创作一别苗头。以小说为例,我们谈在台湾的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在大马的潘雨桐、小黑、梁放或是游走海外的黎紫书时,几乎可以立刻想到这些作家各自的特色。
在这样广义的马华文学的范畴里,李天葆占据了一个微妙的位置。李天葆一九六九年出生于吉隆坡,十七岁开始创作。早在九十年代他就已崭露头角,赢得马华文学界一系列重要奖项。这时的李天葆不过二十来岁,但是下笔老练细致,而且古意盎然。像《州府人物连环志》状写殖民时期南洋州府(吉隆坡)华埠的浮世风情,惟妙惟肖,就曾引起极多好评。以后他再接再厉,完全沉浸于由文字所塑造的仿古世界里。这个世界秾艳绮丽,带有淡淡颓废色彩;只要看看他部分作品的标题,像《绛桃换荔红》、《桃红刺青》、《十艳忆檀郎》之《绮罗香》、之《绛帐海棠春》、之《猫儿端凳美人坐》就可以思过半矣。甚至他的博客都名为《紫猫梦桃百花亭》。
李天葆同辈的作家多半勇于创新,而且对马华的历史处境念兹在兹;黄锦树、黎紫书莫不如此。甚至稍早一辈的作家像李永平、张贵兴也都对身份、文化的多重性有相当自觉。李天葆的文字却有意避开这些当下、切身的题材。他转而堆砌罗愁绮恨,描摹歌声魅影。“我不大写现在,只是我呼吸的是当下的空气,眼前浮现的是早已沉淀的金尘金影——要写的,已写的,都暂时在这里作个备忘。”他俨然是个不可救药的“骸骨迷恋者”。
但我以为正是因为李天葆如此“不可救药”,他的写作观才让我们好奇。有了他的纷红骇绿,当代马华创作版图才更显得错综复杂。但李天葆的叙事只能让读者发思古之幽情么?或是他有意无意透露了马华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极端征兆?新作《绮罗香》可以作为我们切入问题的焦点。
李天葆的古典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古典。从时空上来说,大约以他出生的六十年代末的吉隆坡为坐标,各往前后延伸一二十年。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这其实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时期。但在李天葆的眼里,一切却有了恍若隔世的氛围。
那是怎么样的年月?吴莺音、姚莉、潘秀琼的歌声荡漾在老去的乐园巷里,街头“电懋”、“邵氏”公司电影海报上的李丽华、葛兰任凭风吹雨打,永远巧笑盼兮。马六甲海峡的暖风一路吹上半岛,午后的日头炎炎,哪家留声机传来的粤曲,混着此起彼落的麻将声、印度小贩半调子的惠州官话叫卖声、串烤沙爹和羊肉咖哩的味道……唐山加南洋,一切时空错位,但一切又仿佛天长地久,永远的异国里的中国情调。
李天葆要讲的故事也并不那么古典。老去的脱衣舞娘回首前尘往事,当年色香俱全,现在形销骨立;落魄的女厨师身怀绝技,却死于非命;女老千带着儿子一站又一站地吹捧骗;小姨子和死了老婆的姐夫间道是无情却有情……李天葆的故事恒常以女性为重心,这些女子有的遇人不淑,有的贪恋虚荣。他们的伧俗凉薄的身世和李天葆泥金重彩式的风格于是产生奇异的不协调。
李天葆的文笔细腻繁复,当然让我们想到张爱玲。这些年来他也的确甩不开“南洋张爱玲”的包袱。如果张腔标记在于文字意象的参差对照、华丽加苍凉,李的书写也许庶几近之。但仔细读来,我们发觉李天葆(和他的人物)缺乏张的眼界和历练,也因此少了张的尖诮和警醒。然而这可能才是李天葆的本色。他描写一种捉襟见肘的华丽、不过如此的苍凉,仿佛暗示吉隆坡到底不比上海或是香港,远离了《传奇》的发祥地,再动人的传奇也不那么传奇了。他在文字上的刻意求工,反而提醒了我们他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时空和语境上的差距。如此,作为“南洋的”张派私淑者,李天葆已经不自觉地显露了他的离散位置。
归根究底,李天葆并不像张爱玲,反而像是影响了张爱玲的那些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隔代遗传。《玉梨魂》、《美人泪》、《芙蓉雨》、《孽冤镜》、《雪鸿泪史》,甚至上至《海上花列传》。这些小说的作者诉说俚俗男女的贪痴嗔怨,无可如何的啼笑因缘,感伤之余,不免有了物伤其类的自怜。所谓才子落魄,佳人蒙尘,这才对上了李天葆的胃口。他新书卷首语谓之《绮罗风尘芳香和圣母声光》:“凡是陋室里皆是明娟,落在尘埃无不是奇花,背景总得是险恶江湖闯荡出一片笙歌柔靡,几近原始的柳巷芳草纵然粗俗,也带三分痴情。”诚哉斯言。
张爱玲受教于鸳蝴传统,却“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庸俗反当代”。李天葆没有这样的野心。他沉浸在吉隆坡半新不旧的华人社会氛围里,难以自拔。他“但求沉醉在失去的光阴洞窟里,弥漫的是老早已消逝的歌声;过往的莺啼,在时空中找不着位置,惟有寄居在嗜痂者的耳畔脑际。与记忆,与梦幻,织成一大片桃红绯紫的安全网,让我们这些同类梦魂有所归依”。
李天葆是二十世纪末迟到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而且流落到了南方以南。就着他自觉的位置往回看,我们赫然理解鸳鸯蝴蝶派原来也可以是一种“离散”文学。大传统剥离、时间散落后,鸳蝴文人抚今追昔,有着百味杂陈的忧伤。风花雪月成了排遣、推移身世之感的修辞演出,久而久之,竟成为一种“癖”。这大约是李天葆对现代中国文学流变始料未及的贡献了。
问题是,比起清末民国的鸳蝴前辈,李天葆又有什么样的“身世”,足以引起他文字上如此华丽而又忧郁的演出?这引领我们进入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的辩证关系。李天葆出生在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是马华社会政治史上重要的年份。马来西亚自从独立以来,华人与马来人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承上的矛盾一直难以解决。
当局大举镇压,趁势落实各种排华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人社会念兹在兹的华文教育传承问题。
在一个中华文化备受打压的环境里,马华作者究竟要何去何从?他们如何运用华语——中文——持续他们的话语权?一九九O年,第三届乡青小说奖特优奖由李天葆的《秋千·落花天》和黄锦树《M的失踪》平分秋色。这样的结果充满象征意义。彼时的黄锦树已经负笈台湾,但对故乡的关切未曾或已。他的评论和小说精彩犀利,目标正对准马华文学与中国(想象)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黄认为既然马华已经是独立的政治文化主体,没有必要遥奉中国/唐山正朔,自命为海外薪传。而“好的”中文书写成为隐喻性的辩论焦点。《M的失踪》讽刺所谓的马华经典作家其实查无此人,间接也对此前写实主义所代表的创作传统提出质疑。
李天葆的《秋千·落花天》恰恰反其道而行。这是个平凡女子的择偶故事。女主角心有所属,但几番波折,毕竟没有结果。多年以后她仍然云英未嫁,回顾往事,犹如春梦了无痕。李天葆细细写来,令人动容。他没有黄锦树式的身份认同和语言焦虑,有的是千门万户里小女子婉转委屈的心事。李天葆毫无“破”中文的意图,一任让他的语言踵事增华。从标题《秋千·落花天》开始,中国风味的意象就浓得化不开。
李天葆可以在“黄锦树们”的批判对象中名列前茅。但我另有看法。与正统写实主义的马华文学传统相比,李天葆的书写毋宁代表另外一种极端。他不事民族或种族大义,对任何标榜马华地方色彩、国族风貌的题材尤其敬而远之。如上所述,与其说他所承继的叙事传统是五四新文艺的海外版,不如说他是借着新文艺的招牌偷渡了鸳鸯蝴蝶派。据此,李天葆就算是有中国情结,他的中国也并非“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论述所反射的梦土,而是张恨水、周瘦鹃、刘云若所敷衍出的一个浮世的、狎邪的人间。在这层意义上,李天葆其实是以他自己的方法和主流马华以及主流中国文学论述展开对话。他的意识形态是保守的;惟其过于耽溺,反而有了始料未及的激进意义。
李天葆对文字的一往情深也让我们想到他的前辈李永平与张贵兴。李永平雕琢方块文字,遐想神州符号,已经接近图腾崇拜;张贵兴则堆砌繁复诡谲的意象,直捣象形会意形声的底线,形成另类奇观。两人都不按牌理出牌,下笔行文充满实验性,因此在拥抱或反思中国性的同时也解构了中国性。黄锦树将两人归类为现代派,不是没有原因。两人都颠覆了五四写实主义以降、视现代中文为透明符号的迷思。
比起李永平或张贵兴,李天葆的文字行云流水,可读性要高得多。这却可能只是表象。他征引古典诗词小说章句,排比二十世纪中期(多半来自台湾、香港)的通俗文化,重三叠四,所形成的寓意网络其实一样需要有心人仔细破解。而他所效法的鸳鸯蝴蝶派,本身就是个新旧不分、雅俗夹缠的暧昧传统。究其极致,李天葆将所有这些“中国”想象资源搬到马来半岛后,就算再真心诚意,也不能回避橘逾淮为枳的结果。正是在这些时空和语境的层层落差间,李天葆的叙事变得隐晦:他为什么这样写?他的人物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中国性与否也成为不能闻问的谜了。
一九三八年底郁达夫来到新加坡,开始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流浪。这位新文学健将写下大量旧体诗词,质量都超过他的政论和散文。郁达夫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里坦承:“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从古典诗词到过时流行歌曲,李天葆“骸骨迷恋”的对象有了深沉的质变;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过程,也隐含着无可奈何的让渡。如果古典诗词象征一个其来有自的传统,流行歌曲原就是来源驳杂的音乐,而且忽焉兴起,忽焉寥落,毕竟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比起穷愁赋诗的郁达夫,聆听过气时代曲的李天葆出落得更为荒凉颓废。那中国来的浪子早就下落不明,他的吟哦已经成为绝响,或更诡异的,已经堕落成靡靡之音。
或许是这样(等而下之的)“骸骨”才真正烘托出李天葆的历史叹息和身份反思。除了过气流行歌曲,李天葆也迷恋老电影老照片,而且独沽一味。他从历尽沧桑的女性角色里看到了“圣母声光”,从银幕上的幻影明灭参详人生美学。田中绢代、叶德娴这类明星,上了点年纪,有了点阅历,才是他的偶像。
《绮罗香》一系列故事越到后来鬼气越重,而且以《蕙风楼鬼话》作为结束,几乎是理所当然。
我曾经以“后遗民写作”的观点探讨当代文学里有关事件和记忆的政治学。作为已逝的政治文化悼亡者,遗民指向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他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即主体性摇摇欲坠的边缘上。如果遗民意识总是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变本加厉,宁愿错置那已经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正统的正统。
以这个定义来看李天葆,我认为他堪称当代后遗民梯队里的马华特例。摒弃了家国或正统的凭依,他的写作艳字当头,独树一格,就算有任何感时忧国的情绪,也都成为黯然销魂的借口。他经营文字象征,雕琢人物心理,有着敝帚自珍式的“清坚决绝”,也产生了一种意外的“轻微而郑重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张冠李戴”,因此有了新解。而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绮罗芳香里的鬼气、锦绣文章中的空虚。就这样,在南洋,在姚莉、夏厚兰的歌声中,林黛、乐蒂、尤敏的身影中,李天葆兀自喃喃诉说他一个人的遗事,他的“天葆”遗事。
(本文节选自台湾“麦田出版”《绮罗香》)
·本辑责编 马洪滔宋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