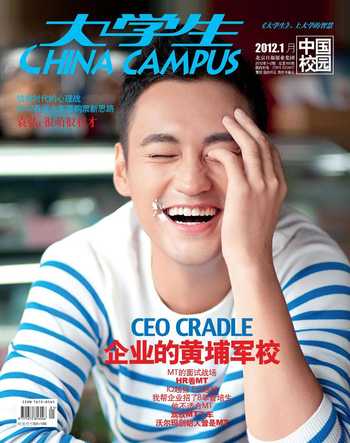芜,湖
清歌
芜湖,芜,湖。字面已经很清楚,草本的品相,水做的骨肉。
所以芜湖是女子,有着挥不去的闺阁气。我与她相伴三十年,同胞一体,相好亲爱,却难说出她究竟好在哪里。她是鱼米之乡,商埠重地,有铁画,蔑编,梨簧戏……是五味俱全的小宝地。但无论用哪一种去匡她,拿什么去比她,都还缺了一味。她的引子是水,所以千变万化,她是2000年前一脉大水自东而来,忽然迎面天门山一横,像逶迤而行的仙人打了个趔趄,便一折,一回,折而北去。其时道旁湖沼密布,遍布鸠鸟,芜藻深幽,称为“芜湖”。
芜湖是小城,小是五脏俱全的小,城却是真正的一方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自古以来是皖江要塞,兵家必争的芜湖城,却少见笔直通畅的大道,满城拐来弯去的深巷子,不供人快马尽看一日花,倒是可以走街串巷寻好酒。芜湖的街巷都离不开水,不在江边,就在湖畔,或者从桥畔斜出,四通八达,是串联城市的经纬。
芜湖是一座向里收着的城。她也真真像是养在家中的小妹一样,是每一个芜湖人的心头肉。芜湖人在外提到家乡,经常掠过安徽,只说芜湖,似乎徽系那一道龙脉,也系不住一个芜湖似的,必要将她单独凸显出来。别人都说芜湖风光美,空气好,芜湖女孩的整体标致,但进一步再问到芜湖哪里最好?芜湖人也只是笑一笑,像有一把暖火融融的点在心窝里。芜湖的好,是那种家长里短,街知巷闻的好,是舒坦,是爱不释手。她的香,贴心得不得了,直接的不得了,是油烟香和油墨香,熏烤香和熏花香的入世和实惠。
芜湖的美味从不去江湖上闯名堂,不去外面打江山,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汤汁淋漓,原汁原味全在深深的巷子里收着。我小时候住在中山桥下,依着江。我时常捧着一个大大的搪瓷茶缸,独自走过夜眠的街去桥头下馄饨。一片温暖明亮的灯火,一个一个的馄饨面摊,肩挑可走,支地可坐,摊头雪亮的白炽灯,热腾腾的水气中,老师傅正在下馄饨。配料,舀汤,捞起,“嘶啦”一声泻入碗里,一边撒进萝卜榨菜,一边捻起香葱,在汤面上点成一圈,转眼一钵美味浓香扑鼻,大功告成。我付了两角钱,捧起沉甸甸的茶缸,心满意足地往回走,树上团团簇簇是被月照成银紫的泡桐花,远处是沉睡的中江塔,拙而挺,苍然屹立。江中渔火明明暗暗,长江虽近在眼前,却像看不见一般,只是那闲闲水声,缓缓入耳……我在这样的一座桥下,这样的一条江边慢慢长大。
只要有外地亲戚来芜湖,必会被拎着去老字号茶楼,那里有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与之媲美的小笼汤包和虾籽面;在那些压抑的成长期里,补课的脚步沉重地踏在冬天的晚上,梧桐树下却有刚揭锅的一包豆沙的梅花糕,油炸的臭干子,脆得没办法吃完整的炸春卷;还有那些背着画板,单车驶过镜湖烟柳堤的春日,路旁是永远排队的凉粉摊,一溜青花碗,里面雪白一堆银丝粉,浇上一勺鲜红水辣椒和剁碎的萝卜丁,小虾皮,香菜末……远处的公园里是一溜老人在遛鸟,白石圆桌上搁着棋盘,旁边有剃头挑子,老师傅一面给客人系白布舀水,一面有人拎着篮子上前卖热腾腾的藕稀饭和炒栗子……芜湖人的吃,浸染在每一日,每一步,每一处里,是言语形容不出的舒坦和习惯,非自家人不能体会。
这是个适合生活,适合养老,更适合被挂念,被称为“家”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地方,才使人对“归依”充满暖热的期待。她可以从明媚少女,一步步演变成体贴少妇,和与你一同搀手的耄耋老人。你从哪一种眼看她,她便正巧是那个模样。她不是骄矜尊贵的大小姐,她是懂事知礼会情趣的小大姐。她是晒过阳光的热被窝,远行时恨不得折起放进衣袋一起带走的小棉袄,体贴温存骨肉亲。她丰富但不厚重,风情但不轻佻。她是桂花树下的脂粉气,铁画遒劲淋漓的大师气,竹篾编织的工斧气,以及瓷盘菜篮里的持家。她的气质充满流动,她是青衣江畔的一个梦境,是下游平原的一块沃土,是疾流中的一个驻足,音符中的一个缓顿——她叫芜湖。
责任编辑:刁雅琴
——储铁艺铁画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