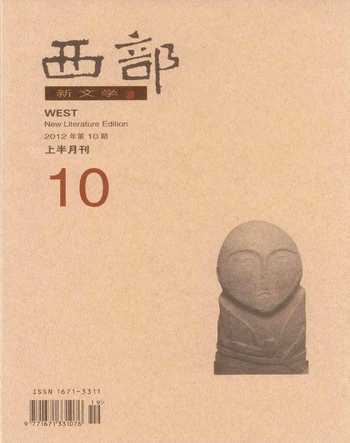最初的梦想
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与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的事物。
——海子《弑》
1
十年之后,当重木再次仰望高大庄严的凤凰传媒集团的大楼时,他想起父亲和夏院的话。
九月的南京天空万里无云,澄澈无比,仿佛永恒的悲伤。重木看着自己手中厚厚的一沓书稿,莞尔一笑。依旧是十年前的信纸,十年前的笔迹,十年前的题材和十年前的自己,唯一改变的是心境。此时的心情无比平静,宛若千年的纳木错圣湖。
此时,他想找个地方坐坐,吸一根烟,于是,他想到了对面的那一家小旅馆。这里的一切都如十年前一般。精干漂亮的女老板,坐在门前剥豆子的老人,还有这间低矮阴暗、条件很差的房间。
“是住房的吗?我家这里是整个南京最便宜的旅馆了,六十块钱一个晚上,有电视、空调,还有卫生间,很方便!”老板娘依旧是媚笑着对他说。
“一个人。住一个晚上。”重木说。
老板娘热情地带着他去看房间。走廊的两边墙壁上挂着廉价的工艺画,熏黑的灯泡散发着昏黄油腻的光芒。每个门上挂着破旧不堪的小牌子,上面的数字大都被磨损了。而在走廊的尽头,就是重木的房间。
“这是您的房间!”老板娘说,“这间屋子比其他屋子多一张写字台,我看你像是个动笔头的,也方便些!”
房间如记忆中一样。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一个小柜子,二十一寸的彩电,厚重灰暗的窗帘和肮脏狭小的卫生间。重木把行李放进柜子里,躺在床上重新看了遍诗稿。床褥很潮且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味道。
落在南方与北方泪水旁的村庄
是抑扬与流言 是我的故乡
封闭的红木门里关着哭泣的婴儿
稻田中收割与死亡
在只有一根蜡烛的屋子里
我听见破碎的过去破碎
和我十九年前遗落的梦想
房间里寂静无声,而窗外嘈杂纷扰的汽笛声、叫嚷与高笑声也都在此刻停滞,缓缓地,以一种回忆——沉重的方式赋予重木。
他知道父亲不会喜欢这些东西,也许直到今天……如果父亲还在的话,他依旧不会同意自己为了这些“ 无用的、招麻烦的”东西而丢弃工作。如果父亲还在,当他看到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依旧是一贫如洗——没有房子,没有车,亦没有妻子。曾经村子里唯一上过大学的,现在却是村子里最没用的。
想到这里,重木不由得苦笑。在村人的眼里,自己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整日蜷在屋子里一待就是一天,不出去找工作,不与亲戚走动请他们帮忙。自己的一切为村里提供了无穷的反面教材和茶后谈资。在那个北方封闭的有着百户人家的村子里,贫穷即说明了一切。
他曾经努力地希望父亲摆脱过去的阴影接受自己的梦想,后来他才发现,父亲并不是与自己或是自己的梦想过不去,而是与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历久弥新的恐惧过不去。或者说,是那些东西从未放过父亲,无论多少年过去了,从未松手。
重木想起夏院的话。她说“假如生活将你欺骗”,而曾经的自己从未好好地、认真地想过这句话,或说是自己在小学四年级就会背的普希金的诗。
2
重木喜欢沉浸在回忆中,无论是痛苦或是喜悦的。那些逝去恍若落日流金的日子里,散落着自己太多的青春与青春里的热情、孤傲、不屑与梦想。那些永不褪色的东西,执拗的东西在以后的日子里显得弥足珍贵。就像祖母(在这里,重木依旧想叫她奶奶)在自己年幼的心灵里埋下的,并决定自己一生的文学种子。“美丽的叶赛宁村庄,海子的麦地和太阳”,还有许许多多如蜜糖般甜美的岁月。
重木感到心里突然堵得难受,或许是房间的原因,他感到不安与悲伤,就如十几年前那刻的那些莫名的悲伤。重木披上衣服离开房间。傍晚的南京依旧是喧闹不已,拥挤、尖叫的汽车和行人,匆匆逝去,就宛如西方最后的一缕红霞也在重木抬首之时轰然落下。繁华落尽后的荒凉与孤独。南京,这座辉煌了百年的城市,如今已如耄耋的老人,令人疼惜和厌恶。
旅馆前的老人依旧坐在门前,双眼迷蒙地盯着某处出神,脸上是悲伤的表情。十年之后,刻薄的时光对这位老人依旧是无能为力,仅仅是在他苍老的脸上留下一些不甘的痕迹。而如今的自己早已是面目全非,无人能识。
重木在老人身旁的矮凳上坐了下来,也望着老人凝视的地方。许久,老人突然以一种仿佛智者的声音对重木说:“我以前见过你啊!在那幢大楼前!”老人伸着枯瘦干焦的手指着对面的凤凰传媒大楼。
“您老的记性真好!”重木说。
“你一个人?”
“就一人。从前也是我一人……”重木笑了笑,突然有了兴趣。 “以前是父亲拦着不让来,就一个人偷着来了。当时还是奶奶给的钱,她支持我来这里。她说我有榆树赋予的灵气……也能写出叶赛宁和夸西莫多那样的诗句。”
老人点了点头。重木继续说道:“我奶奶也是一位诗人。她说只做过十几天,后来就被抄家批斗了……我祖父当时在县图书馆工作,并且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抄家的时候,我父亲可能才十几岁,他被吓怕了。在家里搜出了《普吕多姆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还有叶芝和聂鲁达的诗集。这些东西使得原本可以劳改的祖父失去了机会。疯狂的红卫兵揪着奶奶在街上游行,并给她挂上了‘牛鬼蛇神的牌子。”
重木再次感到一股巨大的悲伤与不安从四周袭来,包裹着自己。夜幕下的南京显得过分的吵闹与绝望。那是他十年前,一个人站在热闹的拥挤的新街口时所感到的绝望和迷茫,还有恐惧。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迷路,看着灯红酒绿,高楼耸立,唯独没有自己安身立命之所。那样庞大的孤独和绝望就如今夜的南京。
“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海子是这样说的。
“那后来呢,儿子踢了母亲。”老人看了眼重木,缓缓地说。
“是的,在一次集体批斗中,他们让父亲揭发奶奶的罪状,父亲一一说了,并跟着众人一起踢了奶奶……父亲的那一脚刚好踢在奶奶的膝盖上,奶奶从此跛着走路。在被关进‘牛棚的第二天祖父就因不堪折磨自杀了。他年少的时候是整个镇子唯一的秀才,整个镇子的光荣。奶奶一滴泪也没有流,当晚红卫兵就把祖父的尸体弄了出去,后来就一直没找到。”重木掏出支烟,点上。他看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
他想起父亲在低矮的草屋里偷偷写字的那个夏夜。浓稠的夜翻涌着滚烫的热气,夏虫啁啾惹人烦躁。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蚊子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奶奶就静静地躺在偏屋里,穿着整洁的衣服,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上也抹了她平日里最爱的头油。此时的奶奶如往日般整洁干净,面容沧桑,唯一不同的就是她不会在黎明醒来,不会再读那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诗,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普希金的、叶赛宁的还有泰戈尔与艾青的。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奶奶临终前对重木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奶奶对父亲说了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并且想了十年依旧不知道会是什么。
“奶奶的挽联是父亲写的,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父亲是识字的,并且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父亲一直以来都是极力反对我走奶奶的路,直到他过世时留给我的遗言依旧是。当时,我一个人去了四川,没能见他最后一面!”重木感到手中的烟一点点燃完,熏人的烟让老人咳嗽连连,重木赶紧掐了烟。
“你来是做什么的?”老人问。
重木说:“来完成多年前错过的事情!”
“你到过不少地方?”
“是的!我走过不少地方,新疆、四川一带,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圣湖……我想四处看看,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就像奶奶曾说的‘榆树所赋予的灵气。我看许多人的诗,无论叶赛宁还是叶芝,或者是里尔克、马拉美、兰波甚至是拜伦、雪莱,他们都拥有独属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有独属自己灵魂。语言和表达方式可以模仿和理解,灵魂却不行。这就是我要用十年甚至更久来寻找的东西。”
老人微微地叹口气,他说:“别人不一定买账!现在人很难讨好!”
重木不由笑出了声,他说:“我写诗不是为了别人,只是想弥补一下曾经的遗憾。”
这时,老板娘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也许是今天不少人住宿,她一脸欢笑。老板娘坐到一把椅子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重木:“哎!你可不要误会了,我觉得你像一个人……嗨!只看过几眼,我都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
“一个男孩?”
“对了!还让你猜中了。就一个人,大约十七八岁,提个包,留着长发……看样子也是农村来的,我以为是来打工的,你猜怎么着?那小子是来找对面出版社的,我还以为他有亲戚在里面,不想就他一人来了。”老板娘皱着眉头说。
“为什么您记得那么清楚啊?”
“也不是记得清楚。不是今天看到你了吗?也就想起了,就这么一说。我这里每天有那么多人,怎么会记得哪一个!而且你住的那间屋子就是那个小伙子住过的。别说,你和他还有些像!”
重木腼腆地笑了笑,起身准备离开。
那老人又望着他说了句:“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已经好多年了!”重木说。
“问人家这干什么啊?”老板娘不悦地问老人,又对重木指了指老人的头,“有问题!”
重木不语,走回房间。
3
重木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回想着刚才老人的话。不知不觉中,他的脑海里出现父亲的身影。依旧是那样的瘦弱,依旧挺直了腰板,面容严肃,不苟言笑,说话冷漠,独断专行。
他从未用温和的语气和自己说过话,全都是命令的、不可抗拒的,而自己的未来也是由他掌握。念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他都已经布置妥当,即使不在了,也依旧主宰着一切。
但是他也知道,上帝并未如他所愿给他一个温和听话的孩子,而是一个处处与他作对和反抗的调皮鬼,一个在自己母亲身旁长大,对那些文学,对那些死人文字感兴趣的孩子。他对此怒不可遏。
重木开心地笑了,像个孩子一样笑了。继而是呜咽,大哭与痛哭流涕。就这样无助且孤独地哭着,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突然地想哭。
于是,在这狭隘阴暗的房间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抱头大哭,歇斯底里。
“我感觉到千百万人在受苦受难。可是,我仰望天空,冥冥中觉得世界还能好转,这场残酷的战争也会终结,和平与安详会重新回来。”
在那个夏夜,奶奶为自己读《安妮日记》。父亲就坐在外边,静静地吸烟。那一年,就是自己独自跑到南京的时候。
……
“奶奶,以后我写诗也会有那么多人看吗?”
“不必为取悦或迎合别人而去写诗。写诗只是给自己看的,给奶奶看的。”
……
原来,在十年前的那个夜晚自己就已经走在自己为自己开辟的那条注定孤独与不安的路上。也正因此,所有人都不会了解为此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就像父亲为自己所付出的。
时间开始慢慢沉淀,他再也不必去猜、去想,奶奶弥留之际会对父亲说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要感谢落日,让所有人看到他远去的背影,他已经把这世间惊世骇俗的一幕展示给了我们,因此一切都显得格外珍贵。
宋杰,笔名重木。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不安的时代。许多东西都渐渐地消失,但文学不会,反而正在以一种奢侈的方式百世流芳。我想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说出只属于自己或是无意中又暗合他人想法的话。我只想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来看待这些真假难辨的世界,我想用自己的文章来证明梦想永远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