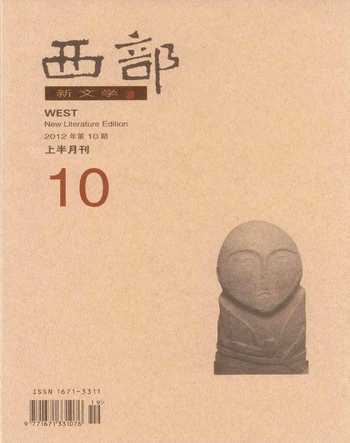人物散章
胡澄
临终的孤独
随着死期的临近,父亲越来越不安,越来越需要子女们陪伴。此刻,医治无术,生还无望,父亲只是希望子女们围着他,一家人团坐在他周围,只有这样他才稍觉安慰。我知道父亲舍不得与我们分离。
一家人一起走到现在,忽然出现了一条岔路。父亲一直是领着我们走的,现在,他要丢下我们,独自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父亲非常无助、孤独。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的临终状态:骨瘦如柴的他,卷缩在床的一角,眼中含泪,时不时地瞄我们一眼,竭力地呼吸着,直至渐渐慢下来、慢下来。一家人围着他,但守不住他。他多么愿意留下来,与我们一起,但他必须离开,独自走。死的艰难其实是一种孤独。父亲最后环视我们一眼,极不情愿地放下了他的呼吸和心跳。
我对此刻的父亲充满难以言喻的怜悯。但我转又想起别的生灵,它们无声无息地死,谁又了解它们的临终状态呢?动物世界远比人类残酷,年迈的猴王或狮王,必定被驱逐,远离家园,妻妾被霸占,子女被残杀。曾经辉煌的他,必定在贫病交加、凄怆的孤独中死去。生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终结方式呢?圣者们一直在寻找出路,寻找一种安详、圆满的完结。
死而升天,或死而往西方极乐世界去,都是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憧憬,但也未知其不真。谁又回来否认其存在呢?科学也不否认人临死时的种种映象。我的母亲临死时看到空中一片鲜花,还有七仙女;另一些人看到菩萨前来接应。这些都是对死的安慰,消除死的孤独,使死变得丰富多彩。
渐修者,早早准备着死,让死的技艺炉火纯青。
烟 水
这一片开阔的水域,杨树、柳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树,三三两两地立在水中,它们的影子倒着立在水中。现在是三月,叶芽不断冒出来,绿焰般往上空和水底蹿,但它们看上去一动不动。一辆汽车轰隆隆从桥上驰过,桥的影子微微晃动,但丝毫没有惊扰水中的寂静。树丛之间,弥漫着似有若无的烟缕。坡堤上,盛开的油菜与斜照的夕光相映成金。绿树丛中粉墙黛瓦的小屋似乎从没有人出入。白鹭霍地起飞,霍地降下,白鹭的影子比白鹭还白。堤岸与山相接,沿堤往左,两山相交成四十五度夹角,山色嫩得淌水,如果将它们麻花般绞起来,一定会绞出另一条绿色的河流。夹角之间,散落着油菜、小麦、桑树、桃花和飘棉的杨柳,沟渠低声地欢唱,斜阳恰到好处地照耀,似乎为摄影作的准备。远远的,她看见丈夫笑得这般开心,他和两个漂亮的女同事谈论有关摄影问题,似乎非常有趣。一个五十多岁又割去一侧乳房的女人,她知道,对于这个世界她已经是一个多余的局外人;对于整个人生也是一处过于绵长的闲笔,就像热门连续剧的最后几集拼凑,实在是没有故事了。尽管,曾经被珍爱,曾经张扬过,曾经是一幢别墅里显赫的女主人。唉!一切如真如幻如烟水!但她微微笑着,觉得活着终究是好的。感谢我的双脚把我带到这儿,她这样想。感谢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这一切!哦,谢谢这多余,再也不用怕点名了,再也没有人能点到我,这个世界再没有严厉的老师和上司。
免 战
她洞悉了这个男人,知道他订了一连串的作战计划。如果他迷恋于作战,那我岂不成了战场?她这样想。她找到他,直捷了当地告诉他:她喜欢他。“如果你是真诚的,那我们继续;如果不是你内心所需,则请停止。”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十分冒险,也十分愚蠢,这是美丽人生最具破坏性的举动。通常,男人会感到乏味,从而使一场尚未开始的故事胎死腹中。一场圆满的战略,尚未部署就宣告结束,这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再说,作为一个男人,谁会喜欢未经战斗的战利品呢?然而,一切经不起考验的东西终究是假的,一切假的东西不如提前死去。“我这样做减少了许多消耗!”她不无得意地想。
男人喜欢将爱情看成两个人的战争,如果还有另外人介入,则升级为多国战争;往往战争结束意味着爱情终结。归根到底是,男人喜欢战争,所谓奋斗即是各种各样的战争。好战的因子埋藏在男人的血液里,而部分男人则把征服女人当作攻打山头,打下一个就会去打第二个、第三个……女人们啊!要洞悉真假,寻找和平,寻找两水融汇,共泽原野,默然无声而又源远流长——这样的爱情。
戏一样的婚姻
到了婚姻登记处,才发现忘了带身份证。男朋友因此觉得这场婚姻或许不妥,再也无法下决心结婚。男朋友的心像开败了的水仙花东倒西歪了,她知道,他已四处活动寻找新的女友。奇怪的是,他们始终不曾反目成仇,相反他们始终是朋友,甚至,与新女友相交的情况都会如实禀报这个本该早已成为老婆的女人。一年又一年过去,男人成了王老五,女人成为剩女。相互都有些许不舍,又有些许不满。在男人看来:女人内心含玉,可外表实在难以让人满意——这其实是根源所在。在女人看来,男人仪表堂堂,可内心捉摸不定。然而女人始终怀着当初的梦想:希望他与所有女人无缘,终有一天彻底回头。可王老五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女人结婚生子,女人至此才开始下决心嫁人。有一天,她泪水涟涟地想说:“没人要我了,我与新男友又分手了。”“亲,把他逮回来。你就告诉他,如果放弃你,就等于放弃了终生一遇的爱情……”——我这边说得随便、玩笑,她那边却真的实施,付诸行动。就这样决定一生的婚姻定了下来,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及一场轻描淡写的爱情定格在一张纸上。这张纸多好啊,要是没有它,多少男人会在女人中终生飘荡,多少女人老死等不来一个男人!
丑女的幸福
翻阅结婚照的时候,同事说:“唉,你已经够难看了,你老公比你还难看。”大家笑成一团,似乎“难看”是个美妙的赞扬词。新婚的她确实够难看,婚纱仿佛披在大象身上,五官无一官俊俏,可就是脸上的表情不难看,那笑有些傻,却是晴朗的。单位里有许多剩女,有人结婚总让人羡慕,好像现当今结婚是件奢侈的事。人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居然捷足先登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她刚出院不久,诊断是“肺癌”。要不是医生说有病理切片这样的诊断依据,人们一定会找医生痛骂:什么鸟庸医,这什么诊断?可是,医生确实将她的胸膛剖开,切下了半小叶肺,这病了的半小叶肺给家属看过,以示诊断准确无误。幸运的是,她痊愈了,出院了,结婚了,生女了,并且接着幸福,依然白白胖胖、开开心心,仿佛从来没有病、没有痛,也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和阴影。
艳 遇
“他有四天没给我打电话了,他这次回老家带着一个女人。”表妹泣不成声。过了几天,表妹说:“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们三个一起见的面。我说:‘谢谢你爱上我老公,不过他送你的戒指是我们结婚的信物,我想向你买回来。至于我们俩,取谁舍谁,一切由我老公决定,如果他选了你,我就把他让给你,但他必须净身出门,因为他违反了我和他的契约。如果他选择我,则请你与他一刀两断,从此不再联系,否则我们三人都不幸福。”结果是,戒指免费收回;表妹夫也选择了表妹并答应把手机交于表妹监管,从此不再和那女人联系。但表妹夫从此失魂落魄,经常一个人发呆,还口口声声跟表妹说:“她是真的爱我,并不是看上我的钱。她说即使我背债她也愿意嫁给我。”说得表妹寝食难安,充满危机感。有时,表妹看得不忍,就说:“你要是实在想她,就给她打电话吧,当我的面打,我保证不插话。”表妹夫于是真的给那女人打电话,打了一次,无人接听,再打,又是无人接听。凭直觉,表妹夫觉得她不接电话是因为身边有人,不方便接听。不久,真相大白了:她是某娱乐场所的陪酒女,不理表妹夫是因为有了新业务。
要与死人离婚
假如他死在她后面,这辈子她将多么幸福!可是,他提前死了,死于一场车祸。随着他的死,一切破绽都露了出来,仿佛他活着就是个守门员,把自己的一切秘密给守住。呵!原先一心一意爱着她的这个男人,他的前妻要求分到一半家产;另一个不认识的女人领着一个十岁的男孩要求继承全部的资产,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按当地风俗,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这个女人,被他生前口口声声爱着哄着小心呵护着的人,严重地傻了眼。悲伤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跟你离婚!”
送葬的队伍里有三个怒目侧视的女人和三个哀哀哭泣的孩子。他的照片,嘴角浮笑,似乎在看一场好戏。
股市和钱
股市跳水,我手心淌汗,第一次进股市,我不知道股市这么流氓,一下子掉下来,一年的工资没了。可伙同我炒股的同事说:“胡医师,咱有工资咱怕啥也?反正咱不会饿肚子。”那口气像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那么豪迈,然而用于吃饭的钱,她却像六十年代那般节约。从北方来到南方后,家里的老公公第一次来探亲,在她家大约住了十来日,她总是数落那老头不知节俭,筷子总伸向那碗红烧肉。还有一位同事,没有轿车也没有电瓶车,可他上下班不乘校车,原因是:不乘校车可以拿到乘车补贴。这个补贴用于坐公交车绰绰有余,一个月大约能省下百来元钱。股市里,他已亏掉了三十多万元。
蔡医师
蔡医师是文革前中医学院本科生,父母都是离休干部,娶了一个离休干部的女儿,也是正规医科大学的本科生。他们婚后住在一套六十多平米的老式套房里,直至现在。二十年前,当我们这些新分配工作的小年轻们身无分文时,他家已有二三十万元的积蓄。这在当时可以买上非常像样的二套商品房。但蔡医师认为,他已住得好好的,不必折腾房子。蔡医师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业余时间练练毛笔字,双休日与老伴一起到免费公园走走,从不打的,也不曾想到过买车。现在的衣服布料不像以前洗几桶水就破,一件衣服可以无休止地穿下去。因此,蔡医师一家花钱很少,几乎每月都有余钱续存到银行里去。半个世纪下来,积了百余万元钱。渐渐大起来的外孙偶尔来他家住,他的老伴始觉得家里空间太少,让外孙住着窘促,想买套大一点的房子,可是百余万元人民币,在现在的杭州城里,一个单间都买不下来了。老伴因此时有怨言,可蔡医师还是认为他们住得好好的,用不着去买房。他说:“挤什么啦?一点不挤。我睡沙发好啦!”
蔡医师到现在仍是个中级职称,老伴要他去升一个高级,蔡医师说:“升什么啦?升不升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水平。”
蔡医师只有一个女儿,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后来读了点化妆方面的书,现在电视台做化妆师,赚的钱是蔡医师的两倍,可她经常要蔡医师接济。为了方便接送宝宝上学,蔡医师给她买了辆“速腾”,自此以后,她经常打电话说:“加油没钱了,老爸汇一点过来。”“交保险钱不够,老爸借一点给我。”大约过了两年,外孙前来试探,说:“外公,这个车太差了,换一辆好吗?”
“领 导”
领导就是我们的头儿。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六人,领导一人加上我们五人。领导从来不把自己加入“我们”之中,在她看来我们五人都是“你方”,而她是“我方”。有一天,我们之中的一人,她的父亲死了,她哭着向领导请假。领导说:“等一等,我问问临时工有没有丧葬假?”“就是没有,我也走了!”我们之中的她此时又悲伤又愤怒。对于这一点,领导并无认识,她觉得一个临时工,许是没有丧葬假的。她这是负责任,以免放错了假。后来我的父亲也要死了,眼看着就要开学了,我哭着给领导打电话,我说:“我的父亲快不行了,我可能不能按时报到了。”领导说:“你那个进东西的单子在不在身边?”她的意思是:如果“进东西单子”在身边,就让我打电话进东西。再后来,领导的妈妈病了,领导说要去送妈妈医病。我们说,“好的,你放心去吧!有什么事我们会处理的,处理不了给你打电话。”现在,我们大家非常高兴,领导不在时,我们经常挤在一起窃窃私语。我们说,奇怪,领导好像变了。
拉平板车的老人
拉平板车的老人八十多岁了,无儿无女无固定资产,但他很快乐,每天穿街走巷的,捡可乐瓶、易拉罐、旧纸板等,变废为宝。困了,往平板车上一躺,每天都能睡得美美的。他面容慈祥、身板扎实,无病无灾。汶川地震了,全国人民都为之哭泣、为之献力。拉平板车的老人找到镇政府,要求献上自己的全部财产——三万多元钱。镇政府工作人员,看着他的穿戴,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接下这个钱。后来经多方请示,决定收下老人的几百元钱,其余的奉劝老人留下养老。老人无奈,只好拿着钱返回。第二天,老人又去镇政府捐钱,如此三翻几次,镇政府工作人员只好替灾区人民接下了老人的全部心意。老人那笑,至今仍留在我眼前。老人一定没读过佛经,他不认识字,不懂得放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等义;我读过了,能释字解义,然而,我永远只有羞惭,永远只有在口头上羞愧,这辈子都不会彻底改变行为。
父老的病与死
一 病
母亲病时,他捧着自己的头,心想:“一天上千元的医疗费,母亲怎舍得花呢?主要是母亲不认识字,不懂理,因而特别怕死。”“我绝不会像她那样不顾后人。”他说:“母亲,你一辈子都没赚那么多钱。”
不久,他病了,得了跟他母亲一样的病,但花了更多的钱。病情复发时,他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钱不成问题,我就是要活命,要做人。”他的儿子捧着自己的头,心里嘟噜:“钱不成问题,亏他说得出来……”
后来,有了农医保,拎了一大叠发票,报回了大约20%的医疗费,折合起来上万元。这可把他一家乐坏了,仿佛这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政府真好啊!”他们感叹。当然他们得继续省吃俭用,花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还债。
二 死
死神其实已多次造访过她。死神来到她家,直捷了当地进来,死神看了看她,他不想那么毫无阻拦地把她带走。死神悻悻地走了,觉得这一家人好乏味。由于她的多余、她的愚笨,谁都不想争夺她,她因而多活了一阵子。但死神或许是有任务的,当他过于劳累的时候,他就拿她凑数,我猜想。就在昨天,我看到她时,她还好好的,还认得我。我递给她二百元钱,说:“拿去买吃的,爱吃什么买什么。”她高兴地点点头。今天早上,我接过电话,那头告诉我:她死了,就在昨晚,也不知什么时候。
房前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发出“啊!啊!啊!”的惊叹。都说:怎么这么快呢?昨天还好好的。大家平静地谈论她的死,仿佛在谈一场传奇。我是真的替她高兴。我说:“婶母,还是您傻人有傻福!安心地走吧!别再回来。”
他一辈子走街穿巷,积攒了上百万的钱。现在,躺在床上,他知道这辈子再也不会赚钱了。这辈子,他除了赚到钱,还赚了一个弱智的儿子,留有一个多病的老伴。“不花钱就等于赚钱。”——他这样想。似乎躺在床上,还有些许赚钱的快乐。当然,死神造访他了,他知道。但他不想与死神抗战。“随便你,何时将我带走,反正我不花一分钱。”他倔强地想。“将钱留给弱智的儿子,他还要活下去。”——他那么清晰,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似乎还伴随一丝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