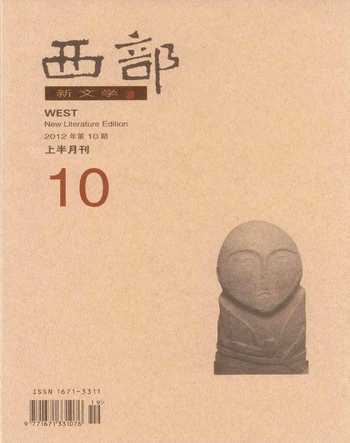病房手记
病房里的一张床
躺在病床上三天了,辗转反侧,没有困觉的时候,就免不了多想,一下子前生后世的想了那么多,潮水般涌来的,竟然是这么些年来差不多被自己快要忘光了的那些“病”。什么头疼脑热、热胀风寒,那些潜伏在身体里的疾病,在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欺骗着我们,而我们的肌体里,早已被埋伏了疾病的千军万马,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也不愿意想到这些被疾病缠绕的问题。只有等到这一天,你躺倒在病床上的时候,才愿意面对这一张张签满了“疾病”的病历单。所以,一个人有了病,他才需要健康,一个没有病的人,他要“健康”这个劳什子做什么?
对于习惯了家庭生活的人来说,一下子住到病房里来,面对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病人,多少有些困难和尴尬。但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就像你无法选择疾病一样,有时候,你也无法选择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住在我对面九号床上的“病人”,是一位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的中年男人。我先他一个小时住进来,等到他被老婆陪着住进来的时候,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多少在心理上有一点“老人”的味道了。他懵懵懂懂地走进来,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我,有一点拘束还是紧张说不清楚,反正是半天没有一句话,见他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又不愿意开口,我只好故作友好地冲着他笑了一下:你好!可能被我的这一声问候给“吓着”了,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便仓促地在嗓子眼里回了一声:你好!声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脸上的笑容也是被临时挤出来的。
就这样沉默着谁也不说话,但他总是试探性地不时用眼睛盯着我看,眼神怪怪的,不知道他是想我和搭讪,还是故作深沉?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不尴不尬的折磨,就又硬着头皮问他:“你也是糖尿病?”他迅速地回答:“甲亢。”他的回答有气无力。我笑笑称:“我们两个的病刚好相反。”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他。完了就再也没有话了。我有些讨厌这个家伙了,有什么牛逼的,不就是一个“病人”吗?后来护士进来了,问他话的时候,他也是爱理不理的。小护士也是见得多了,见怪不怪。医生查房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他老婆和医生的一段对话,得知他不仅是“甲亢”,还有代谢综合症、轻度抑郁症的病史时,我心里的一切也释然了。一个“病人”,遇见了另一个“病人”,惺惺相惜,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九床话少,但鼾声却并不含糊。入夜,这个闷头闷脑的人,倒头就睡着了,他甚至连被子都没有来得及盖好,就酣然入梦。一夜鼾声如雷,鲜有间歇。有时候可能被自己的“喘息”给噎住了,我以为他会就此醒来,有过一刻钟的间歇,谁知这老兄翻身睡去,气喘匀了,扯着大呼,又继续着他的“春秋大梦”。本来就有点神经衰弱的我,这回算是遇着了对手,他持续在一场彻夜的睡眠之中,鼾声雷动,我睁着眼睛,似睡若梦,气不过时,就会用脚狠狠地砸一下床板,或者拿手在床头柜上故意猛敲一下,反正是要弄出一点声响,以中断这个家伙肆无忌惮的“鼾声”。到后来,我倒替这个可怜的“打鼾者”同情起来,感到他的喉咙被什么东西严重堵塞了,每一声喘息都是这样困难,担心他哪一口气接不上,就永远地喘不上来了。
第二天,我赶紧让海笑买了一副耳塞来。从此便不受这鼾声的搅扰,一夜好梦,踏踏实实地睡觉了。
九床依然是不爱说话,但熟悉了以后,表情便温和得多了,脸上的紧张和防范疑云也渐渐散去。夜里,他的鼾声照旧如雷,我却因为一副耳塞的缘故,相安无事,习以为常了。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翻报纸、看杂志的时候,他也会好奇地朝着我这边目不转睛地看。我以为他要看我手里的杂志和报纸,而当我把报纸和杂志放在床头柜上并示意他可以看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看见一样,除了不停地吃东西,就是光着膀子斜斜地躺着,落叶扫秋风般 “喘息”着。他的鼾声时断时续,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哪个时候睡着,又是在哪个时候醒着的。
无意中的一次对话吓了我一跳。那天晚上,我出去办事回来得有点晚,夜里十二点半的时候,我推开病房的门,听他在床上扯呼,便悄悄地睡下了。第二天,我说昨天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呼呼大睡了。他说,没有,你回来的时候我知道呢。我有点懵,难道他是假寐,还是他醒着的时候也打呼?
就这样白天黑夜地被对面床上的鼾声“陪伴着”,我似乎已经很熟悉了病房里的生活,甚至在我拿下耳塞的时候,我的心脏也会随着另一个病人的鼾声起伏着呢。
每天早晨,五点,还是六点的样子,我就醒来了。我已经不再害怕被对面床上鼾声打搅。我打开电脑,旁若无人地敲击下这些文字,为我在人世间拥有的这一间病房,为另一张病床上的鼾声和睡眠,也为我自己的这一张病床上,短暂的安歇和遐思,感恩,并深深地祈祷。
郁苗和郁简
入院的第二天,按惯例,做一些和糖尿病相关的检查。这是医生的要求,也是我个人的意愿。这次来住院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必要的检查,看看自己身体里的血糖,到底达到了怎样一种不可遏止的程度,还有就是担心这几年的糖尿病,有没有引起并发症。我这四十多年的身体,已经足够疲劳了,这架身体里的老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了四十多年,有些部件出现了问题,这是正常的。俗话说人不是钢铁,就是真正的钢铁,四十多年了,也早已经到了该检修的年龄了呀。
头天晚上,值班的护士就反复地给我讲了,明天早上不要吃饭,空腹检查。我也谨记心头,可是第二天早上,等护士过来抽完了血,我以为就万事大吉了。顺手倒了一杯开水,喝了,觉得意犹未尽,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一根黄瓜,在水龙头底下洗了洗,咔哧咔哧地嚼起来。路过病房的护士见我一大早举着根黄瓜,有滋有味地嚼着,用诧异的眼神望着我说,叔叔,今天早上你不是空腹做检查吗?怎么一大早就吃起东西来了?我若无其事地回答,已经抽完血了。小护士不解地问,要去做B超呢,还没有上班,怎么就完了?我这才恍然大悟,有负小护士的一片热心不说,这一个晚上的“空腹”,算是白折腾了。
后来问了主管医生,我说只吃了根黄瓜,能不能继续做检查?医生笑着问我,护士昨天晚上没有给你讲清楚吧?我怕把这个责任推到护士的头上去,连忙说,护士说清楚了,交代了好几遍,是我自己理解错了。医生说,那就先做不需要空腹的检查吧,明天早上继续“空腹”。
就这样,我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病号服,混迹在一群皱皱巴巴的病号服中间,像一个真正的病号一样,来到医院的体检中心。多年来,我都是一个自我怀疑主义者。在乌鲁木齐生活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一次身份的转化,都会让我产生一些怀疑和犹豫。比如退役后,第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我就怀疑自己的这个市民身份是不是真的,老是担心哪一天,会被发现是哪些方面审查不严,或者哪一个环节上弄错了,使自己错误地拥有了这个城市的户籍而得到纠正,重新回到自己的那个小村子里去。后来报社给我分了一套房子也是这样,搬进去住了好长时间了,老是怀疑这套房子不是自己的,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收回去了。这种来自于自身的怀疑和犹豫,使得我在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错觉:你暂时所拥有的,不一定就属于你,所以要小心地看护好了,谨小慎微,别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个“自己”,不小心给真的弄丢了。
人生如戏,我们都是人生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演着演着,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回不来,世界也回不去了。
我坐在走廊里的一排椅子上,等待着被叫号。恍惚中听见一个女高音重复地叫着:郁苗,郁苗!叫了好几遍都没有人答应,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是不是在叫我呢?连忙冲过去问,是不是在叫我?你是谁?埋头于一堆检验单和计算机屏幕间的女大夫问我。我是郁笛,是不是你刚才念的那个郁苗?女大夫拿过刚才那个单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谁把笛字写得跟苗一样。说着,她顺手在我的名字上用笔改动了一下说,好了,到对面的房子做检查。
我接过单子,一路小跑来到对面。我怕自己耽误得太久,又要重新排队了,等我单子交到另一位做心电图的大夫手上时,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我坐在走廊另一侧的椅子上,等待着再一次被叫号。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拿着一摞单子出现心电图室的门口,她不无温柔地喊道:郁简。有了上一次被叫成郁苗的经历,这一次我比较警惕,连忙起身跑过来,纠正道:是不是郁笛?女大夫认真地看了一下单子,小声地重复了一遍:郁笛。
等到我躺在床上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这一个上午,分别被叫作郁苗和郁简的那个人,难道就是我吗?人这一生的历史,如此短暂,却有无数种可能会被改变。古往今来,我们像一粒尘埃一样漂浮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别人也找不到。你在世界上的这个符号,别人也早已经无数次地用过了。我们只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如此小的范围内使用,并暂时地拥有着自己的这个“符号”而已。所谓“名垂青史”、“千古流芳”,那是一件比死亡更难以企及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也生活在另一个更加虚无的幻象世界里。
所以,不管是郁苗也好,郁简也罢,我都是欣然接受的。因为在我看来,人海茫茫,浮世无边,我的身体和灵魂早已经四分五裂,各自奔赴在不同的路上,并不属于“郁笛”这个浪得虚名的家伙独自拥有。
我的血和糖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血液里糖多了?糖尿病这个病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铭心刻骨。最为困惑的是,医生问我家族和父母有没有什么疾病遗传史。我一下子想起了离开人世的父母,一个人飘泊在外这么久了,临到了疾病,还要到父母那里去找一些缘由吗?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忆,他短暂的一生得过什么病,就像他的身世一样,是我一生的谜团。母亲一辈子被疾病折磨,她是多年积劳成疾,我仅能记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让她的晚年,从来没有直起过腰来,她把腰弯得像一张弓,每每走起路来都要气喘吁吁,不管和谁说话,先要把头仰起来,那种艰难的喘息和咳嗽声,深深地刺痛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告诉医生,这就是我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疾病信息。
我知道,医生需要的不是这些。
小的时候家里穷,吃不饱饭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的疾病大多和饥饿有关。后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我在童年时代对自己人生的预测,也完全脱离了我梦想的边界。这些年,毫无顾忌地吃了那么多,喝了那么多,这和我的血液里的“糖”有关系吗?有人说糖尿病是吃出来、喝出来的,这话说得当然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吃喝都导致血糖的升高。而一个人的代谢功能,最终还应该归结于一个更复杂的精神系统。
想想被查出血糖有问题的那一年,应该是2007年的夏天。例行体检,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叫住我说,血糖高了,住院再好好地查一下,可能是糖尿病。我有些恐慌,但并没有以为自己真的就是糖尿病,因为连医生都说“可能是糖尿病”。接着住院、检查,几乎把所有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也在医生的指导下把血糖控制下来了。那个时候,就被医生告知说,糖尿病已经可以确诊了,但又没有达到“医保”确定的“慢性病”的标准。我不明就里,也一直心存侥幸,以为身体里的这一场劫难,应该在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我过了一段小心谨慎地日子。少食、清淡、无糖,开始是戒酒,后是少量饮酒,最后是偶有大醉。有一段时间,明明身体发出了警报和信号,但是停不下来了,每一场酒,总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微醺最好,大醉无妨,早已经把血糖的事情忘得一乾二净。
想想看,酒这个东西,真的比魔鬼还要魔鬼。你不去碰它,什么事情都没有,你若惹了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酒桌上,你不端杯子,有人去替你怀念那些豪饮的历史,说喝一杯又死不了人,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有些人声泪俱下,举着一杯酒说,这就是一杯毒药,兄弟你今晚上把它喝了又能怎样?你一听这话就没有了退路,赶紧喝了吧,不就是一杯酒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不了的事情是,天底下没有千杯不醉的事,酒桌上的话,半疯半癫,过后没有几个人会把它当真。所谓酒逢知己,那真是酒桌上最好的借口了。我相信在许多时候,从酒桌上下来,血糖就跟着上来了。我也曾经无数次地发誓,再也不碰酒了,可是,每每被怂恿着,不由自主地又端起了杯子。美酒穿肠,喝声一片。你端了第一杯,就会有第二杯、第三杯等着你。所以经常醉酒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把自己给灌醉的,没有人非要强迫着你,无非是你的耳根子软,经不住劝,说得好听一点,你心地善良,不忍心薄了劝酒人的面子,宁愿拿自己的身体和性命抵押,也不能在酒桌上塌了场子。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还没有血糖问题的时候,我会在酒桌上称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喝酒。别人就问,你有什么病?身体壮得像头牛!我接着说,有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慢性前列腺,别人一听就大笑一片,知道我这是为不喝酒找理由,胡咧咧呢。也有人把这当作成酒桌上的段子,当成笑话一笑而过。殊不知自己糟蹋自己,就是为了少喝一杯酒而已。
酒喝多了,血糖自然就会升高,这是多么浅显的“硬道理”。可是这么多年,我硬是把这样的“硬道理”给软着了路。当然软下来的,还有自己的身体。
我是一个吃过苦的人,但却享受不了自己身体里的“甜”。我的身体里每天携带着这么多超标准的“糖”,却要忍受着“尿糖”的痛苦。但是我知道,快乐不会因为“糖”而减少,痛苦也不会因为血液里的“糖”而变得更多一点。
需要再次声明的是,戒酒了!在“血”和“糖”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我的生活之前,我希望自己血液里的“糖”,来得慢一点,再少一点吧。
“杯具”变成了”悲剧”,人生的这一场酒,我已痛饮多年,到了该歇歇的时候了。
护士课
内二科的护士们,大多年轻漂亮。可是住进病房好几天了,来来往往的护士们,我一个也没有认得下,她们清一色的护士帽下面忽闪着一双青春的眼睛,然后是清一色的大口罩,然后是清一色的长长的工作服。有时候,我能够辨别出她们的声音和脚步,却永远也记不住她们的名字,虽然她们的名字就挂在胸前的工作牌上。我只是记住了那些浅浅的笑,并不是仅仅因为青春而美丽的声音。有人把她们比喻为天使,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我穿上病号服,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来来往往的护士姑娘们,一口一个“八号”叔叔,叫得亲切而又自然。仿佛“八号”这张病床,就是为我准备的。我的命运和我的疾病,在这里以“八号”的名义被修改和注射,被以药片和液体的形式注入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个有病的人,被重新编号,进入到一个由护士们管理的病号服的序列,就暂时没有了你的社会属性,什么科长主任、老师教授,在这里,只剩下一个统一的编号。护士们理所当然地唤着这些编号,给你发药,给你注射,给你量血压、测体温。同样,这些编号的下面,是有血压和体温的沉重的肉身,他们因为身体或者心理的疾患,被统一地编排在这些秩序井然的号码序列里。
我们常常说到医院里来,是来看医生的,实际上,你住在医院里看见最多的,是这些进进出出的护士们,而不是医生。一天之中,你在病房里看见医生的次数总是有限的,而护士们却不是这样。她们频繁地出现在你病房里,在你的全部疗病过程中,是她们代表了医、药以及整个的医疗系统,对你实施最有效的治疗和护理。可以这样说吧,是护士们职业的微笑、细心的体察,最真切地安抚着你的疾病和疼痛,即使她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医生的嘱咐和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有意否定和忽略医生对于病人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疾病,也都是经由医生的诊断和发现,最终走向治疗之路的。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护”和“医”是互为依存和不可替代的。
我住院的这几天,医院里好像来了一个工作组,随时都有可能要到病房里来检查。这可忙坏了护士们,也搞得气氛有点紧张。有一天上午,我刚躺在病床上准备输液,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拿着一个小本本进来,问我说,八号叔叔,你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吗?我说糖尿病呀。那你知道自己的主管医生和主管护士都是谁吗?我说我的主管医生好像是梁医生吧,主管护士,是那个段玉玉吗?见我回答得含含糊糊,小护士有点着急了,她不无娇气地说,叔叔,不能这么犹豫的,要记住了,不然,检查组要扣分的。我恍然大悟,连忙说,对不起姑娘,你继续问,我一定准确回答。小护士也跟着笑了。她继续说,那我再问你,你知道现在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饮食吗?我想了一下回答说,糖尿病人的饮食!显出一分得意的表情。小护士又急了,她不停地用笔敲着手里的小本本说,大胡子叔叔,准确地回答应该是清淡、无糖的饮食,一定要记住!我有些意外她这次没有叫我“八号”,而叫我“大胡子叔叔”,连忙点头如捣蒜,向她保证,检查组来的时候我绝不会出问题。
看来我的回答,小护士还是满意的。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病房的时候,我也自作多情地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护士姑娘,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在我这张病床的正上方,天花板上有一只去年的苍蝇站着不动,不知是死的还是活的,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把它给弄下来,要不然我看着闹心,检查组来了,也影响环境呀!听我这一说,病房里的人全都笑了。小护士笑着扬起头来在天花板找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看见,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便笑着说,检查组不查这一项,扭头出去了。
其实这只“苍蝇”是存在的,或者它是另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昆虫。我躺在这张病床上的第一天,这只张开翅膀的昆虫就在那里了。它张着翅膀,在天花板上一盏吊灯的旁边,欲飞不能,仿佛被凝固的一个标本。我凝神地看过很久,曾经以为是一只带翅膀的昆虫暂时停留在这儿,可是好几天了,它一直没有飞走,它一动不动地被固定在天花板上了,那一双翅膀上落满了透明的灰尘。我想把它赶跑,或者用一根竹竿把它轻轻地拨下来,可是我无能为力。
世间万物,一草一木,都会有终了的时候。而一只昆虫,为什么会在那样高的地方终止了飞行?每一天躺在床上,只要一抬头,我就会看见那一双张开的翅膀,没有被它带走的时间和方向,在那一刻的天花板上,停留着。
小护士的功课做得好,却独独忘记了天花板上的这一只昆虫,和它张开的翅膀。
身体里的黑暗
夜已经深了。寂静也像一些梦中的黑夜,影影绰绰。对面九床上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几次欲从梦中醒来,挣扎着,还是放弃了。就这样若梦若醒地不知道躺了多久,等到我彻底地睁开了眼睛,房间里微弱的光亮,恰好遮挡了对面九床上那一张熟睡中的脸庞。这是另一个人的睡梦和鼾声,而我却醒着,这两个命运毫不相关的人,拥有着同一个黑夜里共同的病房。这多么像一场密谋,被不同的疾病追赶着,星夜兼程。
我想我是做着一场梦的。黑夜里的恍惚,使我无法转过身来。我又一次梦见了三年前去世的母亲,她的前世般的悲苦和愁容,是我一生的梦境里无法摆脱的阴影。这才是我终生的疾病,身体里的故乡,一生的命运中无法抛弃的黑暗。
昨天去了眼科,做“眼底造影”,需要吃一片药,点上眼药,闭目,等待瞳孔散开。正常情况下,半个小时足够了,医生说我的血糖高,瞳孔散得慢,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按照护士的交代,点上眼药之后,就不能再睁开眼了,否则,瞳孔散不开,就白耽误了工夫。
为了保证检测效果,点上眼药后,我就被陪同前往的金虎兄弟扶着,来到走廊里的一处长椅上坐下,等待着瞳孔的散开。我努力闭着眼睛,不让一点光线从眼睛里穿过,并用心体会着这黑暗中的一切。金虎怕我寂寞,总是在不停地给我说着话。我们从他的一部中篇小说,聊到了乡村的老家,又从他作品中的方言俗语,聊到了我们即将消失的乡村记忆。
由于不能睁开眼睛,不需要目光的交集和会意,我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得以一个人沉浸在时间的黑暗之中,思绪随着话题的飘移,轻易地就能够进入到自己黑暗中的想象或者记忆里去。一个人处在黑暗中之中,感觉世界的色彩都放在了别处,往事飘渺,忽远忽近,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停靠的中心。我几次想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被自己假设的世界,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我也有意想让自己,在这个漆黑一团的幻象世界里,多停留一会儿。
记得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人》,说的是城市盲道被肆意挤占,而大多数眼睛明亮的人,无视盲人的基本权益。那个时候,我完全是一个不需要体验“黑暗”的人,我是用自己的光明,来揣摩别人在“黑暗”中的行走。今天,我却需要在这短暂的“失明状态”里,还原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在眼科医院的走廊里,你才可以遇见那么多患有“眼睛疾病”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都闭着眼睛在说“瞎”话。闭上眼睛之后,你才发现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如此嘈杂,那些操着四川话、甘肃话和河南话的人,一定还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还有另外一些我听不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环顾四周(对不起,这一刻我闭着眼睛,已经无法环顾了),试图从这些混杂的声音和缝隙里,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落脚的地方。我发现这是徒劳的。我身处在自己身体的黑暗中,到处都是语言的漩涡,我无法抽身,也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这个嘈杂的世界里全身而退。
因为闭上了眼睛,耳朵里便灌满了各个方向的声音,一时间无从辨别,不知道把自己的声音存放在哪里。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似乎是至理名言,大意是说,上帝给你关闭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也是蛮荒谬的。你想想看,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窗户就是窗户,难道还能当门用吗?她给关闭了一扇门就是一扇门,跟窗户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了门,只能爬窗户,这是被逼无奈的事情。
人有很多路是走不通的,最后总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我们绕不过命运这道坎,便饶舌般地给自己编织了那么多谎言,貌似在安慰别人,其实全是在欺骗自己。那天做B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无意中瞅了一眼操作中的计算机屏幕。那一眼,着实把我吓得够呛——我看见的,是一个让我如此陌生的自己。这些来自身体内部的影像,黑暗中的蠕动,犹如肥沃的土壤,那一片血肉模糊的原野上,沟渠纵横,山脉相连,竟然也是一个如此气象万千的完整世界。
想一想,我们生活在多么真实的黑暗中。我们总是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更知之甚少。等到身体病了的时候,才需要打开自己,装做无辜的样子来请求疗救,就像拯救一片山河破碎的国土,等到大面积地沦陷了,多半已是家破人亡,一片焦土。所以疾病中的人,对身体是盲目的,医生也只能按照我们身体的意愿,来归还我们一部分健康,完全的康复,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绝对的健康,在谁的身上都不会存在。
人的恐惧据说大多来自于黑暗之中,而我们往往会来到在这样一些缺少光亮的夜晚,在不为人知的“黑暗”中,举着一根命运的火把。
植物园
从空军医院的北侧一个小门出去,穿过一条坑洼不平的马路,就是植物园高高的铁栅栏上,爬满绿色植物的“院墙”了。往左走上十几米,是乌鲁木齐闻名已久的北京路。早在二十多年前,北京路就以其路面宽阔、双向通行,道路两侧的树木整齐、“植被”茂密而为人称道。
我居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对北京路以及北京路一带的小区和街道并不熟悉,也对诸如植物园这样的“城市绿地”,多年来也只是心存向往,踏足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住在空军医院,可谓近在咫尺,心里就想,一定趁这次住院的机会,到这向往已久的园子里好好地走一走。
没想到这机会说来就来了。昨天下午,九床被他的爱人转到了隔壁的另一间病房里去了。海笑过来的时候,看见病房里空出了一张床,就说她晚上不想回去了,在病房里陪我住上一晚上。这样,我们就有了晚饭后的一段闲暇时光 ,穿过那条窄窄的马路,沿着北京路这一侧高高的“植物院墙”,寻找到了植物园五元钱一张的门票。
这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一团泼墨般的夕阳,把城市的天边,染成了一片遥远的火焰。而植物园里的安静,也是我所想象的。虽然夕阳那一团火焰远在天边,她的光影和温度,还是在这个傍晚,恰到好处地镀亮了植物园里每一条幽秘的小路。花影摇曳,树叶婆娑,在春天还没有彻底结束的时候,植物们就已经率先来到了夏季。
傍晚的阳光,是最适合用来散步的,只是,在这个季节里你看不到落叶般的黄金,你满眼的花香,或者已经残了的花瓣。一小片又一小片金色、白色、粉色和红色,或者紫色的花朵,被一阵微风吹了,摇头晃脑的,像一群群开花的少女,摆动着裙裾,傍晚的树荫下面,便多了些无声的歌者。
草地上,树叶上,甚至这些行人稀少的林间小路上,恰好是刚刚被昨天的一场雨水洗过的,洁净的花香,和青草的气息,弥漫在这个园子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来到一大朵盛开的白色芍药面前,看她薄如蝉翼的花瓣在枝头颤抖着,海笑说,怎么像假的一样啊,这么大的一朵花,仿佛是被安放在花池里的盆景。
远远地看见一些树木,都似曾相识,却叫不上名字。什么高大的樟子松,幼小的山樱桃,我想我都是见过的。我出生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就在山野里长大,那些漫山遍野的植物和原野上无名的花朵,塞满了我苦涩而又不乏快乐的童年记忆。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远离土地和山野的自然主义者,却原来,我是并不熟悉植物的。
一些植物让我觉得陌生,或许是它们来自异国他乡的缘故。那些南美和欧洲大陆的高大植物,就像一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样,站在一群和风细雨的海棠果和杜子梨的旁边,显得有些扎眼睛。
我们还不能责怪这些被移植的“外来物种”,其实我们谁又不是这个世界的“外来者”呢?四海为家的人,哪一片土地都是异乡。我这样想着,也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天涯客旅,也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我抬头看了看西边的天空,夕阳落尽的时候,那一片“最后的光芒”,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最终砸向了一片参差不齐的楼顶。我看得出奇,觉得这末日般的辉煌,怎么这么近呀。
这时候,我坐在一汪水塘边的石头上,看见脚底下的这一汪浅浅的水里,一只小鸟在不远处快乐地“戏水”。一只麻雀大小的类似于喜鹊的小鸟,它先是在水边尝试着“吃”了几口水,觉得不过瘾,便忽闪着翅膀往深处走去,进而将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试图将整个的身体都浸到水里去,终是由于胆小或者其他缘故,只是湿了大半个身子在水里抖动,细小的水花,溅落一圈圈涟漪。它顾不上这些,只是腾地一下从水里蹿起,贴着水面,一个弧线飞到了一块从湖水里探出头来的石头上,左顾右盼,惊动了另一只独自在浅水里饮水的小鸟。被打搅的另一只小鸟不耐烦了吗?它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这位不速之客,有点厌烦地伸了伸脖子,一定还用鸟语骂了几句,心有不甘地又低头喝了几口水,一个扑棱子飞身走了,沿着茂密的树林,去了云深不知处。
一只小鸟飞身离去,消失在夕阳陷落的那一片天空。我以为留下的这一只小鸟,可以安心地在水面上“游戏”了,可是它只是犹豫了片刻,在水面上盘旋一圈,飞走了。我还以为,这是两只毫不相干的鸟。只见后面的这一只小鸟,在树林上空绕了一圈,便沿着前一只小鸟飞过的路线,弯弯地飞过去了。我有一点意外的兴奋,一种发现的喜悦——两只小鸟,一弯浅水,倦了的云朵,乘着夕阳归去的夫妻鸟。多么微小的爱情,在这个傍晚的夕阳里飞翔。
这一汪水,重又恢复了平静。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吃惊地发呆。这是昨天晚上的那场雨留下的水吗?或者是去年的一片“湖底”?浅浅的一汪水,照见了一对鸟儿卑微的生活里全部的快乐和幸福。
这时我才想起了起身,看见海笑举着手机,在不远处的一片李子树下,不知道是在拍照,还是在记录着什么。夕阳的最后一点点辉光,已经完全被园子里的树影给遮挡了。
亡 者
隔壁病房的一位病人走了。夜半,走廊里传来了一片混乱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凭那悲声里的哭诉,渐渐地,哭声渐稀,只剩下了一个女人的悲恸怎么也止不下来。我听清楚了,这是一位女儿的泣不成声。她反复不停地哭喊着“爸爸”,被一些同样悲切的声音搀扶着,孤单和无助的声音穿过厚厚的墙壁,在门外的走廊里凄凉地回荡着。此刻,悲伤击垮了这个夜晚的女儿。
我看了看表,时间才刚刚凌晨一点多。我不知道这位离去的父亲有多大的年龄,他是一位老者还是英年早逝?死亡这样一件事情,终究还是来临了。此刻,除了女儿一个人在这个夜晚里的失声痛哭,偶尔的劝慰,我可以想见的是,走廊里一片死寂。内二科所在的这一层楼,几乎住满了病号,大概这样的死亡和来自夜晚的哀号,没有人是听不见的。大家用共同的沉默,表达了对这位亡者的哀悼和送别之意。
曾经,这个和我们穿着一样的制式病号服的男人,在走廊里散步、打开水,按照护士和医生的要求,按时吃药,被年轻的护士量过血压、抽血化验。一切都做过了,他曾经等待着康复。他生病的这个季节,春天刚刚过去,夏季的雨水刚刚拍打过他病房的窗台。他想着,病好了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风和雨水的声音,也一同带回去,撒在自家的花盆里,颐养天年。
可是死亡夺走了他生活的计划。我想象着这个放弃了生命的人,他的被亲人的悲声裹挟的魂魄,此刻还没有离开自己温热的身体。在死亡到来的时候,他挣扎过吗?他是否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为继续活着争取过?他心有不甘,还是意犹未尽,风风火火地活了几十年,就这样一撒手,什么都放下了。
我住进来没有几天,可是这些天一直相安无事,并没有听说有病危的病人。刚才护士进来给我测血糖,问我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睡?我说已经睡醒了一觉,被刚才的哭声给吵醒了。小护士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知道她说的习惯是什么意思,医院里死人的事情,司空见惯吧。我忙问她,死者多大年纪?她不无惋惜地回答,四十多岁吧,不到五十岁,癌症晚期。
小护士测完血糖走了,我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想想在这个夜晚的隔壁,撒手而去的那个男人,任凭女儿无助地哭诉,他已经没有办法给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女儿任何一点生命的安慰了。他曾经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吗?他的曾经的疼爱和呵护,此刻正加剧着女儿的悲伤和绝望。爱,是不需要偿还的,而她却加重了另一个人悲伤的分量。
一阵纷乱的脚步声过后,走廊里又恢复了平静,仿佛死亡还没有发生,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了。这时走廊里有了零星的脚步,有小声说话和议论的声音,其实整个夜晚,这个走廊里都不会安静下来。突然到来的一次死亡事件,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夜晚的脚步。
经历过死亡的人,才会懂得珍惜生命。活过了一把年纪之后,看着那些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亲人、故旧,在你的身边曾经那样健康地活过的人,一不留意就撒手了,你甚至还来不及挽留,一切便都成为往事。有人说,生死两茫茫,一场空欢喜。人生当然不只是一场空欢喜,但是太多的牵绊,终究还是要放下的,往往一生的累,只是一场空也为未可知。
终于安静下来了。我站起身来,探头望了一眼窗外的夜色,风摇树影,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看见。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像是坏了,总是在不停地滴水,一刻也不停,滴滴答答,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坐在病房里一筹莫展,想着被刚才的那一场哭嚎掠走了的睡眠,竟然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一场死亡的仪式刚刚结束。在这个陌生的夜晚,一个陌生的人走了,去了我们谁也不知道的远方。
我知道这样的黑夜里,死亡其实只有一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