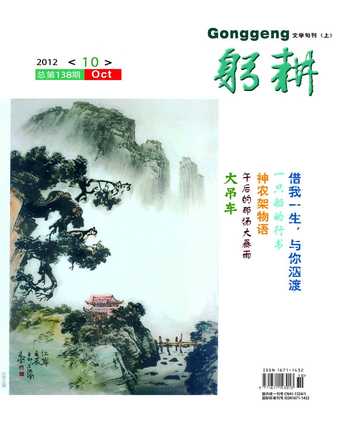王开林随笔
王开林
1965年出生于长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非常人,非常事》等十九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三百种散文、随笔选本和年鉴。获海内外多个文学奖项。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
真作家:勿以字数骄人
文人爱吹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本来无可厚非,但要是某某某将娱乐精神超水平发挥,吹嘘得过于离谱了,他就很可能会沦为笑柄。
有一位著名评论家曾在某省卫星电视上夸下海口,声称自己总共阅读过十万册文史哲书籍。此公四十岁出头,若从六岁算起,阅读史充其量不过三十余年,他必须平均每天浏览十本书(每天阅读十本书近乎扯淡,除非是小人书,除非他不吃饭,不睡觉,一目十行),才能接近那个天文数字。难怪这位著名评论家话音刚落,现场的观众已是一片哗然。那位评论家的小学算术没学好,观众可不愿自己的智商被低估。
作家的《个人简介》是个值得玩味的东西,某些主观夸饰的部分非常逗人。比方说,有的人,不仅在简介中,而且在名片上,也敢标榜自己为“国家一级作家”,这个名目确实很让读者抓瞎。它是一项荣誉?就该有国务院颁发的证书,事实上并非如此;它是一种职称?也不对头,全国各行各业的职称多多,绝对没有哪种职称可冠以“国家”字样。这顶“帽子”太大,任何“脑袋”都嫌太小。那么,就不难断定,某些很不老实的文人对此名目做了易容手术,它原本是文学创作系列的一项职称,全名为“文学创作一级”,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出版部门的“编审”,新闻单位的“高级记者”,只不过它的含金量更低,含水量更大。在有的省级作家协会中,除开行政人员,几乎都找不到职称不是“文学创作一级”的作家了,有人早就建议这样的省作家协会应更名为“省一级作家协会”。黑色幽默太多,此为一桩。
在作家的《个人简介》中,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内容,那就是有的作家喜欢注明自己曾创作了“若干万字”。在某些擅长夸饰的作家笔下,“数百万字”并不充饥,“一千余万字”才勉强打个饱嗝。
在外地开笔会时,我就碰到过这样的狠角色。一位不到五十岁的作家在饭桌上夸口说,他的创作总量是两千万字,我当场就被吓了一大跳,心里却直犯嘀咕。后来,我私底下问他:“你知道鲁迅一生总共创作了多少万字吗?”他没仔细过一过脑子,估数为四五百万字。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梁启超一辈子留下了多少万字的著作,他诚实地回答:“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告诉他:“梁启超著作等身,是中国近、现代最勤奋的大文豪,他一生焚膏继晷,满打满算也只写下一千四百余万字。”我这样说过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后来,我留意到,这位作家确实有所收敛,在《个人简介》中主动将自己的创作总量由两千万字缩水为一千余万字。这个数字仍旧十分惊人,可他总共才出版三四本书,加起来不足一百万字,离著作等身还差一大截。
才华横溢的作家多半生性散漫,勤奋实属不易。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尝言:“今天应该写得多,因此应该写得快,但要快而不急,因此要弹无虚发,颗颗必中。要写得快,就要多想,散步时,洗澡时,吃饭时,甚至约会情妇时,都要想着自己的主题。”这句话强调的,并不是字数,而是“弹无虚发”,即写得好。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和他的文艺美学论文集都是世界名著,这说明他写得好,但他的创作总量并不高。法国文豪、思想家萨特在他的自传《文字生涯》中有一句名言:“每日必写一行。”他强调的是写作的连贯性,他认为,于写作者而言,中断写作有损无益。至于字数多寡,他并不在意。钱钟书先生特别反感多言费词,他曾说:“半克微言胜过万吨废话。”诚然,智者看重的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是谈言微中,于会心处,拈花微笑,甚至不发一声。便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世间确实有雨果、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大文豪,他们写得多,也写得好。但这样高质高产的文豪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作家就算写得多,也未必篇篇皆佳构,部部是精品,能够流传后世的著作就更是百不得一。我曾听一位同辈作家感叹道:“乾隆皇帝一生‘杀诗四万余首,产量接近《全唐诗》,可是将它们捆起来也抵不上王之涣的那首五绝——《登鹳雀楼》,区区二十字就胜过乾隆皇帝一生涂鸦的海量的文字垃圾!”这句话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作家必须写好了,才有底气,才有资本,若单纯以字数骄人,是毫无说服力的,只会贻笑大方。
玫瑰的传说
被过度滥用的玫瑰,唯有我能理解你无法遏制的愤怒。
以“爱”的名义谋杀高贵的花朵,谁还能做出比这更自鸣得意的事情?且看,不知爱为何物的女子得到了她本不该得到的玫瑰,立刻报以愚蠢而又满足的微笑。她的确应该万分庆幸啊!得到了完全不相称的赞美;然而,天知道,她要遭遇的不幸究竟将会有多大?
想以玫瑰谋取爱情的人,绝大多数都只能收获那些一开始就被忽略了的利刺。这是天大的嘲讽,还是屑小的玩笑?玫瑰自有玫瑰的幽默,没有几个人真正明白这一点。发动玫瑰攻势的男人,自己的城池先已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绝大多数女人竟然相信这样的虚弱和滥情正是不可多得的优雅!
一生被玫瑰击伤和灼痛多次而终告不治的女人至死不悟,她们还在等待另一枝玫瑰应运而来,另一个奇迹如期而至。结果可想而知,无数心碎的女人都在重蹈覆辙。
难得的不是玫瑰,而是爱情,满街满市都有鲜艳的玫瑰标价出售,而爱情只在极少数人的心中才得以幸存。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黄金国度,有一座一望无际的玫瑰园。在那里,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莫过于玫瑰节。从千万朵玫瑰花中挑选出最灿烂最芬芳的一枝,由国王亲手颁赐给一对至诚相爱的情侣或白头偕老的夫妇,获此殊荣者将成为黄金国度里最受尊敬的公民。你可能会问,他们怎么处置其他的玫瑰花呢?为了显出那朵至尊玫瑰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其他的玫瑰全部用于榨制玫瑰香露。在偌大的黄金国度里,有偌大的玫瑰园,然而,最幸福最幸运的人(包括国王和王后),一生最多也只能得到一枝采自花园的鲜艳的玫瑰,唯其如此,玫瑰才无比神圣。
后来,有一位大富翁千里跋涉到黄金国度去旅游,参加了万人空巷如痴如醉的玫瑰节。他感到大惑不解,得到一枝玫瑰有什么可特别荣耀的呢?但他极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他坚信自己的原则:金钱能够买到一切。
他快步走近那对刚刚从国王手中获取至尊玫瑰的情侣,表示自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买下他们手中的鲜花,要知道,是任何代价。然而,那对情侣好不容易才听懂他的话,他们仿佛被蝎子和毒蛇狠咬了一口,神色骤然大变,脸上露出世人通常只有遭到极端侮辱后才会露出的极端愤怒的表情。那位美丽的少女将玫瑰紧紧护卫在胸前,那位英武的男子右手则猛然按在腰间的剑柄上。
“莫非你不是黄金国度的公民?居然不知道玫瑰是至高无上的非卖品!可鄙的商人,在我拔出利剑之前,赶紧从这里自动消失。否则,明天你就没有舌头可以向别人开价了!”
听了这义正词严的呵斥,那位富翁直吓得屁滚尿流,在一片嘲骂声中灰溜溜地逃跑了。但他仍未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偷偷地找到玫瑰园的主管,敞开自己的钱袋。这回他如愿以偿,他得到了玫瑰的种子。
富翁回国后,很快就开辟出自己的玫瑰园,比黄金国度的还要大上一百倍。从此,玫瑰的价值一落千丈,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黄金国度的玫瑰园很快就凋敝了。
玫瑰的泛滥,同时导致了爱情的泛滥,尽管玫瑰的象征意义至今还在,情人节尤其少不了它的款款登场和频频亮相,但尽人皆知,玫瑰已不再代表爱情至高无上的荣耀。
曾用心护卫过的玫瑰,用剑护卫过的玫瑰,如今,它在夜色中呼救,已无人理睬。黄金国的玫瑰园离我们遥远而又遥远,只偶尔在梦中,我们才得到了那朵至尊无二的极品之花,依稀仍有一缕淡淡的余香。
“记忆中的玫瑰乃是最好的玫瑰。”
我们喃喃自语,两手空空。
苦苦地怀念吧,古典的玫瑰,古典的爱情。
古瓷上的魂魄
人工百器,各尽其用,惟瓷器聚合天地精华,蕴藉人神气韵,鉴明千古,光灿百世,虽至残缺,其芳魂宛在焉。瓷器之为物也,端正而不僵,爽滑而不腻,济楚而不冶,妩媚而不妖,似含情,似解语,浑融一片淑女意态;望之则温,即之则凉,隐隐然又若天生冰雪肝肠一段。
五月晴煦暄和,二、三好友呼引为伴,前往长沙市博物馆展厅,欣赏沉埋地底千余岁而一朝重见天光的唐代珍瓷──长沙窑出土的釉下彩和模印贴花瓷器。选在时间的此端,眺望古人的髓慧心智,纵有千万美景踊跃当前,何可方比?数十品瓷壶尤为精绝,暂且不论其形款姿态尽显泱泱大唐的风韵,单单是上面的题诗,就足以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心弦为之一响。唐代炽盛的诗风可谓空前绝后,当时的诗人比今日的股民还多。工匠相染成习,心痒了,手痒了,技痒了,就老琢磨着要在那酒壶上茶壶上来点意思,可以是耳熟能详的名作,或劝善诫恶的箴言,也可以是自娱娱人的谐墨。总之,既要有情,还要有味,才好。
“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
毕竟是盛唐,到处都有伸展发达的机会。安土重迁的陈腐观念不再可取,男子汉大丈夫自当高飞远集,力图活出点人生的鲜味来。当年,出外谋生的工匠,出门游宦的书生,出关征战的将士,哪个没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试想,无论饮酒品茶,壶上的这首诗旋转过目,他们都会为之血热心动。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这首精致的小诗颇能激人好奇。“君恨”也好,“我恨”也罢,并非两情不悦,也并非外界下挠钩,而是年龄悬殊。到底相差几何?诗中却未挑明。此处之“恨”与“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恨”颇有些不同,出自少女口吻,一个强劲的“恨”字便将惆怅之意拔得更高更峭。倘若换到今天,这样小儿科的问题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只要老头子够有大票子,就不愁热情洋溢的年轻姑娘不来送抱投怀,他固然无憾,少女又何尝有恨?读了这首小诗,冬烘者也会承认,时代是真的“进步”了。
“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
同伴喃喃自语:“洗净铅华,素面朝天,衣香鬓影,巧笑无言。”我接过他的话头,打趣道:“人世间有跨国之恋,有忘年之交,最绝的,还是发思古之幽情。既恨古人不见你,又恨你不见古人,就只能望壶止渴了!”他莞尔一笑,仍痴痴地立在壶前,似乎那是一把魔壶,里面依然藏着那位二八芳龄的少女。
我最喜欢的并非以上这类或豪或秀或雅或俗的题诗,而是那些言浅意深的警句。寥寥数字,仿佛横空飞来,颇有触目惊心之感。
“有钱冰亦热,无钱火亦寒。”
花岗岩脑袋的守旧派不满现实,动辄就嗤“人心不古”,那么古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又如何?
仍是孔方兄为尊钱为大,余皆次之。极端而言,金钱可以重整是非,另立标准。有钱则心热,心热则冰亦热;无钱则心寒,心寒则火亦寒。寒热依人心而升降,人心依金钱而浮沉,这一点,古今并无大异。
“悬钓之鱼悔不忍饥。”
鱼儿登陆上岸,再懊悔不忍一时之饥,已然悔之晚矣。忍饥不仅是一门功夫,而且是一门学问,鱼儿不是牛鼻子道士,也不是气功大师,要它辟谷,怎么可能?再说,它也辨不清何为钓铒,何为天食,只能睁眼瞎似地碰运气。人为万物之灵,趋利之时尚且不知避害,确实因为“饵料”太香,诱惑太大,心一痒,头一晕,就容易犯糊涂。天下无处卖后悔药,真要有,世人倒是可免去一朝之患和终生之忧。
“行满天下善忍恶。”
好副老江湖的口吻。跑的码头多了,吃的亏受的罪足了,郁结于心头的那一股不平之气,能消则消,能忍则忍,消无可消也还得消,忍无可忍也还得忍。纵然是手持青锋,身怀绝技,又能如何?除恶务尽吗?那是武侠小说中主人公常做的清秋大梦,你要是相信了它,天下就数你最为天真。源自老祖宗的中国武术远不如中国忍术那么登峰造极,在上,则为残忍之“忍”;在下,则为隐忍之“忍”。上面愈是残忍,下面就愈要隐忍,于是集古今之大成的忍术理应列为我们的国术。
“行满天下无口过。”
是自谓慎言?还是劝人慎言?抑或主张言者无罪?一生从未失言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也应是寥若晨星。不可与言而与言,谓之失言;可与言而不与言,谓之失人。问题是,你不知道谁可与言,谁不可与言。人心叵测,世事难料,最凶险的莫过于写信做文章,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等着别人来扼喉绝吭。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即可使撰作者万劫不复,一句抗颜犯上的真话必然使吐露者九死一生,言祸之酷烈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按《魔鬼辞典》的释词法,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肯丢掉无益的思想,宁愿丢掉有用的脑袋的那种人”。这就不奇怪了,“大鸣大放”可以玩死那么多读书人。大唐不兴文字狱,老百姓尽可以豁开嘴巴痛痛快快地说话,那样子的舆论自由,如今我辈只能临风怀想了。
浏览展橱中或完好或残缺的瓷器,比浏览《新唐书》的某章某节更多快意,遥感先人的生活,仿佛身临其境。眼前的瓷器即为不死的精灵,那些诗句正是它们美丽的魂魄。
嫦娥应悔偷灵药
今年中秋的月亮不是圆在十五,圆在十六,而是圆在十七,这多少会使人生出点异样的感觉。我站在楼顶抬头望月,在脖子酸痛之前,想起了后羿和嫦娥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原本就是奇奇怪怪,众说纷纭的。
我个人比较偏好这样一个版本:后羿与嫦娥贵为天神,是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来到人间。这项使命就是射日。当年,天上的太阳多到十颗,炎炎烈日把庄稼都烤焦了,人畜万物如同生活在炼狱之中,生不如死。后羿挽强弓,连发九箭,箭箭命中靶心。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刚刚好,万物得以幸存。后羿成了人间的英雄,他的同行,那些仍在天上安享清福的各路神仙耳闻他威震寰宇,都嫉妒得鼻歪眼斜。一时间,谗毒纷起,天帝偏听偏信,后羿从此被贬落人间,神册永不叙录。
后羿有美妻相伴,打打猎,教教徒弟,就算不返回天宫做神仙,日子照样过得快活滋润。无奈嫦娥不安于室,她更喜欢仙界的生活。嫦娥要设法离开人间,她记得王母娘娘曾赠送给后羿几颗长生不老的仙丹,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于是她翻箱倒柜,把它们找了出来,囫囵一下全吞到肚子里去,全然忘记了王母娘娘当初千叮万嘱的用量和用法。结果是,嫦娥体内骤然产生了无法自制的飞升的冲动,轻易拥有了腾云驾雾的法力。但她找不到北,这冲天一飞,偏离了方向,径直飞到了月亮上的广寒宫。
人类登月的历史,理应提前数千年,这并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论。中国人嫦娥乃是第一个登月的人,而且她没借助任何飞行器,比美国阿波罗号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于1969年7月16日借助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不知要神奇多少亿万倍。只可惜,当年的录像技术没能同步跟上,否则,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就不只是“四大发明”那么简单了。
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嫦娥有名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前提是,嫦娥深爱后羿,夫妻不幸两地(更准确地说,应是两球:地球和月球)分居。嫦娥的药劲一过,当即后悔,把肠子都悔青了,后路却戛然而断,已丧失飞回人间的任何可能。再说,就算她能飞回去,作为凡人的后羿也早就被人杀害了,她为他守寡,悲情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了。
嫦娥奔月的传说太过离奇,编造的人很有想象力,值得佩服。但我怀疑,嫦娥是一位极聪明的文学女青年,她偷吃的不是王母娘娘惠赠的灵药,而是类似于海洛因之类的毒品,立刻产生了很厉害的幻觉。待到药劲醒透,嫦娥的神情恍恍惚惚,于是她编出这么个神话故事,大家听了觉得好玩,立刻传得家喻户晓。
另有一个版本说,后羿不是天神,他是夏朝开国君王夏启(大禹的儿子)的军事大臣。他逐走了夏启的长子太康,扶立了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这一貌似正史的记载同样是没根没据的传说。至于杀死后羿的人,一说是寒浞,一说是逢蒙,前者是他的亲信,后者是他的高徒。前者是要夺权,没意思透了;后者是要争夺射术“天下第一”的虚誉,同样败人胃口;比起两个男人PK争夺一个美貌的女人,更无聊,也更无趣。
在神话传说中,月亮上那座广寒宫里,除了住着嫦娥这位不老的仙女,还住着一只玉兔和一位伐木工人吴刚。吴刚膀大腰圆,劲猛如牛,平日喜欢喝点自酿的桂花酒。他天天用巨斧砍伐那棵桂花树,几千年过去了,至今仍未砍断一根枝桠。工效这么差,我不说,大家也都猜出来了,原因都出在嫦娥身上。她每日闲得无聊,总要来看吴刚伐桂,吴刚颇有点心猿意马,总是有一斧没一斧地磨洋工。那棵桂花树粗可千人合抱,所以我们在地球上都能看见月中的桂影,吴刚这么弄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倒它的。吴刚跟嫦娥也能搭上讪,但他是个大老粗,别说嫦娥是小资情调,两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吴刚的自卑感一天比一天强,不仅心力亏了,膂力也弱了,只知去逗嫦娥怀里抱着的那只小玉兔玩,只知目送嫦娥孤单清冷的身影返回广寒宫,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更别说毛手毛脚,霸王硬开弓。就这样,吴刚把几千年的大好时光都给蹉跎得干干净净。嫦娥早已变成了性冷感,做事常常漫不经心,容易出错。这不,中秋节的月亮十五圆不了,十六圆不了,非要等到十七才圆。往后嫦娥还会错成啥样,谁知道呢?
吴刚拥有最佳位置却不作为,想做吴刚的人又到不了那个最佳位置,天下无数多情男儿唯有仰天长叹,空老情怀。
我在楼顶望月,胡思乱想,也没去翻书考证这些想法究竟着不着调,对不对谱,只记得一条:“后羿死后英魂不散,变成了打鬼的钟馗。”这个结论是被鲁迅狠狠挖苦过的史学家顾颉刚考证了《淮南子》等古书后作出的。很滑稽的说法,但也还算得上好玩。有朝一日,倘若打鬼的钟馗见到嫦娥,我估计,他们都会被对方吓一大跳,绝对不会是那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小儿女情调。
我生待明日
世上第一等傻瓜喜欢挥霍时间,第二等傻瓜喜欢挥霍感情,第三等傻瓜喜欢挥霍机会,第四等傻瓜喜欢挥霍金钱。
一个人,除非他心如死灰,行将就木,否则只要“明天”一词从脑海中闪霎而过,他立刻就会深感欢欣,满怀期冀。没有人能拒绝明天的莅临,它以多变的面孔造访人间,吉凶祸福悲喜苦乐兴亡成败,这些乃是它赠予芸芸众生的各色不同的大礼包。然而谁知道分摊在自己名下的那一份“惊喜”究竟是什么?
我们习惯了去看时间老脸上冷若冰霜的表情。谁曾瞧见过它善意的笑容?谁曾听见过它惬意的笑语?时间恰似一艘豪华游轮,它不间断地航行,将纷至沓来的过客从今天渡往明天,从生命的清晓渡往生命的黄昏。一代又一代人,由这艘大船渡进了历史的烟霭,渡进了夜晚的梦乡,兔缺乌沉,沧桑陵谷,似乎永无尽期。究竟说来,明天只是时间航程上小小的码头,能使人暂且获得喘息之机。平安岁月,明天是希望的梅林;生死关头,它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中,主人公邓蒂斯身陷死牢,危在旦夕,他仍强烈渴望明天能够成功地越狱,回返巴黎去报仇雪恨,亲手制裁那三个陷害自己的无赖之徒。明天竟是如此的悬疑和焦灼,直把读者的心紧紧揪住不放,直到他在大海中获救,找到狱友赠送的财宝,化名基督山伯爵抵达花都,开始实行其天衣无缝的复仇计划,读者才总算长舒一口气。明天即能伸冤雪耻,惩恶扬善,明天即能为民除奸,替天行道,这正是《基督山恩仇记》读来令人十分爽气的地方。
时光总是一路前行,明天似乎伸手可及,却又像影子一样无法把捉。明天也许是你的良辰吉日,也许毫无新意。我们往往被一个相对的概念愚弄了,以为明天即将来访,可是它永远都不会驾临,当生命戛然而止,明天却依然延伸。这个捉迷藏的游戏,人类已玩了一百万年,或者更久,还将继续玩下去,你说它算得上有趣,还是徒劳?有的人一生得过且过,含哺而嘻,鼓腹而游,无所用其心,他们昨天已经糊糊涂涂,今天照旧浑浑噩噩,没有什么分别;有的人志大才高,规模宏远,目光时时刻刻炯炯地盯着前方,在他们看来,明天意味着很多:有耕耘,也有收获;有竞争的刺激,也有成功的欣慰。
不须为明天营谋,这种清静恬淡的好处,世人多半与它无缘。古代的隐士尚且分为两类:一类是真隐,躬耕垅亩,采菊南山,俗务不复缠身。明天干什么?诗画也好,渔樵也成,总之是闲云快意,野鹤怡情;另一类是假隐,虽栖处烟霞,白云为田,绛雪为饭,走的却是终南捷径,表面上与世无争,心窝里却在盼望明天就有人开着奥迪、奔驰来接他下山,去做官,而且要做朝廷大官。如此捱日,他就颇有点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小孩子常常喜欢天真地问父母:“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父母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明天。”从此他等待着明天的太阳冉冉升起,直等到十八岁,禁不住感叹道:“原来明天要等上这么长的时间,真不容易!”接下去,又有一个问题横亘在他面前:“我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答案如出一辙:“明天。”这一次,他不再傻乎乎地等待了,他要自己去世界上磨炼和闯荡,增长见识和阅历。
莲池法师在《竹窗随笔》中记道:“伊庵有权禅师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么空过,未知来日功夫何如?”禅师最忌执著,但要勇猛精进,时间同样浪费不起,所以伊庵有权禅师对虚度今日颇为自咎,而对于明天则怀有期冀和憧憬。
只有厌世者才会把明天看成陷阱和圈套。他们在今天死心,明天已没有生路可寻,犹如一只被铅弹射中的鸟儿,一头栽落在泥淖里,转瞬间一切都已暗淡下来,成为一个盲点,陷入一团漆黑。即使用石头敲打他们的前额,他们也不会醒来,那么明天请不必为他们劳神。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听一听这首《明日歌》,你若能听得心头一紧,就说明你的意志还没有蛰睡。
希腊小邦底比斯的暴君阿基里斯曾留下过一句有名的口头禅,那就是:“公事明天再办。”这话说得轻松洒脱,他却为此断送了性命。当时大贵族派洛皮达暗中集聚力量,密谋推翻阿基里斯的暴虐统治,有人侦悉这一阴谋,赶紧写信给阿基里斯,敦劝他多加防备,先下手为强。驿使跑断马腿,将快信送到时,正值阿基里斯与家人共进晚餐。他将这封标明“十万火急”的信件搁在一边,满不在乎地说出那句口头禅:“公事明天再办。”他哪里想得到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见着明天的太阳了。
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着一句发人深思的名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光阴似箭,希望如春,箭矢离弦即不再回头,然而又有多少个春天可供我们虚耗呢?一个人既夙兴夜寐为今天活着,又枕戈待旦为明天活着,他必定不甘心平平庸庸窝窝囊囊过上一辈子。他的不满足便是他的动力,而时间一定会拿出足够的善意去成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