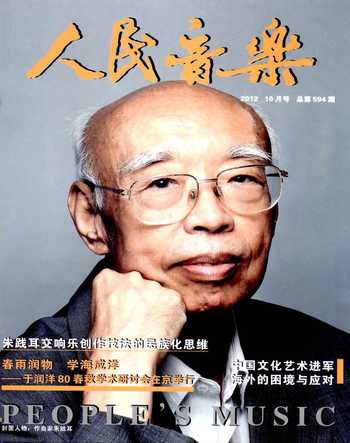作曲家与听众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音乐艺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变化着。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音乐样式,人们褒贬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很多人对现代派音乐的厌弃心理……主要还是因为这些音乐从形态结构上违背了人的听觉生理基础,从而导致了听众对它的本能抗拒……现代派音乐的最大弱点就在于无视接受者的听觉生理机制的内在规定性。”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对某种音乐能否接受主要是个观念问题,也就是说取决于接受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从本质上讲,除了超声波和超低波之外,任何可听范畴的音高,其任何组合都能为人的耳朵所接受。所以从生理角度出发谈这个问题是站不住脚的。关键还在于人的观念而不是生理因素。”②
以上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它揭示出现代音乐审美评价中两种对立的立场,即一方强调“听觉生理机制”,另一方强调“观念”。对此,人们早已从美学、心理学角度作了不少思考,却较少意识到许多争论、分歧的根本原因存在于社会学层面。
首先,若把“听觉生理机制”视为人的先天因素,把“观念”视为后天因素,那么,以上争论便体现出先天与后天因素的矛盾,或说是自然与文化的矛盾。任何人都是先天、后天因素的复合体,前者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心理特征,是人类共通且具有稳定性的因素。后者则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文化、社会特征,是习得的。根据环境不同,每个群体、个体的后天因素皆有差异。在现代音乐审美中,强调“听觉生理机制”者,侧重音乐的人类性或大群体性,强调“观念”者,侧重音乐的个体性或小群体性,立场不同导致评价结果不同。
假若继续追问,为什么双方的立场会不同呢?这便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即双方在音乐领域中承担的角色问题。“社会角色”(Social Role)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用于微观社会——即个体互动关系——的分析,指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它是对处在特定地位上人们行为的期待,也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③。比如,作为一位护士,要为病人打针、送药、换药,要关爱病人,这是她的职责,也是人们对她的期待④。
在音乐领域中,有三种最基本的角色,分别是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创作者和听众。总体上看,他们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取向。创作者的职责是不断创作新作品,这使他必须关注音乐是怎样被创造的,怎样才能把音乐写得有新意、有内涵。由此,他须具备丰富的音乐经验和技术知识。在创作者群体中,有的人传统些,有的人激进些,若是一位勇于创新的现代派作曲家,往往还乐于提出新颖的美学观念以指导创作实践。创作者为履行职责而积累起来的经验、技术、观念,不仅是他创作的依据,也是他评价他人作品的标准。
听众则是一个更为多层次的群体,大多数听众是非专业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趣味自由选择音乐并从中获得审美享受。这使之无需过多考虑创作细节,而更关注音乐成品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与创作者相比,多数听众的音乐经验和技术知识都十分有限,更乐于听到熟悉的音乐,有意无意地接受音乐应是悦耳的,音乐中最重要的是旋律等观念,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音乐评价。
至于专业听众,本身就可能是一位创作者、表演者或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介入现代音乐评价的理论家,其职责是对现代音乐现象进行相对客观的解释与评价。只有尽可能多地积累音乐经验、技术知识及历史知识,理论家才可能较好地履行职责。而经过艰辛思考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成为他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
以上分析看似平淡无奇,却暗示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因果关系:由于社会角色不同,导致现代音乐创作者与为数不少的听众(包括部分理论家)在职责、文化积累、音乐评价标准等方面不同,由此引发争论。下文将从三方面作进一步剖析。
二、从音乐审美经验的积累看角色差异现象
音乐审美经验是积累在人们记忆中,为其所熟悉的各种音乐音响经验。不论何种角色,获得音乐审美经验的唯一途径就是“聆听”。这意味着创作者也必须首先作为欣赏者去聆听他人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聆听”的过程中,不同的聆听者往往受制于不同因素,由此导致审美经验积累的差异。
第一种影响审美经验积累的因素是听觉自然偏好。音乐心理学界认为,人的听觉对声音具有某些先天偏好,如听觉只能把握20—20000赫兹的音高范围;最敏感的音域为20—4000赫兹;只能承受0—120分贝的音强范围;听觉本能地倾向于悦耳与协和的音响,倾向于彼此“接近”并具有“统一性”的音响等⑤。格式塔心理学则相信人的知觉所偏好的形态一般具有“规律性”、“对称性”、“单一性”三个特征⑥。据此,那些较为简单、有规则律动、以悦耳及协和音响为主体、材料变化不太复杂的音乐易于为自然听觉所接受。非专业听众具备较少音乐经验和技术知识,更多地依靠自然听觉聆听音乐,上述制约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明显。相反,专业听众因其有素的训练,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听觉制约,将高度复杂、不协和、非律动的音响吸纳为审美经验积累的一部分。
第二种影响因素是原有的音乐审美经验。若排除后天文化因素影响,任何人在获得音乐审美经验的过程中都将严格受制于听觉自然偏好。但是,符合这一假设的情况是极少的,因为现实中绝大多数聆听者都预先具备一定的积累,原有的审美经验便是其一。无论听众的原有经验以何种音乐风格为主,如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或是流行音乐,都会对本次聆听产生影响,亦即某种音响与人们原有音乐审美经验相似性越大,就越容易被接受,反之,则越不容易被接受。波兰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萨?穴Zofia Lissa,1908—1980?雪在谈及音乐理解时说:“在我们自己的表象中如果不具有对某一种类音乐风格的预先期待和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类音乐。在音乐作品的风格同听者的‘风格期待体系之间的距离愈大,理解这部作品的困难也就愈多。”⑦这里所说的接受者的“表象体系”与本文所说的原有音乐审美经验是一致的。一位对海顿、莫扎特音乐十分熟悉的听众,是较容易理解贝多芬音乐的,但他也许要花些气力去熟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可能会觉得普罗科菲耶夫《彼得与狼》中的“彼得”主题有些怪异,而当遇到勋伯格、梅西安的音乐时,可能会感到迷茫。正如美籍匈牙利哲学家拉兹洛(E.Laszlo,1932—)所说:“仅仅具有肖邦作品的鉴赏力不足以保证我们有欣赏巴托克的能力。”⑧如果说,某种音响与原有音乐审美经验相似性越大,就越容易被人们识别,那么,听众积累的审美经验越丰富,他所能理解的音乐也就越广泛。许多专业听众之所以易于接受现代音乐,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积累了较丰富的现代音乐审美经验,非专业听众则恰恰相反。
第三个因素是作曲技术知识。这一大多数听众所不具备的因素,却是专业听众得以适应那些既陌生又(对于自然听觉而言)不悦耳的音乐的重要原因。如张前所言:“在音响感知中如果有理性认识的帮助与指引,听众就会对音乐更准确、更深刻地进行感知”,在此,理性认识“主要是指对音乐音响的艺术组合及其形式结构的理性认识,它是通过对基本乐理以及和声学、对位法、配器法、曲式学等音乐技术理论知识的掌握来进行的”。⑨如当一位专业听众对照乐谱研读作品时,一边分析其中的技术,同时感受这些技术的实际音响效果。通过分析,他认识到某种音响通过什么技术制造出来,这种认识使得既陌生又不悦耳的声音在理性上变得可把握,通过理性的支持,他反复聆听了作品并渐渐适应。非专业听众不具备技术知识,主要以听觉把握音乐,这是他们不易进入现代音乐欣赏领域的又一原因。
当然,影响审美经验积累的因素仍不止于此,比如,聆听者对作品内涵及背景的了解,他默许的美学观念及对陌生事物的态度等皆可构成影响,这些因素也都可见出现代音乐创作者和多数听众的差异。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赘。
三、从音乐美学观念的特征看角色差异现象
音乐美学观念是人们对音乐艺术的本质、形态、内容、功能等问题所持的观点和态度,其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是音乐,怎样的音乐才是好的。若把这两个颇为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便可能出现许多与音乐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凸显旋律的音乐和凸显节奏或音色的音乐谁更优?音乐是否必须创新?“新”就意味着“好”吗?音乐是否应服务于听觉?服务于谁的听觉?音乐是否应具有民族性?什么才是民族性?什么才是中国式的歌剧等。这些问题往往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有关,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答案。
美学观念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以思想的方式存在,此时,它是一种清晰的理性认识,为其持有者所自觉;二是以非思想的方式存在,此时,它仅是一种模糊的态度,未必为其持有者所自觉。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听众,都具有一定的美学观念,然而,他们的美学观念又有不同特征。
绝大多数非专业听众的美学观念往往是以非思想的方式存在的。这些听众在自己的欣赏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什么是音乐,什么才是好的音乐等问题的模糊态度(如音乐必须有旋律,有调性,必须有规则律动等)。他们甚至不自觉这种态度,只是在接触到与此相抵触的音乐并开始怀疑这不是音乐的时候,才有所自知。有趣的是,这些听众的态度既十分主观,又与多数人较为一致。换言之,他们所偏爱的,也正是大多数人所偏爱的。因为,他们在欣赏实践中更多地依靠于听觉感官,这里潜藏着人类普遍的生理特征。
在专业听众中,理论家的美学观念常以思想的方式存在着。理论家往往要尽可能避免主观价值判断去对诸如什么是音乐、什么才是好的音乐等问题进行思考,尽可能得出相对客观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至少在学术研究中是这样的。也许有人会反驳,音乐史上一些理论家的美学观念不也具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吗?鲍埃修?穴A·M·S·Boethius,约480—525?雪崇尚宇宙的音乐而贬低器乐的音乐,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要让音乐模仿人的自然本性,汉斯利克(Eduara Hanslick?熏1825—1904)宣称音乐的内容不是情感等。的确,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具有主观价值倾向的美学观念,但这些观念又可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类:其一,作为价值坐标提出的美学观念。这并非以今天意义上的学术思维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美学观念,而是以某一理论家或他所处群体的需要为依据得出的观念(如鲍埃修和卢梭两例)。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它可在某时、某地为一部分人带来积极的效果,但随着学术自身的发展,人们需要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去求得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其二,作为反驳而提出的美学观念。如汉斯利克的理论。自然,无论该理论在美学史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不能掩盖其片面性。问题在于,一种片面的理论何以又成了深刻的?原因并不在这种理论本身,而在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学术环境。只有在情感论、表现论无限膨胀至忽略了音乐本身的时候,汉斯利克的片面性才成为了深刻的,换言之,只有在对另一种片面进行反驳的时候,片面的才成为了深刻的。失去这一条件,片面的仍是片面的。
与理论研究不同,艺术创作领域并非一个需要排除主观价值判断的地方,它恰恰是一片体现个性、差异性的天地。一位理论家可能会说,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輥?輮?訛,因为他无法找到能包容一切艺术现象的普遍性定义。但对于一位创作者而言,艺术是什么却是一个真问题,因为他正需要一个能指导自身创造实践的个性化价值坐标。由此,多数创作者获得美学观念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与那些有着鲜明主观价值判断倾向的理论家相似,而与那些追求普遍性答案的理论家相悖。创作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自己的价值坐标,甚至反叛他人的价值坐标,哪怕其思想偶尔会走极端。由此,有人说“我不能想象音乐什么也没有表现”(巴托克语)?輥?輯?訛;有人却说“音乐从它的本质上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斯特拉文斯基语)?輥?輰?訛;有人说音乐创作中和声最重要(拉莫语),有人却认为旋律更重要(卢梭语)?輥?輱?訛;有人说“作曲家到了最后就是比观念”(谭盾语)?輥?輲?訛,有人则说“谁在乎你听不听”(巴比特)?輥?輳?訛;有人竭力让不协和音得到解放(勋伯格语),更有人要让音乐回到生活(凯奇语)。我们不能也无须用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待它们,因为提出这些观念的人不是在进行理论研究。
四、现代音乐审美中角色差异现象的
不可避免性
上文从音乐审美经验积累和美学观念特征两方面剖析了创作者和不同类型的听众之间的差异,紧随而来的问题是,人们可否消除这些差异?要知道,差异消除了,关于现代音乐的各类争论也就化解了。但是,差异可能消除吗?
对于非专业听众而言,在有限的音乐能力范围内选择聆听何种音乐,选择何种美学观念,都是他的自由,因为他无需承担音乐职业所规定的任何职责。而对于专业音乐工作者,特别是创作者而言,似乎没有这种全然的自由。一方面,创作者也在依据自己的偏好选择音乐,并大胆地创造新音乐,甚至颠覆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创作者的选择本身也受到某些不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的规定:(1)角色与群体的规定。作为一位现代创作者,从踏上创作道路的那天起,就在努力使自己符合专业或职业的要求,他必须积极地关注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聆听、研究那些在音乐史上有重要影响却相对复杂的音乐,否则,根本无法将自己的创作并入音乐历史的轨道,也无法走在音乐创作的前沿,甚至无法获得所在创作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同。这里,似乎有一种群体内的无形规则,强有力地引导、约束着创作者。我国作曲家陈其钢曾说:“现代音乐自二十世纪以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旋律,你如果作一个有完整旋律的作品,人们会说这不是现代音乐,你离经叛道了,受到的压力会很大。”?輥?輴?訛这种压力正体现出创作者群体趣味对某个体的无形限制。此外,现代作曲家的角色还要求某人必须有所创新,这种产生于18世纪末的观念已然成为今天每一位创作者职责的一部分?輥?輵?訛。由此,他无法满足于无新意的作品,而要寻求新的、个性化的音乐语言,以确证自己的创造力,丰富音乐的百花园。正是在此诉求的驱策下,他们探索音乐创作的各种可能性,从序列手法到复杂节奏开掘,从以数列控制音乐形式到以哲学(如阴阳哲学)思想控制音乐形式,从对民间音调的运用到对新音响的探索,甚至完全放弃对音乐作品的控制等。(2)音乐文化发展现状的规定。任何创作者都不得不在现有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些文化成果既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创新的起点。比如,一位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创作者,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出要创造一种新的音高控制体系的需要,因为,调性和声体系在当时并未被开发殆尽,人们仅会去考虑如何使该体系的可能性得到更充分地开掘。换言之,创新的需要可以在现有体系内得到满足。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就不一样了,经瓦格纳等作曲家之手,该音高控制体系已被充分开掘,在强烈的创新使命感的推动下,创作者不得不寻求新的音高控制途径,由此产生了各种无调性作曲技术。美国文化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1900—1975)曾提及“文化范式”的概念,认为“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整合与统一;它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并按一定的途径或原则组织起来”,“一个具有特定前提和某种发展原则的范式有着确定的潜力和内在固有的局限。一旦达到了这些极限便不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当绘画和雕刻真实地再现了自然物体,也便达到了极限而无可再发展了”,“某种音乐范式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中显然已达到它的顶峰”。?輥?輶?訛如果我们把调性和声体系视为音乐文化的某种范式,那么,该体系从形成到饱和的发展过程正是一个不以某位创作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化自身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位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且有着强烈创新使命感的创作者,都不得不对该体系的饱和做出反应。以上两方面限制都超越了个体创作者的可控范围,创作者可能并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受到它们的影响。也许,一位创作者的成功,正在于面对并超越这些限制,在不自由中找寻自由,在限制中探寻最佳选择!而对于身处创作群体之外的大多数听众而言,这一切皆是陌生且不易理解的。
如果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听众,都必须面对某些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限制,那么彼此间的差异便是无法消除的,有关现代音乐的争论也将永远进行下去。如果说,这就是现代多元音乐世界的现实,它无可更改,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接受它?也许,接受差异反而会减少争论,反而会促进角色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在此,作曲家仍可能坚持自己的创新诉求,但他更清楚自己在为哪一类听众所创作着。若要争取更多听众,那么,作曲家或可走到听众中间,用听众可理解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创作意图,或创作出接近或符合多数听众偏好的音乐。选择权仍在作曲家手上。对于多数听众而言,了解现代作曲家的所思所感,了解创作群体对创作个体的规定性及其历史成因是有助益的。在面对带有实验性的作品——如凯奇的《4分33秒》、赖克的《六架钢琴》(Six Piano,1973)时,有必要关注它们在创作群体内部对同代、后代作曲家的启发价值。诚然,听众也依然保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①②《关于现代音乐语言问题的讨论》系列文章第1篇:《中国音乐报》1989年1月13日。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会角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④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⑤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7页。
⑥[美]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⑦[波]卓菲娅·丽萨《卓菲娅·丽萨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于润洋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⑧[匈]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⑨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⑩[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芽波普尔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62页。
⑾[美]约瑟夫·马格利斯(Joseph Machlis):《当代音乐导论》(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Music?熏 J M Dent & Sons Ltd 1980),第182页。原文为:I cannot conceive of music that expresses absolutely nothing .
⑿[美]斯特拉文斯基《我的生活纪事》,转引自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⒀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⒁卞祖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关于音乐观念与音乐评论的争论》,《人民音乐》2002年第3期。
⒂巴比特《谁在乎你听不听》,蔡良玉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⒃陈其钢《走出“现代音乐”追求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98年第6期。
⒄众所周知,中世纪的作曲家必须符合宗教仪式的限制,还未形成鲜明的原创性诉求,甚至,教会还明令禁止在弥撒中使用原创的音乐(莉迪亚·戈尔《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罗东晖译,杨燕迪审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第40页);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更多地为宫廷和教堂服务,仍多少受制于宗教仪式的需要和贵族的艺术趣味;18世纪末以降,作曲家渐渐摆脱了外在束缚,他们与听众一道,对原创性有了明确的要求。贝多芬曾说:“我不了解,也不想听别人的音乐,以防丧失我自己的原创性。”而莫扎特的一首《C大调圆号协奏曲》则被听众批评为没有原创性,罗西尼更因多次重复同样的音乐而受到抨击。也正在此时,法国、英国陆续出现了有关版权保护的法律,以确认作曲家对作品的原创性和所有权(同上:第237-240页)。随后,经浪漫主义者的强化,“原创”、“创新”、“个性”这些词藻更是深入人心,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作曲家的自我要求,一直延续到今天。
⒅[美]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
柯扬 博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