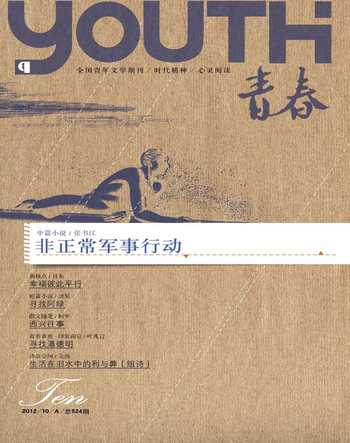乡情散文三则
姚正安
父亲米寿
父亲今年八十八岁,谓之为“米寿”。
早前,我不知道八十八是“米寿”,是几年前读宗璞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始知“米寿”一说。
宗璞说她的父亲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八十八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幅对联,一幅给自己,一幅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幅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三松即三松堂,冯友兰的居室)。”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艹”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金岳霖是哲学家,冯友兰称赞其学问修养高超,白马指公孙龙,青牛指老子)。原来,八十八是由“米”字拆开的,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
米寿的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做着三件事,忙碌而有规律。
父亲每天起得很早,无论春夏秋冬,天麻麻亮就起床了。洗漱后,就急匆匆地到村东头开庙门,打扫、敬香。父亲曾不止一次很骄傲地告诉我,原先村里的庙很大,香火很盛,每年三月三迎会,那场面很是了得。文化大革命中,庙里的菩萨被烧了,庙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大约十多年前,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老人,看到别村建庙了,便寻思着将闲置的仓库,恢复成庙。倡议一经提出,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家家户户出钱出力,不多时,破庙整修完工,从苏州请回菩萨。从那时起,父亲便有了一项固定的工作,保管庙里的钥匙。庙门不是每天都打开的,但平时只要需要,父亲是随喊随到,极负责任。
庙里的事情停当后,父亲就回家烧早饭。我和弟弟在外地工作,父母仍生活在农村老家。母亲长父亲两岁,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大病没有,小病小痛不断。服侍母亲,操持家务,便成了父亲生活的主要内容。
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看到父亲正跪在浮箱码头上汰衣服,我的眼睛立即湿润了,父亲不会游泳,万一滑下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责怪父亲不该如此大意,父亲若无其事,连说,不碍事,做惯了。想想,父亲也是无奈,我们在外地,衣服总不能等我们回家洗。虽然姐姐嫁在本村,也不能事事留给姐姐做,用父亲的话说,“他们家里事情也多”。父亲小时候娇生惯养,家务从不染指,是生活逼着父亲学会了做家务,学会了服侍人。
今年春节后不久,我的三舅妈去世了,按说,母亲九十岁了,可以不去,通知我们一声就行了。可母亲执意要去,对前来送信的娘家人说:“小伙他们忙就不去了,我们去,我和弟媳相处几十年,没有红过脸,现在她走了,去送送她”。父亲陪着母亲去了娘家。偏偏那几天特别冷,母亲回来后就生病了,气管炎、肺炎并发,挂了几天水也不见效。我请教县医院的专家,开了药,送回去。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父亲也不断地咳嗽,流清水鼻涕。
我说,爸,你怎么也感冒了。父亲说,你妈妈身体不好,夜里要喝几次茶,我都要起来倒。说着说着,父亲的眼睛红了。父亲感到委屈?痛苦?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性子急,做事快,父亲的笨手笨脚难免遭到母亲的白眼,真是难为了父亲。父亲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已经多年。父亲是为我们做的,如果我和弟弟在家做农民,父亲的负担兴许会轻些。
虽然只有父母两个人生活,但开门几件事也是少不了的,何况还要应付门面户差,本家的红白大事,因为我们不在家,父母虽年迈,也得去帮忙,纵然不做什么重活,一天坐下来,也够呛。因而,父亲成天闲不住,有了空闲,还要种菜,父母居所旁有一块两分地的菜地,种些常规蔬菜。我们戏言,那块菜地是父亲的健身广场。我们同意并帮助父亲整理菜地,其用意也是让父亲活动活动筋骨。
我说父亲成年累月做着三件事:烧香、做家务、种菜。其实,事套事,事连事,何止三件。
前些年,父亲还打打小麻将,自从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做家务后,麻将也不打了,成天围着家转,围着母亲转。
但父亲活得快乐,活得充实。我每次回家,老人家必早早地等候在村后的停车场旁,走的时候,也一定陪我一路走一路谈,腰板挺直,步履稳健,声音洪亮,怎么看也不像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
父母健康长寿是子女的福份。我希望父亲健康快乐地活着,希望父亲搀扶着父母欢度百岁,走进茶寿。
母亲的眼光
1973年夏季,我初中毕业,在升高中问题上还出现了一点波折。那一年升高中与往年有所不同,那一年是邓小平复出搞整顿,学生升学不能只凭推荐,还要看成绩,因此是学校、大队联合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学校推荐意见有分歧,有老师以我调皮为由,拟不予推荐,是班主任的一句话帮我解了围,班主任说,“哪个小孩不调皮,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就行了,再说,他家成份好”。“他家成份好”是关键,那时,政审很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是不可能被推荐上学的。学校关算是过了。当然是谁说的,为什么说,后来我是知道的,不去说它。大队推荐一路绿灯,大队干部比较开明,他们的观点是,“不管哪家的孩子,只要符合条件,就让他们上”。
更大的阻力在家里。我们家比较特殊,等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几个姐姐都已出嫁,我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爷爷奶奶虽分开单过,但还算在一家户头上。全家六人,只有爸妈两个劳力,而且,妈曾经摔过一跤,腿脚不便,真正算起来也就是一个半劳力。那时,生产队分粮分油以及年终决算都以工分多少为依据,我们家因为工分少,因而不仅平时分到的实物少,年终决算还常常超支。如果我能出来,无疑能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况且,生产队与我年龄相仿的,都出来挣工分了。因此,爷爷奶奶包括姐姐姐夫都主张,农村人识点字算了,识多少字有什么用,字不能当饭吃,早点出来挣工分才是正途。爸爸始终没有说是也没有说非,大的问题上爸爸的态度一贯如此。
我当时年龄小不懂事,又有几个伙伴劝我出来与他们一同干活,对上不上高中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大人让上就上,不让上就修地球。
我上与不上高中的关键就看妈妈的态度了。
妈妈的态度令爷爷奶奶吃惊。妈说,五丫头(我排行老五,乳名),已经考上了,学校大队又同意,就让他上。再说,他现在身体单,出来也挣不了大工分。爷爷说,一天哪怕挣五分工,一年也是千把分,到底能多分些东西。妈说,工分少点就少点,大不了少吃点少用点。字识到肚子里不得坏。爷爷急了,“我这是在帮你们”。妈说,我晓得,你是为我们好,挣工分的日子长呢,还是让他上。
我当时弄不懂,爷爷是个读书人,又特别喜欢我,为什么不同意我上学呢?后来,爷爷告诉我,他是舍不得我爸爸,爸爸从小身体单薄,又生性软弱,在生产队说不上被别人欺负,但处于弱势地位,爷爷希望我出来帮帮爸爸,帮助家里挑点担子。
由于妈妈的坚持,我顺利地升入了高中。几年后,还是妈妈的坚持,弟弟也升入高中。农民家庭两个儿子上高中的,在我们村,我们家差不多是唯一的。邻居都说妈妈不简单,其所以不简单,就是宁愿自己多吃苦,也要让儿子读书。
妈妈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妈妈的眼光是深远的,用妈妈的话说,看到的不只是脚面上的一点好处。如果不是妈妈的坚持,我和弟都会初中毕业后参加劳动。且不说,上高中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不上高中有什么坏处,“前面的路是黑的”,谁也能以预料,村里没有上高中而做官发财的,大有人在。但妈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机会人生中不可多得。
我和弟没有辜负妈妈,现在我和弟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有一个不富有但很幸福的家庭。这是妈哺育的结果,也是对妈哺育的最好回报。
远去的端午
离家三十多年,在外地度过了三十多个端午。在端午未列为国假前,端午节与休息日相遇的情况似乎很少,我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家里没有老人做帮手,因而,既不能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节,也没认真地享受过端午,只有一两年,看到邻居家挂艾蒿,也到附近的菜场买几根艾条挂上。偏我不喜欢吃粽子,因而,端午与平日无异。
我脑子里的端午还是三十多年前老家人过端午的情形。
三十多年前,老家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但老家人把个端午过得火热火热的。每家必裹粽子。还离端午远着哩,村子前后小河里就听到兴化小贩卖棕箬的吆喝声,端午前几天大大小小的巷子里就满溢着棕叶的清香。只不过因家庭条件优劣,粽子的数量和品种略有区别而矣。条件好的,粽子裹得多,养在水缸里,能吃上几个月,品种也多些,不仅有白粽子(纯糯米),还有红豆(赤豆)粽子、蚕豆粽子(在糯米里掺上豆类),至于,咸肉粽子、香肠粽子是后来的事。每家必挂艾蒿和菖蒲,那时这两种植物,村前村后荒塘水沟里多的是,下工拔几根就是了。老人们说,菖蒲是神手里的箭,能刺杀妖魔。除了极少数困难人家,大多数小孩都于端午早晨在手腕里戴上百索子(用五颜六色的棉线绞成),讲究的人家还给小孩穿上虎鞋(鞋的前半部分绣成虎脸形状)。老家还有涂雄黄水、喝雄黄酒、吃九红菜的习俗。所谓九红菜是九种食物的总称,我只记得炒苋菜、炒韮菜、煮咸鸭蛋、炒长鱼(黄鳝)、红烧肉、红烧鱼,一般人家都凑不全九红。
老家没人能说出端午的来历,至少,我没听过完整的端午习俗的由来,爷爷和父亲都是读过私塾的,他们也没向我讲过这方面的传说或者故事。端午与纪念屈原、与劳动人民尊重自然、祈求健康,是长大后从书里知道的。但老家人代代相传,把端午的核心内容承继下来了,虽然物质匮乏,而态度是认真的,用心也是虔诚的,并且叮嘱小孩要防百脚、壁虎子,那时住的是草房,这些动物特别多。
今年端午一早回家,一路上,脑子里闪过一幕幕老家人过端午的镜头。一位老奶奶捧着一只碗,筷子上戳着一只澄黄澄黄的粽子,也许是牙齿不好,头歪着嚼,脸上漾着幸福的波浪。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缠着妈妈为他戴上长命百索子。一位中年男子拎着菜篮子一路走一路叽咕:“长鱼怎这么快就卖光了,到哪找长鱼呢?”
这么想着,已经来到村后。沿着小路向家里走,路两边有村民三三两两地聊天,有老人分拣青菜,嗅不到粽叶的幽香,看不见艾蒲的踪影。家中,九十岁的母亲坐在凳上打盹,米寿的父亲在院子里晾衣服。门上没有艾蒿,厨房里没有鱼虾。
父亲见我,说:“你妈妈这几天身体不好,已经挂了几天水,过一等,还要挂。”
妻子收拾从城里带回的菜,准备烧饭。我到姐姐家看看。姐夫在门前乘凉,中风的姐姐在躺椅上睡觉,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
我奇怪地问姐夫:“今天不是端午节吗,庄上怎么这样冷清?”
姐夫说:“大忙刚结束,年青的外出打工了,年老的累了歇歇,哪个还顾得上过节。”
我留心路过的每户人家,几乎家家如此,过着平常的生活,没有艾条,没有雄黄,没有百索子,没有九红菜。
端午离老家远去了。
其实又岂止是端午,春节也是一样。我每年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村子里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也和我一样,能回来的都赶回来过年。除了村后停车场上各式车子、除夕夜如雨的爆竹,我也感受不到既往的年味。
小时候,一进腊月,男女老少都忙着过年,磨粉面、蒸团糕、做新鞋、刻画边、打扫除,忙得开开心心,忙得热热闹闹。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欢欢喜喜地拜年,拜长辈年,拜本家年,邻居们相互拜年。八九点钟光景,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开始演出了,大人小孩又奔到大会堂看演出,真是笑声歌声随风飘荡,恭喜发财不绝于耳。
现在的情形大异于前,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忙着打牌,老人们忙着烧饭做菜,小孩们忙着看电视。一家一单元,做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小巷里很少有人走动。如果不是鲜艳的春联,没有轰鸣的爆竹,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春节。
端午离老家人远去了,春节离老家人远去了,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离老家人远去了。端午、中秋,更多的是作为时间概念保留着。
有位民俗学家分析,在农村老年人无力撑起传统节日,年轻人想着挣钱,想着过现代化的生活,不屑于民俗风情。
那么,在城里呢。城市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社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一方面传统遭遇着现代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异地的风情形不成气候。传统也与现代城市渐行渐远。
传统是根,没根的浮萍会飘向何方?
责任编辑⊙青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