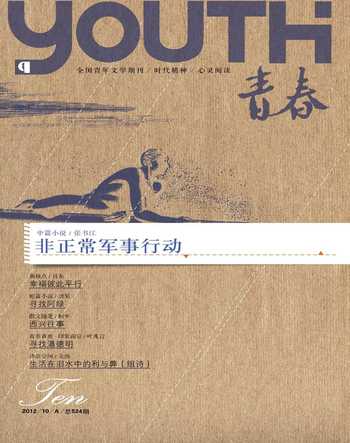幸福彼此平行
1
莫小帘对我说过,很多很多年以前,人都是纸做的。可以是红色的纸,也可以是白色纸。用红色的纸时,人被包成一个红包的模样;如果是用白纸,看上去就像一盏孔明灯。
说这话的时候,莫小帘还是大学里一个喜欢望天空的女孩;我是一个喜欢玩吉他的愤青。
而突然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开车在国道上狂奔,正准备去接新娘。那个叫莫小帘的女子,在去年夏天,离家出走,仿佛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月后,我和妻子走进电影院,看了最近热映的美国大片《2012》。看完从影院出来的时候,这句话在我心头重新流过去,像一个黑色的鬼闪了一下,就不见了。那时我刚换了新车,凑钱买的,雪铁龙世嘉三厢,还开不到一千公里。车子处于磨合期,妻子也处于磨合期,其实,日子也处于磨合期。
这样的日子,几乎没有故事——按时上班,回家看电视,晚上抱老婆,按时睡觉,并准备第二天上班去见一些隐约相似的人,说一些和昨天类似的话,月底的时候,到工资卡里面去查工资,取钱,还房贷,给车加油,然后把钱捏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过。磨合期嘛,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的,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能节省不少的能量。你不能说青春无悔,也不能说心有不甘——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和许多80后一样,这样的日子简直不值一提。
每天都在期待周末和假期,好像我们是为了假期才活着一样。终于周末到了,想起这个月闯了两次红灯,四百大洋,去交了钱,一个人开着车,整个空间好像是你的,又好像不是你的,于是,突然想去看看海。应该说,故事是从看海这个荒唐的念头开始的。
2
车在路上,人在车中,车里放着低低的音乐。
这是下午,照例阳光灿烂,白云都被赶到天边去了,天空的中央,是一片蓝得非常寂寞的晶莹的颜色。车子转了一个弯,进入了一条大路,仰头望去时,在一片田野的尽头,云层堆在一起,金黄色的阳光打在云堆上,那简直就是一尊大佛,盘腿而坐,正俯下身子,对我微笑。不知一股什么力量在我心头撞击了一下。大佛啊,生活的网将人死死网住,这样日复一日的岁月何时是个头。我停车熄火,音乐也消失无踪,而心中的音乐突然响起。突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我不禁伏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起来。
广漠的田野中间,一条笔直的路,一辆车,那么小,车里那个中年人也那么小,他像野草一样,已经完全陷进生活里,无法自拔。
我哭了一会,想想有点滑稽,有点无厘头,有点不可思议,于是又对自己笑了笑,带着泪花笑了几声,觉得浑身舒畅,很爽。一踩油门,继续往前走。又转了一个弯,前面修路,请绕道,好吧,绕道,再往前,越走越荒凉,又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彻底地迷路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是香蕉林,每条路基本都一样。掏出手机,没信号,惨了,一种不祥掠过了我的心头,眼看天气入冬,太阳会很快下山,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不小心就会成为明天日报的头条新闻。
又转了两个弯,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居然看到了远处有稀疏的灯光,我大喜若狂,沿着颠簸的土路往前走,看起来很近,其实还远得很。
这是一个山脚下的村庄,地势较高,所以老远能看得到,慢慢接近一户人家(其实就是用竹子搭建的房子),灯光从果树林中透出来,依稀能听得到屋里收音机的声音。就在这时,突然看到前面黑影一闪,接着我就听到一声狗的惨叫声,我急忙刹车,但已经太迟了,我知道这条狗死定了。紧接着,在果树林里面的这间屋里,传来了脚步声和手电筒的光,我赶忙熄火下车,这时,两支手电的光照在我脸上,眼睛都睁不开。
来者何人我一点都看不清楚,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终于开口说话,我才知道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男孩喊:“奶奶,有人撞死了我们家天神!”
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年龄更小:“快来啊,天神还在动!”
我从女孩的手电筒的光线看去,那条黑色的狗,有点脱毛,黑色的毛发覆盖不住红色的皮肤,它在我前轮后面露出一条很短的尾巴,浑身不停地颤抖,车下是一摊血。我本能地上去,想把狗抱出来。我蹲下身,去拉狗的后腿,它发出了更为凄厉的叫声,这时竹屋里面,由远而近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回头看看,第三支手电筒在移动,但接着,我感觉到前臂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那条脱了毛的黑狗,转过头来将我的手臂死死地咬住。
我惨叫一声想挣脱,但那条狗用迷离的眼神看着我,一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我感觉自己的手臂就要断了,支撑不住,我也瘫倒在地上,那条狗的前腿蹬在我肚子上,腰基本已经被碾断了。它死死地咬着我,眼神如死水,身体正在慢慢变冷。我眼前的光线越来越粗糙起来,最后一片朦胧。
我要死了么?
3
我的世界一片朦胧。但眼前却是十二指街熟悉的风景,莫小帘轻声地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满街飘飞的木棉花的白絮?
那些木棉花絮飘飞的季节,十二指街干净得只容得下呼吸。莫小帘和她的男朋友在十二指街一栋破旧的出租屋里租下了一间套房,狭窄的楼梯,两重铁门和生锈的铁窗罩,莫小帘说,只有这些才让人感觉踏实,铁是最安全可靠的。但铁门和铁罩防得住小偷,却防不住人的心,莫小帘很快面临情敌的挑衅,男友开始站在她这一边,但后来倒戈,认为她无理取闹,于是搬了出去。大学爱情嘛,当然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在我请她吃了三趟麻辣烫以后,她宣称她已经痊愈。
我问她是否考虑搬出那个五楼的房间,回到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人多热闹些,也就不会想东想西”,并提出如果搬家,我愿意当免费劳力。
她捏了捏我的手臂说:“你这也算肌肉?连我这个人都搬不动,还说要搬家,你省省吧!”接着,她说宿舍环境不好,洗澡都要到公共浴室,劝我也搬出来一起住:“三室一厅,不住也浪费。况且你来撑撑门面,那头中山狼也不会太猖狂,总带着那只狐狸来我面前晃。”
我理解她的心情,但这时候搬进去,嫌疑太大,弄不好会说不清道不明,别人以为我趁火打劫。于是我表示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再搬进去吧,反正有三个房间。
“等?你没希望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宿舍里赌你到毕业都找不到女朋友,赔率都达到十六比一啦!”说完她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最后泣不成声。
我知道大学失恋,三顿麻辣烫还是搞不定的。第一周为适应期,第二周为反刍期,第三周是煎熬期,第四周是掩盖期,至少必须一个月才能把爱情这个毒彻底戒掉。
“那你说说我现在是什么期?”
“你现在是鼻涕期,就是半生不死那种……把鼻涕擦了吧!”我给她递去了纸巾,同时告诉他,我们男生吃饭,从来不带纸巾,环保节能。她说你们脏。我说那不脏,我们每顿饭都擦嘴的。然后演示给她看:把一次性筷子拿起来,两根,一左一右从嘴巴上刮过去,就跟剃胡子一样,唰唰,你看,干净了!
她破涕为笑。
4
失恋之后,莫小帘迷上了折纸。她的房间里挂满了各种动物,纸鹤、纸虾、纸螃蟹、纸蛤蟆、纸袋鼠……品种繁多,琳琅满目,但所有的动物却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白色,一种是红色。
“很多很多年以前,人都是纸做的。可以是红色的纸,也可以是白色纸。用红色的纸时,人被包成一个红包的模样;如果是用白纸,看上去就像一盏孔明灯。”
我问她,是不是红色代表开心,白色代表不开心?还是红色表示庸俗的生活,白色表示超脱的生活?抑或,红是生,白是死?
她笑而不答,却嫌我一口气问了太多问题。
也正因为她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这一句话竟然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连同那栋幽暗的出租屋,铁门铁窗和红白两色的折纸,都被保存在十二指街美丽的木棉花絮里。那是关于青春的部分,每每想起总令人心头发酸。
她折纸的技术越来越好,基本是折什么像什么,但是她自己也迷惑起来:“全是动物,再好的纸也折不出一个人。”
莫小帘说:“毕业以后我要去一个海边的城市工作,说起来你别笑我,长这么大,我还没看过海。”这是她抬起眼睛,安静地看着我,气氛过于抒情,于是我和她讨论起窗外的木棉树,这些年老的树,在古老的州府,一年又一年地盛开着,丝毫也不觉得寂寞。
在这抒情的时刻,莫小帘讲起了她的父亲。我知道她跟她父亲一直很僵,在她看来,父亲的专横和固执似乎无法用岁月去化解。但在这个时候,莫小帘讲起了七岁那一年,父亲开着公交车送她上学的情景:“那别提有多神气!一辆公交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开摩托送小孩上学的家长都要抬起头来看我!”可是不久,父亲因为擅自改动公交路线被辞退,失业了。
从莫小帘眼中闪烁的光芒看来,这是父爱的一个顶点,似乎此前此后,父亲就不是父亲,而是敌人。她说她为什么会失去这个人,是因为自己不愿意说我爱你,我想你,我想见到你。就像是小时候,父亲要出门,她紧紧地抿着嘴唇,就是不说“我想跟你去”,然后趴在窗沿上,看着父亲渐行渐远,自己却绝望地跌坐在门槛上。
一所种满木棉树的大学,一条开满木棉花的老街,一所被铁和水泥包围的房子,还有一个紧紧抓住自己不放的女孩。当我们回忆着消逝岁月的时候,却不知道多年以后竟然回忆着这些回忆,而朦胧中的痛感让我一点点地清醒过来。
5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自己正是从地底下慢慢升腾到人间。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我身上拔出一些细长的针,我唉唉地叫了两声,旁边一个男孩的声音响起:“给你水!”
他举着一碗水,但动作粗鲁,所以溅得满地都是。
那个老者喃喃说到:“死不了——我就说三针下去,他一定会醒来的……走开点,小心你的水!”他把那个男孩喝退两步,然后站起来,把手上的银针放进盒子里。
这时候我又听到炒菜的声音,然后那个老头对一个阿婆说:“他没什么事,按时煎药给他吃,烧退了就没事。那我走了!”
阿婆声音奇大地邀请他留下来吃饭,然后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说她自己的。即使头痛欲裂,我也大概可以推断出阿婆耳朵不大好使。那个男孩坚持要把他那碗水给我喝,但我的右臂包扎得像个南瓜。我挣扎着坐起来,喝了一碗水,这时我闻到一股强烈的尿臭味,闻一闻才知道,原来是从我包扎的那只手发出来的。
在一旁的男孩咧嘴笑了。他告诉我,在昏迷的这两天里,我已经吃了两条蜈蚣。包扎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指了指墙角的一只木桶:“那是撒尿用的,桶里面那层白色的东西……”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又捏着鼻子,调皮地跳开几米远,站在那里傻笑。
两天后,高烧退去,我基本能够下床行走。这两天躺在床上,我经常能听到我那辆车的喇叭被按得“叭叭”的响,知道有一群孩子在鼓捣我的新车,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出门一看,果然,窗玻璃被砸掉两块,座椅上都是脚印和泥土,方向盘全是口香糖。
那个男孩小心翼翼地从我后面跟上来,我转过身的时候,我两只手高高举起来,把那我的手机递给我:“给,你的,我从他们手里抢下来给你的。”手机已经没电,黑屏。我看着他晶莹的眼睛,突然又一种感动涌上心头。
阿婆提着嗓门嚷着告诉我,要打手机得爬到山上去才打得到。她无意间又说了一句:“山那边就是大海了。现在都没人出海捕鱼了,年轻人都走了,到城市里去,半坡村啊,荒了,剩下都是老人和小孩。”
原来我已经到了海边了!
阿婆把饭菜端了上来,说:“吃吧,小伙子,吃吧,饿了才会想家,吃饱了你就不会想家。”
6
我突然内心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我一直都渴望一个转身,能够切换了人生的频道,刷新人生的屏幕,一切重新开始。当然,这个渴望,是渴望自己拥有得更多,希望得到的不断增加,既要白马,也要轻裘,所以有无穷无尽的痛苦。但如果人生运算减法,将一切都减去,我的妻子、房子、车子,以及以后会有的孩子,全部不要了,人生也就切换了一个频道了。
这样一个频道,莫小帘开通了,在去年夏天;但我不能,我没有勇气这样做。
那一年冬天,大三,处于大学时光的腰椎上,寒风吹得人全身酸痛。莫小帘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围着枣红色的围巾,蹬着皮靴,哐嗒哐嗒地走在十二指街的石板路上,麻辣烫和炒栗子的香味,让这个冬天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大三,我和莫小帘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彼此感知对方的存在,却又各忙各的。这大概符合大部分朋友的状态,我将这种状况概括为“幸福彼此平行”。
直到这一天,莫小帘突然出现在我眼前,黑大衣、枣红围巾和皮靴,她似乎瘦了,一双眼睛显得很大。但她笑着说没有瘦,是热胀冷缩的缘故。
她此行的目的,是想告诉我,她想读研。家里一定会在附近安排工作,毕业就得回家,回家就得面对父母,找工作找对象结婚生子,一辈子就那样固定下来,这是她最不愿意的。
“读研究生?你没问题吧?是不是昨天晚上被蚊子踢额头了?吊儿郎当地玩到大三,然后说要读研?”
面对我的惊讶,她似乎胸有成竹:“我想申请保研。”
“这不可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你都拼不过那些书呆子和关系户。”
这时她的电话响了,她转过身去接电话,说了几句,突然将电话举向空中,然后伸过头来,在我耳边低声说:“我老爸,你听,他又在发威——”那个高高举起的电话里面,的确传来一个义正辞严的声音。
7
快进入大四的时候,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写诗歌的女孩子,开始了一段乌托邦的两地恋。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要女人,我就会被性欲折磨;如果有了女人,我就会被爱情折磨。但开始了两地恋,结果我既被爱情折磨,也被性欲折磨。
这个女诗人对诗歌过于执着,换言之,性格非常偏激,用她的话说:“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生的受难;这个光荣的封号并非养尊处优,而是在受难中还要不停地创造,不能关闭自己,而是执意将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说出来。”这些倒还没什么,关键是她抵制手机,出门不带手机,我只能打电话到她家或她宿舍。这倒也还能忍受,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她喜欢挂人家电话,两句话谈不拢,她也不跟你吵架,不回应不纠缠,“咵哒”一声,在那头就把电话给挂了,回头吩咐家人朋友,如果我再打来就说她不在。我们距离上千公里,我不可能马上坐飞机去找她理论,一股气憋在心里,郁郁不得宣。这样一个月下来,我病了两次,足足瘦了八斤。
我想这样不是办法,还是冷静处理,挥慧剑斩情丝,换了手机号码,改了邮箱,将她拉入QQ的黑名单,如此一来,整个世界轻松多了。
但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该女诗人穿着高跟鞋,提着旅行包,出现在我宿舍门口找我。此时我正吃完榴莲,在阳台上刷牙,只穿一条短裤,拖鞋,一口白沫,见到只在视频时才见到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呆住了。
女诗人哭诉了这段时间的暗无天日、惨无人道,我酸酸地问一句:“是不是觉得有一股气憋在心里,郁郁不得宣?”她连连点头,眼泪就出来了。让一个女人在男生宿舍哭,总也不是办法。莫小帘和她十二指街五楼的房间让我眼前一亮,于是吃完饭之后,我带着女诗人,提着行李,直奔莫小帘的房子而去。
敲门。莫小帘不在。打了三次电话,莫小帘终于接了,我大吼一声:“你在哪里?”她略带紧张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现在在你房间外面的楼梯口,你快点给我回来。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不知哪来的火气。
女诗人说:“好啊,你现在倒学我挂电话了你!”
我们在五楼的楼梯口,在一片漆黑中坐了好久,一直找不到话题。莫小帘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浑身都湿透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她松了一口气,白了我一眼:“你这人,真抠门,连开房的钱都要省。”
她说话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很浓的烟味。
“你抽烟?”
“我没有。”她矢口否认。
一种疑惑的迷雾蒙上了我的心头,在我眼前的莫小帘,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个无尽的黑夜,心思细腻的莫小帘走进去了,天亮了,却是一个不修边幅的莫小帘走了出来。
当回过头去,透过时光的茫茫雾霭,我只能轻声地说一句:莫小帘,此刻的我只是一个颤抖的人,凝视着你心中的羞涩和绝望。
8
在半坡村,蚊子几乎与空气同在,无孔不入。
我的血型显然很合蚊子的胃口,在这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地方,似乎只有它们最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也可以选择步行两公里,据阿婆说,那里有一家商店,里头有公用电话,但我似乎没有这个打算。
我的打算很简单——既然是为看海而来,我好歹也要去看看属于我的大海。我艰难地爬上了山顶,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四周树林阴郁,南方初冬的风正不紧不慢地吹刮着,所到之处树木俯首称臣。不远处,那一片碧蓝的水,被定义为大海。他们无休止地拍打着山脚下的岩石。
我突然觉得,我还年轻,我才二十九岁,但时间仿佛并不容许我再肆意妄为,我花了巨大的力气,为自己设定了最平稳的人生轨迹,在上面滑行,同时看着其他滑行的人,所有的轨道都是平行线,或多或少的攀比,但更多的是祝福,这些被定义为平行的幸福,它将耗尽我的一生。
面朝大海,我似乎想了很多,也似乎什么都没想。人类一思考,大海就发笑,涛声一阵又一阵,欢腾喧嚣,但不过也是一天又一天的重复罢了。重复大概才是生活的本质吧。
从半坡村出来,我恍若隔世。我开着我破损不堪的新车往回走,想着离家出走的莫小帘,会不会也到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呢?
这两天那帮孩子又爬上车顶,居然又把我天窗踩坏了。阳光灿烂,一路上我这身行头引来不少目光。把车开进4S店,无法取证,保险办不下来,维修费将花去我至少两个月的工资。我垂头丧气,自己坐公车回家。
推门进去,感觉自己用钥匙开门的动作都有些陌生。我这也算是一个离家出走玩失踪的人了,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我的妻子,她现在是熟睡了,还是在喂乌龟?
妻子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开始激动得大哭起来,接着又怒不可竭,大吵大闹。宣泄完之后,她瘫坐在沙发上,听我讲述整个过程。听完以后,她将信将疑起来:“没有去找情人约会?没有被海盗抓走?我的神,我连最坏的打算都有了!我已经报了案,联系了报社的人,准备明天去登寻人启事!”
她的手还在颤抖,并暗暗地抽泣起来。我看着她高高低低颤动的肩膀,心头不禁掠过一丝酸楚,这种酸酸的感觉一举击败了我在半坡村酝酿过的所有想法,这一刻,我才仿佛从天空中掉落到尘世,重新见到悲悯的大佛。生活告诉我们,只有大地才是踏实的。
我抡起袖子,把我手臂上的伤疤给她看。是的,要亮出伤疤,才是最好的证据。她大吃一惊,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你打了狂犬病疫苗了吗?”
一句话把我问傻了,我上网百度了一下狂犬病,登时崩溃。如果这样死掉,那也太惨了吧?我想起那条叫天神的狗,它脱了毛的红色的皮肤,仿佛他随时都可以从一个天神变成一个死神,把我拎走。自此,狂犬病像一枚定时炸弹一样安装在我的恐惧里,它随时都可能引爆,然后,砰地一声爆炸。
9
当恶之花慢慢绽放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她将开得很美,很绚烂,但却无法估计结果。我隐隐感觉莫小帘不对劲,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该来的总会来,保研的名单终于定下来,公示就贴在研究生院的外墙上,但看得人很少。只有我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地点过去,没有,真没有莫小帘的名字。所以,一个晚上,我都在等莫小帘的电话。有一种朋友,她必须在失败的时候才会走近你,形成交集,而在她幸福的时候,她就如一根平行线,你永远也找不到她在哪。
但是这一次,她没有给我电话。一连两天过去,她都没有来找我。我有点心灰意冷,看来,我在她心里已经贬值了。终于忍不住,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宿舍里的同学。我问:“她怎么样了?”该同学天真的对我说:“问情况是吗?抢救过来了,脱离危险了。我还在忙……”咔,对方挂了电话。
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话没说完,怎么就喜欢挂人家电话。重拨过去,我才知道,莫小帘自杀未遂,正在医院急救室里。
我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醒了。她躺在床上,看到我,眼睛里顿时全是泪水,打个转就流进耳朵里。她说:“你走吧,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但当我走过去时,她却又紧紧地抱住我:“你别走……他骗了我,他骗了我……”
她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她的谁,结果他们都很识相地退出了病房,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里交给你啦,有什么打电话啊。”说话的时候,都不忘打量一下我,这种被扫描的感觉真是怪怪的。
人都走后,莫小帘直奔主题:“徐可然,你是学法律的,我留了一条内裤,咱们可以告他,告他强暴!”她眼睛都发出绿光。
“告谁?”
“告……告……”她又突然溃缩了下来。
我将保研以及之前她身上浓浓的烟味联系起来,大概也可以猜出几成。
“是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抽烟的教授?”
“呸!我恨不得撕了他,还德高望重!”
“他答应你保研?”
她点了点头:“我是不是特幼稚?”
“嗯,很傻很天真。”我故意揶揄道。
我又花了三顿麻辣烫,才重新调整了这匹野马的心态,并平息了她上诉的想法,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对了没有。我买了些彩色的纸送给她,但她对我说,她已经不喜欢折纸了,她现在爱花花绿绿的彩票。
过了些时候,莫小帘突然漠不经心又开始了另外一段恋爱。我说她是抢在毕业之前,补上一段黄昏恋。她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0
据说狂犬病的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怕声、怕光、怕水,喝一点水就喉咙发紧痉挛,反正必死无疑。
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好像那条叫天神的狗还是比较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地方是它咬了我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有时两天可以达到长出寸许,我经常修剪,但它还是常会伸进嘴巴里。于是我只能在鼻子下面留了一撮小胡子以混淆视听,遮掩一下。仿佛那条狗没有长够的毛,现在全长到我鼻子里去。
毕业后我和莫小帘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直到去年夏天,莫小帘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老人家几乎是哭着哀求我,让我告诉他小帘的下落,我很诚恳地告诉他,对这件事,我爱莫能助。我认识的那个莫小帘,大概会像一盏白纸糊成的孔明灯,随着海涛声漂浮在天地之间的某个角落。
责任编辑⊙育邦
作者简介:
且东,原名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曾在《北京文学》、《山花》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宿命飘摇的裙摆》、《此外无他》,诗集《只能如此》。现居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