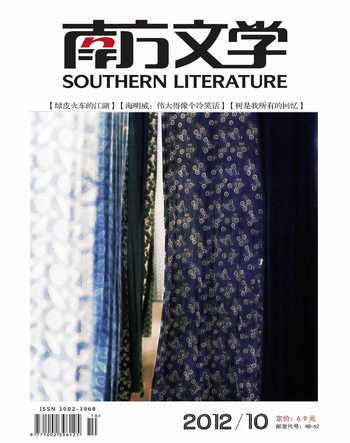格里斯海姆的尽头是田野
草籽
好似一世的乡愁找到了归宿,我再也没想过要离开这块面积仅有二十一平方公里的地方。
以貌取城
德国这个小镇,我先取中它的,正是它平淡无奇的外貌。
搬来这里前,已经在德国待了整整十年,这一次,因为是最后安家的地方,选择起来,便在能力范围内,用尽了心力。
我和我老公两个都是懵懂之人,在这之前也只去过两个地方看地,房子还在设计图纸上的那种空地,这是第三次,毛坯房刚刚完工。
进到房子里假装认真地看了一圈——因为既不是学建筑的,又没买房经验,真认真和假认真都差不多。跟建筑商礼貌地告个别,我便拉了老公往镇外跑。
“对不对啦?是不是这个方向?”他一向怀疑我的方位感。
“我是学什么的?还会把地图看错?”我走得起劲,迎着大风头也不回地说。
只大步走了十来分钟,穿过一条大马路,那片田野,那片一直延伸到天地交接处的田野便出现在眼前,我停下了脚步。
我是在那些奇山异峰、小桥流水的精致风景里长大的人,那让无数文人墨客失了魂魄的青山秀水也让我有深深的感动,不是不爱它们,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灭的竟还是一份原始和粗犷。一种从来只能在梦境里寄托给无边的草原和大漠的感情,竟在此时被唤醒,竟是在这里,这片能看到地平线的田野上,我找到了故乡。
这种心灵回归的震撼,没有语言可以形容。
这里的蓝天,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上。
田里种着玉米、麦子和蔬菜,另还有大片的草莓地,草莓到了成熟的季节。茫茫苍穹下,站着两个小人儿,面对着这肥沃而丰硕的大地,体会到今生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喜悦。
我们买下了这栋房子,住进来之后又慢慢挖掘出更广阔的一片天地。向北走是田野,向西走一刻钟,就是森林,那个里面又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便是兔子的耳朵都比田野的兔子耳朵小得多了,小鸟的品种繁多,都叫不出名儿;猫头鹰我也见过两只,地上跑的倒只有小鹿算大动物,兔子多得像老鼠,随处可见,据说是有狐狸,只是它们太害羞,是不肯让人看见的。向东去,要稍微走得远一点,是一片水域,总看得见两三只仙鹤、四五只大雁,还有一群野鸭子在尽情地鸣叫,声音高亢而嘹亮;也有鱼鹰,挺直了乌黑的身子飞过水域附近的田野,水域附近的森林里有野猪,黄昏的时候,听得见那带着凶猛兽性的猪嚎声。向北走十来分钟,便到了小镇的主干道上,交通是极便利的,有轨电车直通附近城市的市中心。这个小镇,各种设施齐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住在里面,不用出镇,生老病死,她全包了。
我是本地人
“你在格里斯海姆买房子了?那你就是格里斯海姆人嘛!”一个家住格里斯海姆的同事对我说。这么简单,我成了本地人。
“哪有那么容易,我们是外地人啊!”在北京的同学对我说。她去北京也有十来年了,外地人的帽子怎么都甩不掉。
还好,我的心从来不属于大城市。
纯黑的长发,眼睛没有凹进去,鼻梁没有高高挺起,我不用说话,走在街头,自然是一派东方风味,不要说外地人,我分明是外国人。可是我从未在路人的眼神里看到一丝一毫的异样,更不要说歧视和排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被完全接纳了。
每日里散步,我会跟每一个陌生人打招呼,问一声早上好,道一声日安,再不然会跟牵狗的老头聊上半天,连狗也认我做朋友,自己叼着网球找我玩。
散步要经过的篱笆边,天天见面的那个和善的女人,一头火一般的红发,走过她院子边,随便聊两句。会被她硬塞一挂香蕉、一袋苹果或其他什么水果到你怀里。等到我们把MERCI巧克力丢进她的信箱时,倒把她骇了一跳,她显然是从未想过有回报的。
还有很多,那个每天碰到的希腊老头,那群傍晚遛狗的男人们,那个对面高楼里住着的披着雪白长发的老太太,还有那个拿社会救济的只对亚洲男人感兴趣的女人,都成了街头熟悉的面孔。渐渐地,便是开车时碰到,也要招手打灯表示问候。格里斯海姆就这么成了我的小镇。爱她祥和安宁的气氛,对外面的世界,人情的冷漠,竞争的激烈,甚至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她好似打了免疫针一般,不受影响。
左邻右舍
拿根竹竿捅自家的天花板,还是拿把榔头敲自己家的墙壁?这种跟邻居交流的方式咱至少听说过,邻居关系最难处,即使在德国也一样,因为“远交而近攻”嘛!
总有人问我邻居怎么样,每次都能让我甜甜地笑起来。如果我停在外面的车子窗户没有完全关紧,邻居会来告诉我。关于房子的养护,他们只要自己想到了,一定会告诉顺带跟我说一声。出去度假时,很自然地把房子和院子都交给邻居,一大串钥匙放心地给人家,留一个手机号码,就出去天南地北地跑,院子自然有人天天浇水,房子里的植物也被侍候得好好的,重要文件我们是没有保险柜的,全丢在房子里,心里从来没有不踏实过。
能有这样的邻居关系已经很不错了,可如果仅限于此的话,这一节也根本不用写。
当年,建筑商在这块地方同时建了十四栋房子,大家住进来的时间相差无几,院子里铺草皮,修栅栏和搭放工具的小木屋时,邻居们常常一起在外面干活。因为谁都没经验,大家就互相交流信息,工具借来借去,就这样彼此很快熟了起来。
妮可儿是我左边的邻居,住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出出进进,一脸幸福,从未见她对孩子发过脾气,而从未受过训斥的孩子看起来那么健康、善良、大方,是绝对迷人的洋娃娃。
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工作的奴隶,好似将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卖给了工作,下班回来只剩下苟延残喘,所以总想找个角落躲起来,不愿意见人,更不愿意说话。
而妮可儿这时却要请我去喝咖啡。我答应了,心里有点忐忑,不知该带什么过去,便把窗台上的那只怪南瓜捧在手上。南瓜的皮自己烂了一个洞,从洞里发出一棵南瓜苗来。我走进她家,把南瓜奉上,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这东西给你小孩玩。”
“哦!我倒是见过。”她笑道,自自然然地谢了我,把南瓜接了下来。
她请我坐下,转身去厨房弄咖啡,又端出自烤的蛋糕。餐桌上没铺桌布,却用黄色的小丝帕和一小瓶插花点缀着,是专门为我弄的。
在这么安宁舒适的聊天环境里,我开始享受与人交谈的乐趣,这是一个跟我一样与世无争的女人,那种超然恬静,正是我最欣赏的品格。
说到邻居,不得不说说我跟弗兰克和他爸爸去小岛上通宵钓鱼的事。
那天晚上,弗兰克按约开车来接我,事先说好是跟他父子俩一起去的,我低头往车窗里张望,却没见着他爸,问他,他说:“爸爸开自己的车来的,我们已经到了那儿了,这是专门来接你。”
弗兰克那么大的人了,即使是对外人,也不说“我爸”而直接说“爸爸”,非常孩子气。
因为刚下了场大雨,小岛绿得叫人不忍心用脚去踏。
推开那两扇矮矮的雕花大木门,搬了东西走进去,一时间,我们好像进入了热带雨林。
过去跟“爸爸”打个招呼,弗兰克来帮我支帐篷,安放东西,一面对他爸高声喊:“爸爸,她有帐篷……爸爸,她有椅子,还有两根鱼竿……”
“爸爸”在那边发出满意的西里呼噜的声音。
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鱼来上钓。
月亮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它低低的挂在远方的树梢上,是橙黄色的满月,大得惊人。整个岛,岛上三个安安静静的人,河对面那些把天也挡去大半的高大树木,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好似只是一幅画,一幅在最美的瞬间被静止下来的画。
那天我只支撑到凌晨三点,一无所获,便去帐篷睡觉了,醒来时,已是早上五点。弗兰克父子钓了许多鳗鱼,他们好心地分了一半给我,被我拿回家一次性吃光,味道好极了。
跟一对男邻居在野外通宵垂钓,这在许多地方不可想象。而弗兰克和他爸爸给我的感觉就像家人,无需防范。
老汉斯的故事
老汉斯喜欢跟年轻女人聊天,他老人家眼中的美女,限于七十岁以下、打扮得整齐得体的女人。
认识老汉斯,是在合唱团里。
一个两万八千人的小镇有这么多的音乐团体,在我是不能想象的。合唱团就有几个:一个专门的管乐队,一个交响乐队,一个正规的音乐学校,一个舞蹈和戏剧音乐团体,还有一些零散的三、四个音乐高手组成的小乐队,一般便是演唱些流行歌曲。而这些,都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平,他们合在一起,开得出一台正规的音乐会来。
里面的人当然都是业余的,包括我。只是我,自打进入合唱团以来,真正开始体会滥竽充数的快乐,即使感冒了喉咙发炎,肿着嗓子,也要去唱歌的。
所有的音乐团体里,历史最悠久的还是我们这个合唱团:日耳曼歌手联合会 1881。算算吧,今年是2012年,整一百三十一年的历史了。
两次世界大战横切其间,而它在人口上居然是连贯的,汉斯和菲利普,两个八十七岁的老人,他俩的祖父就是这合唱团的创始人。
汉斯和菲利普的故事要从八十多年前开始,那一年,两个三岁的小男孩开始上幼儿园了。等读完小学时,战争就来了。
起先只在别的国家打,后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男孩子长到十七八岁时,德国男人已经在战场上快被打光了,稚嫩的汉斯和菲利普自然也一身军装,扛上枪,被送到了前线去当炮灰。他们去了不同的部队,那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分离。
仗没打几年就结束了,两个人居然都没当成炮灰,连个伤都没负就做了俘虏,汉斯去了苏联,菲利普去了美国。后来,绕了半个地球,他们又回到小镇,生儿育女,安居乐业。
那天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正被这两个老人夹在中间坐着。我们唱完歌一起在楼下一个很有情调的酒馆里喝酒,汉斯口若悬河,菲利普只笑眯眯地望着前方不知什么地方。
八十多年纯洁的友谊,真有点超出人的想象力,这样的故事大约也只能发生在格里斯海姆这样的小镇里。
在这里终老
小镇的故事是真真实实的生活,而我日日体会着平淡中涌出的喜悦,就如小镇的外貌,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是实实在在丰腴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人生真的很奇妙,十几年前,我没想到自己会跨出国门,如今,却已完全融入格里斯海姆这个小城镇,它已然是我的第二故乡。好似一世的乡愁找到了归宿,我再也没想过要离开这块面积仅有二十一平方公里的地方。以后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谁也无法预料,但此时,我是这么想的:我要老死在这片纯净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