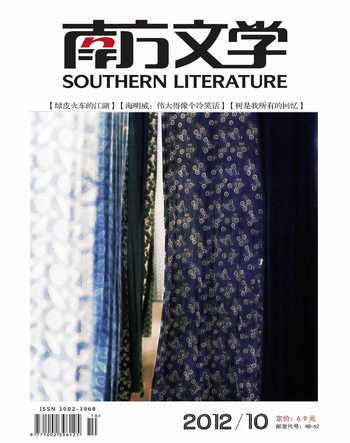为书消得人憔悴
老匪
一个男人竟然要靠妻子卖发换书,这让我情何以堪?
墸墸墸墸墸墸墸墸
发黄的旧书
1958年秋的某一天,二十多岁的母亲怒气冲冲,把父亲书柜里那堆有点发黄的旧书全部横扫了下来。书本噼噼啪啪地跌落,乱七八糟地仰翻在父亲卧室那有很多灰尘的黄土地上。殃及池鱼的还有父亲经常坐在屋前池塘边那驼背李树下悠然拉响的二胡,它在地上弹跳了几下,就“铮”地断了一根弦。
我那年轻的母亲发怒之后,就蹲到地上伤心地哭泣。
可是到了深夜,在队里集体劳动中累了一整天的母亲喂完牛之后,还是整理好那些书,重新整齐地放到父亲的书柜里,那把断弦的二胡也挂到了书柜的旁边。
我长大后和母亲拉家常,才知道,这事是发生在父亲去劳改的第二天。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六年后的事情。
父亲是文革前屯里唯一的初中生,写得一手好文章和楹联,但因为成分不好不能当老师而回家务农了。当年有人大放每亩几万斤的卫星,人们却没有饭吃,父亲和几个激进分子就反对,起初是口头的反对,继而仗着懂几个字,就贴抗议大字报。其结果是被抓被批斗,然后是劳改五年。但后来有老人却说父亲倒因祸得福,躲过了人们漫山遍野挖蕨根吃黄狗头(一种块根类植物)的苦难生活。在那个临时劳教场,父亲先是挖坑种树一两年,最后几年都是在饭堂里当厨师,期满回家,出现在屯人面前的父亲是白白胖胖的。二十多年后“处遗办”给父亲平了反,父亲就常在酒后说,当年我们是没有错的,谁都知道,挖地三尺都没有那么多万斤的粮啊。
父亲酷爱看书,他的书柜很特别,是自制的。父亲在卧室的土墙上挖了个长约四五尺、高近两尺、深一尽左右的洞,刷上石灰,垫上木板,就成一个小书柜了,也可以说是书窗。父亲的那堆旧书就摆放在那里面。山村都是烧柴火的,烟熏得厉害,那堆书就有些发黄。
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就开始从父亲的书柜里拿书来看。那些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幼学琼林》等等,还有一些文学类的。而我最爱看的当然是小说,诸如《红旗谱》、《醒了的土地》、《茫茫的草原》。这些书让我的童年充满乐趣。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堆发黄的旧书,也让我难以忘怀。
这堆旧书不在我父亲的卧室里,而是在邻居老条的床下。当年老条还是一个光棍汉,名叫中田,这好像是日本鬼子的名字,但他绝对是一个正宗的非常善良的中国南方山村的庄稼汉。
中田叔是一个勤劳而且力气蛮大肚皮也很大的壮男人,据他自己说他只在分谷子的那几天能吃饱。他在我们屯里也算是个文化人,年轻时远赴他乡参加“六九二七”工程修铁路,后来回队里当了几年记分员。分谷子的那几天,晚上社员们到他家记工分时,他会靠着那根桶大的椿木屋柱,用双手摩挲着滚圆的肚皮眯着眼睛打着饱嗝说,等下子等下子,让饭下到肚里再说。当年他还有一项得到众人称赞的发明:他家有半张牛皮常年丢在屋角,主要作用是垫底剁猪牛菜,某天,他将牛皮用石头压到我家门前的水塘一角,几天后那牛皮肿胀发软,切细慢煮,配上马蹄香之类的香料,就是上好的菜肴了。后来队干学了他这一招,把公家的几张牛皮丢到水塘里浸泡,几天后每家分得一份。那几餐美味,我至今难忘。
中田叔脾气非常的好,为人特别的宽宏大量。一般地,下雨天或是常日的晚上,屯人总爱到中田叔家聊天,可以说,他那四处漏风的房子,是屯人的集散地。不管他在不在家,屯人总在他那里下棋打牌或瞎吹牛。中田叔很爱讲故事,他嘴巴本来就有点歪,当眯着眼睛讲故事的时候,眉头一高一低地歪斜着,嘴巴就更歪,而且讲到兴奋处还常常溜下长长的口水。但小时候的我却很爱看中田叔的那张歪嘴巴,很佩服他的歪嘴里有那么多的故事。有一次,还读小学的我,乘着没人,终于大着胆子问,中田叔你的故事是哪里来的?中田叔起身就把我带到了他的屋里。于是,我就成了中田叔床下的常客,钻进那里找书看。中田叔床下大多是厚厚的小说,如《三侠五义》《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岩》《赵一曼》等。
我现在爱好文学,应该和父亲以及中田叔的那些旧书有关。
断脚的碗柜
那年十一月,父亲突然宣布说,暂停文学期刊的订阅了。
由于从小就受到父亲和中田叔那些书的熏陶,我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到高中的时候,我家已经是几家刊物的常年订户,记得那些刊物是《广西文学》《雨花》《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嗜书如命的父亲竟决定停订刊物,这让我很无言。我知道,父亲做出这个决定自有他的无奈,他和母亲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本来就够艰苦的了,那年家里又接连死了两头中猪,家庭经济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于是,坐在屯前晒谷坪边的石条上,我向继乐说到了这个事情。因为对酷爱文学的我来说,这事是个不小的打击。
继乐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铁杆粉丝。他很佩服我琴棋书画方面的天赋,每当我夜晚坐在屯前晒谷坪边的石条上吹笛子拉二胡弹弦琴的时候(当然都是父亲的乐器),他总是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后来他还跟着我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能吹拉出一些简单的歌曲。他也是我学画画时最佳的模特——这家伙的定力很好,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达半个小时。我虽然能把他画得相当的形似,但在神似方面却还欠火候。我总画不出他眸子里那深深的忧伤。他父亲是个精神病人,整天在阁楼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别的什么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他母亲在他父亲发病他还小的时候已经远嫁,下落不明。只有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还有小他几岁的妹妹和他相依为命。
我说完自己认为很痛心的事后,继乐想了想说,我借钱给你,不过没有现金,我们抬刚做成的碗柜去卖吧。
继乐爷爷当年是一个拉平锯锯木板的好手,他家三间宽阔的阁楼上堆满了椿木樟木以及不知名木头的板材,在继乐把这些木板糟蹋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他终于修炼成这一带比较出名的木匠师傅。只有十六七岁的他,已经能走村蹿户帮人家做木匠活,挣工钱维持生计。在没人请的空闲时间,他就把阁楼上的那些木板变成风谷车、衣柜、碗柜等家什出卖。
那天正是我们六圩的街日,于是,我们绑好碗柜,抬着往六圩赶。
从我们屯到六圩约有十二华里,当年那村级公路是相当的烂,它被中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挖得到处是坑洼。我们抬碗柜出去的那天是雨后的晴天,路上的坑洼里都是浑黄的泥水,我们不得不在石头上跳着前进。正是因为跳跃的缘故,那绑绳经不住折腾,“咚”的一声,碗柜就掉落在了石头和泥巴混合的路面上。一条“S”形的精雕细刻的碗柜脚断掉了。
继乐兄弟说不要紧,到街上找钉子把它钉上就行了,当然价格会低一点点。于是我们用水洗清碗柜上的泥,然后绑紧继续前行。
那天,我终于如愿地到邮电所订上了我喜欢的书刊。
现在,写这篇与书有关的小文,我自然会想到继乐——我那当年和现在都最要好的兄弟。如今,他在相邻的一个镇上租有门面,经营不锈钢、铝合金门窗,生意不错。
与书摊和书店有关的画面
现在的我有很多书。
这几年,我调动了几次工作,搬家时,这些书的搬移总是我亲自打理,其他的就由妻子全权负责了。
这些书,有一部分是从街头书摊上买来的。
我很佩服靠近大市场那条小巷里的一个湖南书贩,无论你在他那里看多久的书,他对你总还是笑眯眯的,而且还会尽量找凳子或砖头什么的给你坐。也许他相信,对于爱书的人,即使让他看一天,最后大多人还是会买走他的一两本书。是啊,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学书和一些工具书,即使你看了又看,也背不来,最后还是得把它买回家才踏实。这小老板倒是很懂读书人的心理。
相对来说,大市场圩亭下的那个本地书贩的经营方法,就不大讨人喜欢。他那里的客人非常少,你刚一靠近,他就会盯上你,让人非常的不自在。如果你一拿起书,他更是目不斜视了,似乎他已经运好少林气功,万一你拿书就跑,他立马穷追不舍。你只翻了几页,他就会问,你买不买?如果你回答先看看,他就会说不买就不要看了,伸过手来将书拿回去摆到原来的地方。他那里的书摆得很整齐,但卖出去的很少,因为很少有人不看里面的内容仅凭花花绿绿的封面就下决心买书的。在这方面,他真该向那湖南小老板学习。
让人头痛的是,书摊的书虽便宜,但属盗版,纸质粗劣,错别字太多,这跟好好的美食里面吃出沙石一样,坏了人的情绪。所以我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书店购买的。
提起在书店买书,不得不说说我的妻子。
妻子有一头飘飘的长发,乌黑油亮,发质极好。每次走在村道或街道上,她这头漂亮的长发会都引来路人的注目和赞叹。
妻子对自己的这一头漂亮长发也是相当的呵护,两三天就会清洗一次,这在乡下是少有的。有一次妻子赶街回来,骄傲地笑着告诉我,有个好像是城里来的婆娘,跟了她大半天,缠着叫她剪了长发卖给她,而且价格比别人同样长的头发要高出两三倍。妻子格格笑着说,我才不卖呢。
前年县城里的一个亲戚生病住院,我和妻子上城里去探望。从医院出来后,带妻子逛了一下商场,买了两个我一直想帮她买的发夹。妻子高兴地把新发夹别在自己的头发上,美得不行。
逛着逛着,我和妻子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新华书店。我这翻翻那翻翻,最后,对一套精装版的《金庸全集》爱不释手,有心想买,一看价格,居然要四百多块。我叹了口气,放下书,旁边的妻子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没作声。我在乡下工作,难得来县城一趟,乡下街道的个体书店没有这么好的书,但我们带钱不够,刚才在医院给了亲戚几百块钱,现在两人身上只有三百多了。
买不了,享享眼福也好。我又捧起书坐到一张小凳上,翻看着自己还没看过的篇目。
妻子小声说,那你在这里看,我出去转转。她说着就快步出去了。
我被金庸先生带入了险情丛生的江湖世界。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人一拍肩膀惊醒。抬头一看,是一个像妻子的短发女人,细一看,不是像,根本就是妻子嘛!只是,她的长头发呢?
妻子嘻嘻笑着对我说,把长发卖了,你买你的书吧。她说着把握在手里的钱递给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吃惊地看着妻子。看惯了她从少女时代就留起的长发,我还真的不大习惯她这一新的发型。
妻子笑着伸手拧了一下我的腰,小声说,看什么啊,不认得自己的老婆啦?莫担忧,过两年还不是又长了!
作为一个男人,居然要靠妻子卖发换书,这让我情何以堪?看着妻子的笑脸,羞惭过后,无尽的幸福将我包围。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要像爱书一样,爱我身边的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