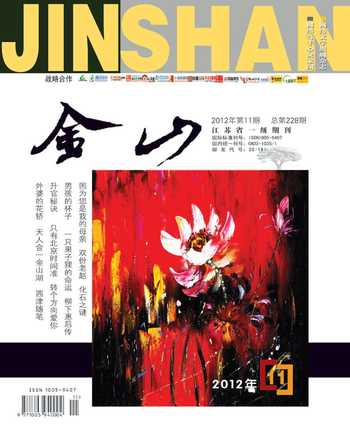苦难中的高贵
张峥嵘
我站在这座叫做“定福寺”的建筑旁,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为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自身那像谜一样的经历,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伯先路南端,是一个三岔路口,高高低低竖着一排排门面房,镇江现存最早的浴室“大兴池”就坐落其中。这些建筑大多已有上百年历史,虽然曾是镇江最热闹的地方,但随着火车站的东移,这儿逐渐成为普通的地区,前来光顾的人不是很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兴池”浴室对过找到了曾听说过的古定福寺。
从三岔路口一条小巷进去不远,就看见一座建筑,破旧的大门,杂乱的院子,虽然门口上方碑刻“古定福禅寺”还留存有几分的古朴和沧桑,撇捺间透露出深深的从容和安详,但破旧、杂乱的现象还是不能与香火缭绕的寺庙挂钩。尽管我看过较多的棚户区,但这所建筑所呈现的狭窄和简陋,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
最早知道“定福寺”,是看了王玉国先生的《镇江文物古迹》的介绍,知道该建筑位于宝盖路320号,相传此处原为灶君庙(也有人说是昭君庙),由一军阀小妾在此出家时重修。
历史上,有关漂亮女人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破败的建筑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怀旧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失去了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逝去的经历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这位落难时的女人——一位军阀的小妾。
她可能是一位像李香君的女人。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她也可能是秦瘦鸥笔下的罗湘绮的原型,师范女中的高材生,清纯美丽……
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这位小妾可能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窘迫的经济、遭人白眼的社会地位曾使她狠下一条心,追求有权有势的人作为她的终身伴侣,来实现她不枉为一生的誓言,但她实在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爱她的人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真,结果落得豪华生活昙花一现,最后流落到定福寺来了结最后的时光。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为什么追求幸福就变得如此困难窘迫了呢?如果每次幸福的追求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人世间人们追求幸福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过分地追求幸福的生活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经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期盼的自身健全?
二
想到这位女子的遭遇,我不仅默默地走出了定福寺的大门。
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这位不幸的女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沁人的世界。
在那痛苦揪心的日子里,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名字被这位小妾记在心里?有没有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去处被她输入心坎,并曾一度犹疑要不要去投奔来说一说自己的害怕?
那天早上,落难的她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外彷徨的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她留念,使她动摇?
不是还有友情吗?难道这位小妾风光时就没有朋友前来联系?
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漂亮的女人只不过是长在权势大树上的叶子,这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这位小妾的落难是一个探测仪,告知她与原先进入的那个层面的真实关系。当她敲开原先自认为不错的某一位朋友的大门时,看到的是临时的笑脸,看到的是索取和探询,等探询明白,彼此无法调和。她很快就明白,她的存在只能给这位朋友带来不安,而她妄想住在这里也非常的不安全。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黄昏的夕阳之中,繁星在天,眼前隐约只有一条出家的路。不必告别,不要留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快步离开要紧。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当事人落难之时,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落难人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
这位女人载着满脑子的迷茫,拖着踉跄的脚步,好似有无数尖针在刺痛着她的心灵,她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三
她来到了这座破庙,拿出仅存的私房钱来维修一番。在香烟缭绕的神佛塑像面前,她希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得到发泄与释放。
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流言蜚语时时出现。灾难使她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她一份宁静,使她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思绪如离云出岫,飘忽不定;时而又如飞瀑流泉,一泻千里。当然,其中不少是胡思乱想,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想什么呢?
一是想个人。回想个人的经历:单纯的童年,迷茫的青年,坎坷的现在;一生中曾有几个关节点,不同的选择可以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像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以议论处……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想得更多的是未来,如何在剩下的日子里平安地了此一生。
二是想爱情。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蹋;在这种赞美和糟蹋中,人们会渐渐成熟,有时会结识各种异性,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三是想友情。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了苦头。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
她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她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她却无意怨恨它,反而时常用温热的手掌抚摸它,让它感受人性至善的热量。
常常有一些妇女前来烧香,保佑她们外出谋生的亲人平安、生意兴隆,而她可能是她们当中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常常要给这些妇女读信、写信。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在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江苏的闯荡者又显得那么的重要。例如,定福寺向东荷花塘三羊巷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而且一当就是十几年,他叫陈光甫,有人称他是当时“中国的摩根”。但是,多数闯荡者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镇江,平生只有这位女人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附近居民的世界,这位不幸的女人快速地进入了附近居民的内心。而她也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我杜撰了这些细节,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这位女人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她是值得歌颂的弱者。
我站在这座叫做“定福寺”的建筑旁,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为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自身那像谜一样的经历,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