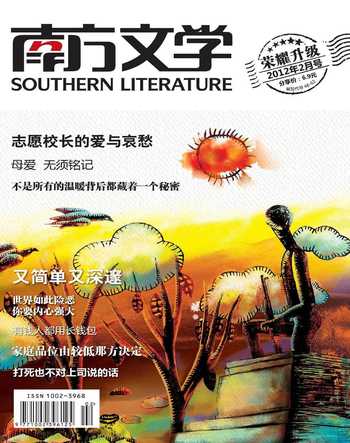一颗尘埃有多重
夏子
我就是一颗尘埃。你想想:一颗尘埃能有多重?
那时,我在一个理论杂志做主编,需要一个自然科学的专家做杂志封面,就想到了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他是这座城市决策层的领导,自动控制系的工科生,留美两年,留日两年,一生都在大学度过。我喜欢看他抽烟,也喜欢看他用英文朗诵诗歌,那姿态是矜持却又谦逊,儒雅却又幽默。
吃饭时,趁着酒兴,我说:“给我们的杂志撑撑门面吧,在这个行业,您具有引领价值。”没想到他倒过来给我沏茶、敬酒、夹菜,温声对我说:“对不起,我只怕要让你失望了,工作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做一些该做的事情。谈不上专家,更做不了封面。”我接茶不接酒,怪他不够意思,但其实我内心是懂得的。他宁愿把智慧学问灌进血浆里,埋在骨髓中,也不愿哗众取宠,附庸风雅。大概是怕我失望,他又酌满一杯酒,解释说:“我就是一颗尘埃,你想想:一颗尘埃能有多重?”
一刹那,我的思维凝固了,惊讶得没有说出话来,好久,我才挤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但这笑容里,满是崇敬。
他的言行击中了我,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浮躁功利的生活中久了,看到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会联想到所谓的梦想、荣誉、功名、权力,还有那些动听的声音、修饰的颜容、节制的欲望、奔涌的柔情。其实这些,都已经被尘埃笼罩,不复原本的面貌。
喝完酒,我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融化了,甚至产生了幻觉:漆黑的夜晚,苍穹下空无一人,我站在广阔的夜色里,突然觉得很孤独,想把以往都忘却掉,让自己也归于泥土,做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
我醉意渐浓,头脑却异常清醒:“看看我们的领导,都成哲学家了。”他就笑,但笑容里,有一种冷静的光芒,照射着我那不堪一击的孤独感。
之后,我们有了工作上的深度合作,偶尔也谈一些彼此的生活和他在国外的见闻。那时他正出版一本理论书籍,书店卖不了多少,全部堆在墙边,望着自己用毕生心血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却没有派上很好的用场,很是郁闷。他感叹:“中国人如果能接受我的观点,大范围内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像星巴克那样的管理模式,平民就有救了,经济就发达了。”我理解他的忧虑,他的抱负和观点,已经远远超前普通人很多年。
后来他从要职上退下来,再也没有在重大活动中出现,再也没有在公共媒体上露脸。他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学者,退下后拒绝所有的应酬,拒绝所有的兼职,拒绝所有的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邀请,在荔枝公园那栋并不起眼的办公室里,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经济学说。
我偶尔会抽空跟他去聊聊天,当他知道我在写影视剧本的时候,竟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劳拉的作品——《草原小屋》。这部作品在1970年代風行美国,几乎家户喻晓,可是没有中文版。他把作品翻译过来,并把《草原小屋》电视剧全部打上中文字幕,刻下来让我细细地看。他说:你写作品,要像劳拉一样,写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哪怕他们是一颗尘埃,也要写出他们的重量来,这才是我欣赏的作家。
这就是“一颗尘埃”的理论。
我们每个人,都是尘埃,都有着自己的重量,都在进行着高尚的劳作、平凡的坚守、默默的忍耐,并不离不弃,不灭不泯。正是这尘埃的集合,托起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