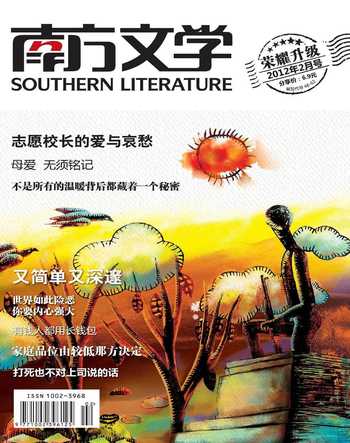你那里下雪了吗
渝李
花园里分岔的小路,没有被选择的方向。
雪坐在那里,白大衣,白帽子,发胖的小脸隐在热牛奶腾起的白雾里。气温8度,专家说今冬这座城比往年冷些,但我看雪,雪的脸颊晕红带醉,像初夏开出的蔷薇。
雪从仙女山归来,似乎也变了仙女,一颦一笑温柔至极,坚冰融了水一般。雪看着我吃点心,沾得满嘴饼干碎屑,她递纸巾给我时语带娇嗔,看你看你……捂住嘴笑,像小孩。
我们说起小时候,在她的闺房里做手工,新发的有着油墨清香的书本,她教我用旧挂历纸将它们包得四棱见方。扉页上,我用水彩笔端正地写上科目和名字,雪说我的字比她的漂亮。她在一旁给钢笔灌墨水,绕着彩字一个一个勾边。雪的刘海很长,细细软软在眼前飘,她用一种啤酒香波,后来似乎停了产。是这样吧,时光潮来潮去卷走许多,唯留下记忆片段像海边的风化石。许多次我想起垂首勾字的雪,乱发拂眼,她随手拿起钢笔帽朝头上一别,笔帽太重太滑,嗒一下掉在书上,溅出一点墨渍,雪将它画成梅花。
我与雪有时吵架,气急的我用圆珠笔画花过雪的娃娃们的脸,雪追着我打,追过长长一条街,追不上便隔着天桥吐口水,哭着回家。和好许久之后,我的模型飞机断了一只翅,经年后雪揭秘真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989年我写出刚劲颜体字,雪画着温柔水粉画,我最宝贝一套模型飞机,雪拥有好多洋娃娃。我们是如此不同,却并不妨碍彼此成为对方极要好的童年玩伴。酸梅粉打开有调羹两个,5毛钱不干胶上的周慧敏各分一半,草蜢和小虎队,那个叫黎明的帅哥——红蜻蜓去了哪里今夜你会不会来,当烦恼愈来愈多玻璃弹珠愈来愈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
后来小虎队唱我们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雪乘梦北去,此后再见,春风正渡桃花。有些陌生的雪,一口京片子,满嘴“咱北京”。雪有了男朋友,正宗帝都爷们,用我们的话叫纯种北京土鳖。雪说去咱北京玩儿吧,我那地方大,住得下。那年雪22岁,大三,和她33岁的男朋友住第三使馆区,后来有见地的知情人士告诫我们,这样看来不能叫那位土鳖啊,要叫也得叫声中华鳖精。
雪没有正式毕业,中华鳖精开小差,情敌斗法中,雪惨败而归。她依然留在北京,依然谈着恋爱,有一年冬天雪带新男友回家,我们一起去仙女山赏雪,雪如女王般将他支使得团团转。男人是长春人,在北京做电脑配件的小生意,经济上和曾经的中华鳖精云泥之别。他一次又一次陪雪玩雪爬犁、雪地摩托,摔倒在雪地上再爬起来笨拙得像只熊。熊伤了脚,依然为雪拎着包,雪没心没肺地笑,对所有的宠爱都视如寻常。
雪说爱情是刚性消费,享受过高端服务,再不能容忍路边摊。她对熊的求婚不紧不慢,依旧左顾右盼。也许雪刚性消费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就像1992年我们同在少年宫为外宾表演舞蹈,她第一次知道了Barbie,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提自己的洋娃娃。
2008年雪出嫁,不是嫁给熊。2009年,熊也结婚了,那天晚上雪打电话给我,疯疯癫癫乱说话,隔了一会儿有个男人抢过电话跟我说再见,我不清楚那个人是她老公还是熊。
去年春天熊有了儿子,雪正闹离婚。雪在Q上无限惆怅地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能怎么说呢,青春是用来犯错,往事是用来遗憾?亲爱,不是那样的。即使你也承认自己那些幼稚或虚荣,现实或贪婪,但我依然觉得,你所经历,不过人生常态。花园里分岔的小路,也许回首时都会对未曾选择的那一条心生怅惘,满怀不甘,即便眼前花好,也依然会惦记别处月圆。只是好在,你仍记得朝下走。
雪在秋天里怀孕,赶着生龙宝宝,离婚的事变成笑谈。有一次她老公出差过来,千万拜托我陪同去挑火锅底料。酸儿辣女,他笑要真是女儿,以后伺候两个女人就更伤脑筋了。他说雪的脾气还是一样坏,但安全值完全在他可控范围内,他说他对雪还像以前一样好,但女人嘛,你懂的。
雪在这个冬天回来过年,赶着去仙女山滑雪场,可惜有孕在身,只能过过眼瘾。雪的话少了,笑多了,笑容孕味十足。聊天告一段落,她给北京的他打电话,喂,你那里下雪了吗?我想她懂,花园里分岔的小路,没有被选择的方向——那个莹洁的世界,落雪纷纷,很美,很静,不要惊动它。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