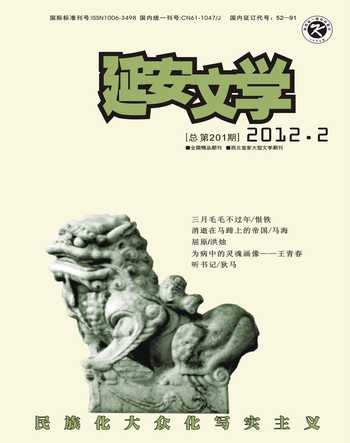人格病象:在乡土叙事中获得小说空间
刘全德
乡土叙事是鲁迅所开创的现代小说支脉的一大遗产,这一叙事的基本倾向可以用“尖锐”、“沉痛”等词语加以概括。“尖锐”是指它对现实的解剖一般而言是不留情面的,以致于有些作品在描写上达到了狰狞惨厉的地步;“沉痛”则是就风格而言,乡土叙事对悲剧事件和悲剧人物的发现、展览是其一段时间内战胜他种叙事风格的一大法宝。在不断变迁其美学面貌的前提下,乡土叙事一直扎根于社会底层,是近百年来小说史上延续路程最远、灌溉面积最大的一大流派,它强有力的现实针对性和欧化了的悲剧式风格也强有力地普及了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基本理念。
著名学者黄子平曾经详解过鲁迅的《药》和丁玲的《在医院里》,并发现了这两个著名短篇之间互相关联的内在机理,这就是现代——当代小说史上一直活跃的“病”的意象。“病”的意象,综合了、聚拢了乡土叙事的基本力量,体现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和强劲的生命力。经由“病”的意象的反复阐释,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小说生发、成长、成熟的策源地和主要传统。
而这个意象化的主题内在包含的人文主义意旨事实上直到现在仍未穷尽,一段时间里盛行一时的底层写作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它与传统乡土叙事在主题上的对接。我们知道,陕西是所谓“农村题材”的写作大省,对农耕时代造就的文明形态、文化取向、社会生活做出具有“宏大叙事”意味的文学概括是陕西众多作家的基础目标,乡土叙事于是成为陕西小说一以贯之的强烈兴趣。遗憾的是,能够深入时代变化了的生活现场,能够体察人性深处的波动并且及时作出准确回应的作家可谓寥寥无几。在底层写作的那个阶段,陕西作家在乡土叙事的推进上基本是碌碌无为地埋头过日子。
陕西作家仍然关注现实,可是看起来他们并不爱这个已经复杂到无法依靠常识去辨认的现实,也不愿意深入、深挖现实生活已经显露的财富,遑论以一己之力去创造真正属于艺术生活的那种高度独立的、辨析并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文本。“病”的意象的长篇著述者,现在还有贾平凹大力支撑,而在短篇小说领域,却是“大雅久不作”了。
前不久,在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王青春这里读到了几个风味独具的短篇,像《王二的鸡》、《黄昏的出走》、《看门者》、《谁在敲门》等都是内中翘楚。这些短篇,以“分而和之”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艺术世界。这些小说,分开来看好像平淡无奇甚至是未完篇的,不是缺窗子就是少门楼,但整体来看却又琴瑟和鸣,在无规矩中自成一派规矩。看似纷乱无章,实则和合一体。这些小说好像精心建造的房间一样,一环套一环,前一个房间没有的东西往往在下一个房间里就出现了。跳跃性强,呼应性强,三五个短篇小说看下来,犹如见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物的侧影。在这个套间一样的世界里,作者为我们提供的最主要、最频繁的意象就是“病象”。不是别的病,而是人格之病,构成了王青春这些短篇小说总体性的艺术发现。在乡土叙事的基础上,重新探索“人格病象”,这是王青春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艺术倾向。
《王二的鸡》写了一个叫王二的农民。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农民,也就是说,是一个得了“病”的人。是人的意识,而不是农民的心理在小说中活动着、冲突着,对人的“人格病象”的观察和表现占据了这个小说的主要篇幅。本来,在现代乡土叙事的小说出现以前,农民是顺民中的顺民,不思考、不反抗,不嚎叫、不痛苦,是经由意识形态的长期浸泡而驯化了的社会动物。在现代作家们笔下,农民的苏醒是普遍伴随着对自身生存惨状的发现而获得逻辑上的认同、情感上的共鸣。而在当代作家笔下,农民这一艺术形象除了罩上“悲惨”命运的老套,还经常性地跟着作家们一起陷入题材性的设定——这个庞大的人口群体仅仅是“农民”而已,一个符号化的、脸谱化的文学存在——农民(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一个意识丰富、感觉灵敏的“人”,他被剔除出去了,被典当为作家们进行农村题材写作时的一个证据,是用来“证明”什么的抽象概念。王二跟上述两种农民都产生了区别。他得了病。是可以称为“狂躁症”的精神疾患。
王二狂躁暴乱的生活源于他是一个人,一个内心里深藏了回忆、屈辱、不快乃至那种可以叫作痛苦的巨流,王二的心里时不时就卷起狂风和漩涡。你完全可以严肃地说,他生活在一个需要灵魂的世界里,他对灵魂悸动的警觉和审视甚至并不需要什么现实的因由。这一切只因为作者在叙述中出现了,作者把自己化身为王二的一部分,属于灵魂的那一部分。一个现代性的人(而不是穿着西装的农民),在灵魂尊严的需求下做出了殊死抵抗,他坚决不允许自己家的鸡跑到村长家下蛋,为此动了杀机,并把这个杀机变成“杀鸡”示威的实际行为。“也许从动了杀戒的那一刻起,王二就走上了一条让他也感到陌生的路,否则他的晕眩就无法解释了。王二端着那只方盘子,仿佛端着一件神器,走上窑侧那条平凡的小路,步态庄严。”(王青春小说《王二的鸡》)杀鸡后的王二,很快失明了,但这种与灵魂无关与精神疾患无关的肉体变化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王二失明了。
王二家里却没有那种悲苦气息,这或许因为此王二非彼王二,意志坚强,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和失明前一样下地干活儿,且对自己女人的态度更好了的原故;或许是因为失了明的王二听觉出奇地灵敏了,能捕捉任何细微声音的好处倒给这个家凭添了些乐趣。
……
王二只是奇怪自己瞎了眼,夫妻俩反而比过去更恩爱了几分。他也不明白其中道理,所以也不想着怎样让自己复明,凡是劝他去医院之类的话他都坚决地不听。
(《王二的鸡》)
接下来,他拒绝村长送上门来的低保,把这看作是包含屈辱意图的权力施舍,还担忧着自己妻子会因为这一类蝇头小利而丧失气节(怕妻子在村长那里丢掉女人的贞操是王二担忧的主要内容,甚至超出了“气节”问题的考虑)。最后,作为仇恨的高潮,王二给自己死去的儿子办了冥婚(在王二和村长的心理意识上,这场冥婚的女主角很有可能是村长的女儿),以至颠覆了这块土地多年不变的“天道”、“规矩”。
在这个小说中,权力引起人格扭曲,或者说,权力妄想症引起了人格扭曲,使一个人走向狂乱和暴躁。对家族式权力网络的破坏欲望,不只改变了王二的现实,也反过来改变了村长(王二心目中的权力掌握者)的现实。近乎于僵硬的乡村秩序,在王二的病理历史上被改写了。关于权力的诉说到此终止。关于驯化的冲动到此平息。王二以他家的鸡为半径,以压制他尊严的乡村权力代言人——村长王大为中心画了一个圆。在画出这个圆以前,躁动狂乱的精神主体经历了戏剧式的较量(以鸡为载体进行的自我心理折磨)、杀机四伏的冒险(由鸡到人必然越过的界限考验着王二的心理承受力)、两人角力抵在一处的反复拼斗(王二屡败屡战)、大团圆的结局(双方家破人亡后实现的冥婚复合)。
王二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与阿Q的新型集合体,始于狂躁症发作,终于大团圆式的悲剧圆满。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人格的病象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王二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记忆中的乡村是20世纪二十年代的,也是21世纪时尚化色彩无所不在的第一个十年。
王二们注定要和灵魂革命的死敌决战到底,王二们注定也会画出一个像阿Q一样的圆。阿Q在公堂上捡起的笔,和王二呕心沥血养活的鸡,担当了同一个任务,就是为生病的灵魂画像。
在另几篇小说里,《黄昏的出走》有一个披上了知识分子外壳的王二,即患了自我压迫症的故事主人公“我”;《谁在敲门》和《看门人》写了臆想症患者,“门”的意象耐人寻味,与“门”有关的人都自闭其中,在现实人际网络的逼迫下臆想着一个广大、完美的世界;《王三愚的瓜》写的是集体的疯狂,令人震惊的过去蔓延到今天以后产生了写作上的激情,“瓜”在陕西民间方言中又是一个隐喻性的词汇,代指那些愚蠢呆傻的人物(比如“瓜怂”之类)。王青春还写过一个原名为《更年期》的长篇小说,更是把某类乡村人物的人格病象上升到民族性格的高度、人类学高度,企图以一种诗意化的观察去描述这种精神早衰病象。
无往而非王二。无往而非人格病象。无往而非乡土叙事的范畴。
王青春是一个有着自我审查倾向的小说作家,追求一种严肃、庄重的文学风格,也追求一种尖锐、锋利的心理解剖,他所赞赏的作家是鲁迅、卡夫卡、路遥这样的人物,而他的创作出发点也在这里。他渴望突进人的内在心理世界,并在那里插下自己的文学旗帜。这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决定了他属于一个沉重的写作者序列。在艺术的入口,在命名一种将要描写的精神疾病的时候,王青春颇近于茅盾的习惯,以象征性的事物去点化主题;而在行文和结束的关口,王青春则走上了鲁迅乃至卡夫卡的路子,尤其是在细节上的苛刻求全、主题上的呼应关联,与那两位都是很相似的。
王青春的小说在陕西的短篇小说界是立得住的。他的小说,有寓意,有生活,细节出彩,讲求叙述上的节奏感,最擅长把细节交织到一个理性化极强的框架中,从而产生一种言外之意——象征化的艺术构思是他最常用的构思方案,再由一个细节入手切入到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上。作为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他的小说内容较为稳定、规整地划分了虚与实的比例,这种比例是茅盾式的:理性大于感性,现实多于虚幻。如果要对此挑一点毛病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某些时候,他的小说的虚写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理性化过强的写作方案的人为调整,故而显得旁逸斜出。在《黄昏的出走》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心理意识的某种错乱、纠结,某种由此而来的艺术秩序上的模糊,也许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说它突兀也好,说它灵光一闪也好,总之在行文中起到了某种意料不到的破坏性,还没有能够和一个艺术整体结合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当然,这并不是某一个作家个人的问题,而和小说艺术的本性有关。在小说领域,仅就技术层面来说,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有时候是存在冲突的,需要不断地在某一关节点上作出一些缝合、弥补、粘连的工作。也许,对于理性较强的作者,这种遗漏有时候是艺术追求上不可避免的代价吧。
关注有着乡村背景的人物心理世界的病态成分,这是王青春的努力所在,也是他创作展开的基本倾向。有这几个别具一格的短篇,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更大期待。
人有病,天知否?一个延续百年的疑问将在王青春的小说世界里得到完美展示。陕西小说,将在这里揭开新的一页。
栏目责编: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