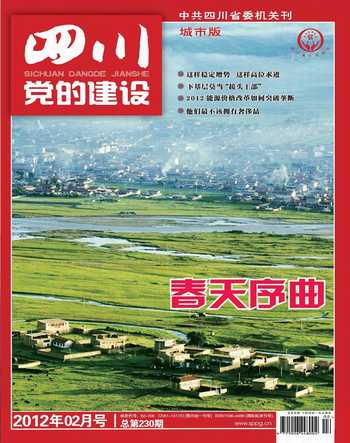四川曲艺:离我们有多近
陈庆 张岚

四川曲艺发源于民间,根植于大众,并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国曲艺界独树一帜。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四川曲艺、重铸辉煌?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一级编剧严西秀。
“不仅仅作用于人的耳目,更要作用于人的心灵。”
记者:严老师,您与四川曲艺结缘数十载,请评价一下目前四川曲艺整体的生存状况。
严西秀:挑战严峻,机遇宝贵。四川曲艺和全国曲艺基本一样,发端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遭遇“辉煌不再”的失落与孤独,这是曲艺不得不面临的挑战,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来调整。我相信当今社会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基层人民群众中,对于那种长在“根”上的、与自己血脉相亲的艺术形态的亲近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再加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发展的决定,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是曲艺发展的宝贵机遇。
当下四川曲艺总体情况是“群众红火,专业艰难”。究其原因,恐怕与“一个是乐生手段、一个是谋生手段”不无关系。
在理县“嘉绒藏区第一寨”甘堡藏寨,流行着十分壮观的大型锅庄“博巴森根”。它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在跳舞中讲述、传承了一段悲壮的爱国历史。更为可贵的是,这竟然是在娱乐中完成的。四川唯一的“中国曲艺之乡”岳池县,每天夕阳西下之时,几千人在陆游广场跳曲艺“坝坝舞”——莲厢、车灯;十几所曲艺特色中小学校的孩子们,“课间操”跳的是车灯、莲厢。这些传统项目,在民间都以“乐生”的方式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而四川的专业曲艺方面,目前只有省团、成都、自贡、巴中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团。尽管活得艰难,大家仍在努力,不时也有新的精彩表现。四川曲艺人,几乎囊括了中国曲艺所有奖牌,且获奖者有年轻化趋势。
记者:这些年来,四川戏剧在努力“突围”,不断尝试新的发展道路。四川曲艺要生存下去,甚至“活”出精彩,需要做哪些工作?
严西秀:最近,我连续观摩了在绍兴举办的“中国曲艺节”和在重庆举办的“中国戏剧节”,感触良多。曲艺也好,戏剧也好,要想活得更好,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认为四川曲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不仅仅作用于人的耳目,更要作用于人的心灵。“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于曲艺尤为重要。反之,无论多么的稀奇古怪、花里胡哨,无论如何超豪华时髦包装,脱离了“三贴近”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死路一条。
当然,“三贴近”绝不是“写中心,唱中心”的政绩文化,文艺应以“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为己任,无论文化官员还是我们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十分清楚,十分清醒。
“无论结果如何,抢救都是必要的。”
记者:目前,四川扬琴、四川清音等曲种都进入了“非遗”行列,这对于四川曲艺来讲意味着什么?
严西秀:一个曲种一旦进入“非遗”,国家将有具体措施予以帮助。如果这些措施得当且能真正落实,对于帮助其健康、延伸其生命,至少留下其“脚印”都会有好处。另外,一旦评为“非遗”,也是社会和政府对这一曲种多种价值的肯定。
一个曲种和一个人一样,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有益地存在过,那么在她行将告别之时,后人必须做一些事。即便面对回光返照,都有预感而又都盼奇迹。无论结果如何,抢救都是必要的。
记者:四川曲艺是否也是个不固定的概念,有推陈出新,不断产生新曲种、淘汰老曲种的可能,从而使“四川曲艺”的内涵能有变化,不至于干涸?
严西秀:曲艺是一个庞大的、动态的体系,曲种之间差异很大。发展变化中,一些曲种兴盛、一些曲种衰亡、一些曲种诞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琵琶弹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南坪(现九寨沟)民歌弹唱衍变而来的。同时南坪弹唱依然存在,二者相行不悖;李伯清的散打,由评书衍变而来,亦与评书相行不悖;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闵天浩、田莱农(田长青)、矮冬瓜(林小东)、胖姐(钟燕平)以及“中江系列”演员们不同风格与韵味的表演,都是新时期四川曲艺的新收获。
只要我们有包容之心态、乐观之精神,爱护后辈、提携新人,不怕并且真诚期望他们把我们“打在沙滩上”,四川曲艺在总体上就不会干涸,更不会消亡。
曲艺发展之路:回归本体,与时俱进
记者:时代变迁,曲艺受众有所萎缩。四川曲艺有没有再次走进大众的可能?未来各曲种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严西秀:曲艺根在民间、魂在江湖。古今中外,曲艺都不是“高雅艺术”,她是大众自娱自乐的产物。只是在发展过程中有文人的介入,使一些曲种、曲目产生了“高雅”的感觉。但这并没有改变曲艺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属性。例如,李伯清的散打,在川、渝、云、贵“川语区”拥有众多观众,在四川曲艺史上盛况空前。
曲艺发展的根本出路,我认为是八个字——回归本体,与时俱进。
当下的情况是,群众红火专业冷。我们更应多关注群众文化中的曲艺发展。泸县农民演艺网,聚合了一百多支农民演出队伍,利用网络走向广阔市场。红白喜事、开业促销,2000多地道农民每年创收几千万。在“中国曲艺之乡”岳池县,一百多支群众曲艺演出队,几百上千人的莲厢队、车灯队,久演不衰,蔚为壮观。金牛区文化馆的曲艺创作演出,非常活跃,连连获奖;成都市、岳池县、遂宁市已经涌现出了不少“曲艺特色”的中小学校,由省曲协组织专家开设各种曲艺特色班;成都市大学生曲艺联盟,哈哈曲艺社在校园、在网络上异常活跃……所有这些,说起就让人激动,想起就让人欣慰。事实上,正是强大而广泛的群众性曲艺活动,继承和发展着曲艺事业。
记者:四川曲艺要“保鲜”,需要出现新的人才。严老师如何看待当前各曲种的人才培养状况?
严西秀:这个问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曲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曲艺人才史。一个曲艺名家撑起一片天空,如果他再用心地教一拨用心学的徒弟,这个曲种就繁花似锦。四川清音、四川谐剧就是典型的实例。当前四川曲艺,在创作方向上出现了新的可喜现象,一批年轻人满怀热情地进入这一领域,青黄不接的窘况有所缓解。他们共同的优势是“四高”:学历高、悟性高、起步高、热情高,这在曲艺历史上从未同时出现。共同的劣势是“三不熟”:不熟悉观众、不熟悉舞台、不熟悉传统。而这“三不熟”基本上是初学者的共性。他们普遍是大学生、研究生,从写诗歌、散文且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进入曲艺。文学创作的ABC 都懂了,曲艺创作的ABC还需学习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脱颖而出;再假以时日,就会有大面积丰收。
创作是文艺活动的中心,剧本是一剧之本,围绕这中心和这个本,就能带动起整个艺术活动的繁荣。当然,要做的事还很多,任重道远。让我用《金龟颂》来结束这篇采访吧:
“负重不累,道远不畏。快快地慢慢走,不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