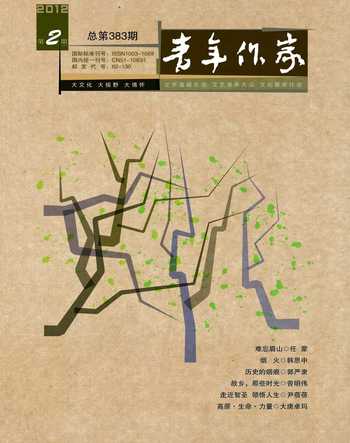枪
邹廷清
今晚,月亮爬上竹梢的时候,我要结束一个人的性命。
能毙命在金枪下的人,除了杨柳河沿岸七个码头的舵爷,谁还有这个资格?嘿嘿,既然码头上的各色人物都知道我们的存在,先给你透露透露自家的身份倒也无妨,免得你认为我是在乱吹牛皮。我们是维护码头秩序公正的终极执法者;我嘛,就是第四代金枪的掌管者。
然而,自从祖师爷与鱼凫桥的余姓、黄水镇的黄姓两大豪门的老祖宗死后,我们就只是活在一纸契约上的影子了,过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日子。唉——!谁让我师爷在执法的四十年里杀了三个舵爷呢?但如果你打算要掏出我就是金枪掌管者的真实身份,即使把爱走火的高射炮顶在我的脑袋上也没门儿。因为从我的师爷开始,各个码头的舵爷们都费尽心机想要把我们挖出来——或是控制利用,或是干脆除掉。
我师父本该好好地把金枪掌管到手指扣不动扳机那一天的,但鱼凫桥码头的胡姓舵爷拒绝在金枪下领死而招致家破人亡后的第七天,他却突然宣布金盆洗手,把金枪传给了我。唉——!真拿他老人家毫无办法。
我祖师爷就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他是余、黄两大豪门决定共同掌管杨柳河水运之初就共同选定的第一人。
还是继续讲我怎么去杀人吧!
出门之前,我仔细把枪擦了个干干净净,将三两八钱纯金霰弹倒进填好火药的枪管,再揉一小团草纸塞进去堵好,最后将一片硬纸板垫在抖好炸药的炮台上,松开扳机,合上机头,把枪往肩上一扛。
是的,我该出门了。虽然时辰是我定的,但要是我迟到了的话,这个法就算执过了。该死的人就会颠动着屁股人间蒸发,去远离故土的码头隐姓埋名,活到寿终正寝。还有,我之所以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擦枪,倒不是今晚金枪要重现江湖,而是领死者与我有那么一点交情。虽然他的双手沾满了不该沾染的血腥,但我还是想让他死得干净一点。这执法嘛,也该要有点人情味不是?
我肩上的这支金枪,从祖师爷一直传到我手上,铁定要三天擦一次、一月放一次空枪的。露在外面的枪管是纯金的,但被我的师爷涂上了黑漆,与乌木枪托浑然一体,要不是形状十分的古怪,看上去与其他短管鸟枪毫无区别。
用三两八钱纯金做成的霰弹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对于码头舵爷的身份,是一点儿也不奢侈的,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钱财还不如臭烘烘的粪土呢。之所以要精确到八钱,也不是为了衬托领死者身份的高贵,而是源于成都坝子的俗语:七上八下;七不出八不归。
然而,三两八钱纯金霰弹还有更歹毒的用处,这个我得先卖个关子。
大年刚过完,我出门的时候,天地间已降起了浓浓的霜,虽然看不见,但裸露在外的肌肤却能真实地感受到。那感觉就如无数的小针尖在轻轻地刺。满世界冷色的灰亮中,我甚至能听见树上的树叶和路边田地里的菜叶在冻硬过程中的坚挺声。那声音犹如巨大的昆虫在啃食软体动物:“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
我走在杨柳河的西岸,把东岸切割月亮的如枯死般的柳枝虚化开去,就能完整地看见有半竹竿高的月亮了。今天是正月十六,月亮虽然浑圆,却不似往年的白白胖胖,微红中透着轻淡的紫色,周围环一圈黑的晕,像极了在石灰中烧熟后平剖开来的半个巨大的鸡蛋。
我师父说如果出现这种天象,三年之内一定会发生大的灾难——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好在出门时自家的那条狗没有冲我狂吠或扑上来咬我,要不我就会去邪想这天灾或人祸会不会降临在到自己身上。
你可以不信这个,但我却十二分地相信,因为我师父的儿子在十八岁那年秋天,出门时被自家那条很乖的狗咬了小腿,结果好端端地走在平整的路上就跌了一跤,被路旁一根尖尖的小树桩戳穿喉咙死了。
杨柳河的水流声很轻,轻得像怀春的少女在无人处随风而起的情歌——娇羞却撩人心弦。河面上生出淡淡的雾,先是丝丝缕缕地连接,然后在两尺高处飘浮成一片,纱般的轻巧透明,却不往岸上蔓延,就那么柔情地轻弄着娇羞却撩人心弦的流水声,浪漫得跟仙境一般。
河两岸能目击的人家都熄灭了温暖的灯光。隐藏院落的树木于是就绵延开去,在若隐若现中朦胧得似浅山的影。除了出远门必须要赶回家的人,这个时候是很难碰上一个人影子的。我虽然走得极轻巧,但翻动的脚步在薄霜上踩出的“嚓咕嚓咕”声还是被近处耳灵的狗听见了。它们都懒得动窝,就那么趴着扬起头来象征性地叫上几声了事,其他听见的狗是不理会这种叫声的,因为明白毫无意义。但若是有一条狗发出了凶狠的狂吠警告,远远近近的狗就会在附和中把叫声连成一片,让正经夜行的人也会生出作贼心虚的感觉来。
正好端端地走路,第六感中就有了一个人影,是从前面远处的一棵曲柳树干上分离出来飘到路上的,然后迈着轻盈得似乎离地的步子迎着我走来。我说过那是感觉,因为当我能真实地看见有人对面而来时,那人影己在离我一丈远的地方了。
是个女子。一身雪白的衣裙,一束长长的秀发从背后拢在胸前。要是按照规矩的话,她是该让到路边等我先过去的。但她却把这规矩当成了一坨狗屎,直直地对着我走来。眼看就要撞上了,我只得往路边闪让。
虽然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凭那身段必定是个美女无疑。我看着从面前要过去的女子正这么想时,突然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么冷的天,她居然穿着一袭蝉羽般透明的衣裙,以至于让我在若隐若现中看见了她靠我这边的那个丰满的乳房与暗红色的乳晕……随着心尖上“轰”的一声炸响,我的头皮在一麻一紧之后,身上所有的毛根就竖了起来。我是不怕鬼的,但那是在没有见过以前,现在突然碰见了,才发现即使是这么漂亮的女鬼也是如此的可怕。
可能是我的恐惧被女鬼感应到了,她停下来转向我问:“你知道我是鬼魂了?”见我赶紧摇头,便用一只纤细小巧的手捂住樱桃小口“嘻——”地笑出声来,然后把一双手从胸部轻轻地抚到大腿,身上的白色衣裙就不见了,她把胸前的那束长发拢到背后,张开双臂在原地轻盈地转了一圈:“我是你这生中注定要看见的唯一的鬼魂,之所以要你完全看清我的裸体,是因为我的圣洁能洗清你的罪孽,会帮你度过今世最大的一次劫难。”
就在我拼命点头时,女鬼却空气一般消失了,只在我耳际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那笑声我好像在昨天听过,又好像在前世听过,更好像在根本没有到来的以后听过……我猛地打了一个激颤,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仍然好端端地在走路。虽然女鬼的样子和声音还留存在视觉与听觉中,但我却认定刚才是走神了,因为最近几天我老是在白天走神。于是开心一笑自语道:“人见稀罕事必定寿命长。我居然把女鬼的裸体看了个一清二楚,真是稀罕到天上去了!有趣,有趣!都说人霉碰见鬼,鬼霉撞见人,这两个
‘霉字相互抵消后,我不就要红运裹身了?”也不回身去看,轻哼着川戏段子又往我要杀人的地方走去。
玉石堰高高耸立的堤埂下,有一片近二十亩大的乱葬坟地,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全是密密匝匝的坟堆(很早以前是,而且是坟挨坟,棺材重棺材,这跟玉石有关),现在能看见的坟堆不但稀稀拉拉,而且圆滑平缓得根本就不像坟的样子,更像是农户去年种南瓜或土耳瓜随意垒出的小土堆。
由于坟的主人都是些客死异乡者,自然就没有亲眷来上坟培土了,春季,满坟地长出闲花野草,绿油油的,俨然就成了天然牧场,远近的牛都赶来啃食;冬季霜冻之后,随着最后一抹绿色的消失,整个坟地便在凄凄惶惶中枯黄成了一片。来不及等来过大年的欢乐,顽皮的小儿们便偷了家里的火柴,在雀跃中将枯黄变成随风狂舞的火海,最后留下一片焦土,任由未燃尽的剑茅主干在刺骨的寒风中指向无言的苍天,摇曳着无人问津的孤独。
玉石堰的上、下首,原来有两棵柏树对望而生。三年前,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传回胜利捷报,所有川人无不欢欣鼓舞。为慰劳前方将士,爱国的商贾与百姓纷纷解囊,各地的川剧名角更是奔走相告,要组织一个阵容一流的川剧班子去前线慰问演出。灌县在所有戏班中精挑细选了九个台柱子,加上四个车夫,带着一应演出用具和全灌县捐赠的慰问金,向晚时分一路吹吹打打地出发,要到成都集中。谁知那十三人在途中却消失了踪迹,就像一粒随风飞扬的尘埃消失在了上接天下连地的空气中一样。三天后有渔夫在新津县黄水镇捞起了三具像充了气的赤裸女尸,于是通过各个码头把消息沿杨柳河往上游传递。通过辨认,那三具女尸就是灌县的三个川剧名角。
省政府勒令沿杨柳河各县政府明察暗访了三年,结果却一无所获。
那是一个盛夏晚上发生的惨案。可能就在惨案发生后,成都平原突然雷雨交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雷把玉石堰下首的那棵参天柏树连根拔了起来——在黄水镇发现尸体之前,整棵柏树已被附近的人连根带枝分割而去,能烧的当了燃柴,能用的做了家具。而上首的那棵巨柏在七七四十九天后,朝下的那一半树干与树冠干枯了,另一半却仍然茂盛地活着。人们认定有神灵附在了树身上,远远近近的虔诚者在菩萨生日的那天都来烧香敬拜,并在树身上系满了红布。
我要杀人的地点就在那棵巨柏脚下。
现在,我已站在了柏树下,面朝月亮。树的巨大与我的渺小在月亮的逆光中形成强烈的反差。我把枪举过头顶,再横放在后肩背上,就那么反着双手把手腕搭在枪管和枪托上,潇洒得跟守护巨柏的稻草人一般。
正好是我定的时间。
身后的堤坡上传来小石子滚动的声音,是我要杀的人穿过坟地上来赴约了。我就那么面朝月亮站着,一直等到上堤来的脚步声停在身后三步远的地方。
“我来了。”身后的声音显得十分的淡定。
“但你迟到了。”我没有要转身的意思,因为我拥有绝对的主宰权。
“月亮有圆有缺,竹子有高有低,是你来得早了。”身后的人咳嗽了两声,是被烟呛的。
“有道理!”我喊了一声,然后慢慢把身体转过来。
他没有与我和月亮站在一条线上,所以那张脸就完全暴露在了月光下,虽然朦胧,我还是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脸却在月光的阴影里。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的模样分辨出来,接着嘟哝着不知骂了一句什么后,用恨不得把自己脑袋拧下的声音说:“怎么会是你?!要是我早三天知道,我们就该交换位置了!”
“怎么不应该是我?”我得意地笑了起来,“早就知道要尿床,你干吗还要去喝那一缸子水呢?”
“我在暗中挖了你两年多,为的就是不想让今晚的事情发生,可你却人模狗样地隔三岔五还与我喝茶吃酒。”他也轻轻地笑了一下,却笑得十分勉强,“那时正缺钱,我把各个堂口的公款输了……”巨柏树上的一只鹞鹰突然拉下一泡屎来。这个吃红肉拉白屎的家伙是不按常规下屎的,而是一跷尾巴往后激射,正射在他的鼻子上。他没有恼怒,先用手把鼻子上的屎捋去,再用手帕揩干净脸和手,将手帕丢在地上才又接着说,“很多人都在等着我的屁股从那把交椅上挪开,这你比谁都清楚。”
“清楚。”我把枪从后肩背上拿下来,把枪管倒立着,轻轻杵在右脚背上,“要不是你与你的兄弟伙挖我挖得太露骨了,我还真查不出是你带人做的这宗悬案。你犯的是这把金枪要执行的首罪——汉奸罪。天怒人怨呵……”说到这里,我咳嗽了两声正言道:“不是愚下言语陡,大哥将令不自由……”
“算了,别再唱那‘开山令了!我背得比你还要顺溜。”他有些不耐烦,打断我问,“你能告诉我到底是谁卖我的吗?”然后把头仰了起来,像是要在“呜呜”的河风声中用眼睛去丈量巨柏实在的高度。
我把枪提起来,深深地吸了口冰凉的霜风后说:“时辰到了。”
我的话显然让他感到很是失望。他慢慢地垂下头,转身时嘟哝着说:“这是他妈的什么兄弟伙!抢钱有他,强奸戏子有他,丢人下河有他,分钱有他……”突然问我,“我能不跪下吗?”
“不能。”我知道这是他想要的最后的尊严,但我不能满足他。既然有了规矩就一定得按规矩来办不是?“要是你铁了心不想下跪的话,现在就跑吧,我不会阻止你的。”
他背朝着我摇了摇头,我看得出那头摇得十分的哀伤。他跪了下去,但却跪得腰身笔直,好像后面要来不是枪弹,而是一阵轻拂岸的河风。
我提起枪,掰开机头,拿掉垫在炮台上的纸片……就在我毫不犹豫要扣动扳机时,他手中的枪响了,子弹从后脑穿出,混合着血液的脑浆热乎乎地溅得我一脸都是。更可恶的是,他并未立即扑倒在地,而是仍然那么笔直地跪着。
这个江湖老油条!居然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趁转身跪下时从腰间拔出了手枪,把枪管塞进嘴里扣动了扳机,并在枪响的同时发出了令我很不舒服的得意的笑声!
“你真他妈的蠢到家了!”我看着他的后背恼怒地说,“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个全尸了?你什么都可以侮辱,就是不能侮辱这把金枪!它既然已经现身了,就得完成它的使命,你就是在自己的头上打出十个窟窿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骂完,我手中的金枪“嗵——”地一声响了,枪管里的三两八钱纯金霰弹全部射进了他的后背,至少有十粒是钻进了他的心脏的。
然而,枪响之后,这个顽固而又自以为聪明的家伙,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极不甘心,还是那么跪着,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致,本想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的,但拼命忍住了,仰头向天愤怒地吼了一声后,提着枪顺着玉石堰往下游走去,到第七步时才听见他身体扑倒在地的声音——沉闷而实在。
我希望刚才的那一枪之后,金枪就再也不要重现江湖了。
但希望归希望,这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是人尽皆知的:况且,写书之人是以挖人祖坟、出卖秘密为能事的。
谁他妈的知道身后的事呢?
但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当我往回走到碰见女鬼的地方时,真的就听见了身后乱葬坟地传来的鬼魂的哭笑声:“呜呜呜……哇哇哇……嗬嗬嗬……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