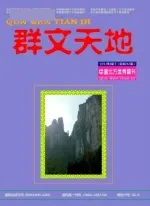谈“花儿”的文学特色
杨正荣

“走苦水别喊乱弹,走碾伯别唱少年”。这是一句相传的古话。清朝时,我们青海是属于甘肃省的,清在青海的行政设治是农业区一道(西宁分巡道)一府(西宁府),三县(西宁、碾伯、大通),四厅(循化、贵德、丹噶尔、巴燕戎),我们民和、乐都是一县,县政府设在碾伯。民国十八年分省时分开,乐都县县府仍在碾伯,民和县府设在古鄯。从以上的话里说明,青海是民歌的故乡,是产生“花儿”的窝窝。“花儿”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用来反映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爱情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好庄稼三种三磨哩,山药里点黄豆哩;好夫妻三说三笑哩,少年俩解忧愁哩。”“一对儿白马进西海,轻风儿吹者个雨来;一听见花儿把头抬,精神儿又不由地起来。”
“花儿”又叫“山歌”,又叫“少年”,顾名思义“花儿”是人间最美好的象征,是诗意达到最高的境界,从而她又代指青海高原妇女的美丽形象。这是因为传统“花儿”大都是表现爱情生活的,人们演唱时男方称女方为“好花儿”。
“三尺的白布染毛兰,离不开五倍子皂矾;
说起光阴我难寒,宽心时离不开少年”。
“黄鹰落架又如鸡,孔雀儿脱毛者哩;
阿哥的光阴不如你,少年俩活人者哩”。
“秦始皇建长城磨万民,马步芳要了个路工;
鞭打棍逐的活不成,牛马俩一样的待成”。
“满山满洼的抓蚂蚱,只喂了尕鸡娃了;
一斗八升的往外拿,苦坏了尕冤家了。”
“石头搭桥者水流了,青石头、冰冻者它明亮了;
阿哥们抓兵者又走了,大声吼,你说是牵者么忘掉?”
“刀枪矛子者不要害怕,没犯个法,九龙的口儿里站下;
尕妹是宫灯者阿哥是蜡,大堂上挂,宫灯里把蜡哈照下。”
“能叫过雨打个花,打花时心里面气长;
不叫衙门人来下乡,磕钱者拷打到命上”。
在旧社会里,“花儿”不但表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还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咒骂了黑暗,鞭打了贪官污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起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娱乐人民的作用。因为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花儿”里包含着人民的智慧、经验、思想感情。所以在艺术形式上和表现风格上,深为群众所喜爱、所接受、所欢迎,“花儿”成了心头肉。
解放后,青海“花儿”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这一人民喜爱的古老文化遗产重新得到了新生,在我们伟大祖国百花园里同样盛开着绚丽多彩的花朵,与盛开的百花争艳斗芳,竞相开放。可是“四人帮”又来摧残侮蔑“花儿”,说是情哥情妹的下流货;一些有极左思潮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人,他们对“花儿”横加指责,甚至把搞这一行的人和民歌手打击迫害进行人身攻击,好似犯了罪一样,他们好像是“花儿”命运的主宰者,恨不得把“花儿”一口咬死,起根拔苗,不让她存在于世了。但是,这个多灾多难的艺术花朵历经寒霜破土而出,迎春怒放,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花儿”声仍然响遍四方,特别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之后,“花儿”越长越旺了,冲破了一切阻力,开得颜色更俊了。四次文代会召开后,她更加理直气壮地与其他姐妹艺术争艳比美了。
为使“花儿”开放得更好,就需要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去培育、去浇灌、去扶植,但是目前的“花儿”却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花儿”演唱的推广,二是繁荣“花儿”的文学创作。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花儿”、懂得“花儿”,下面我谈一下“花儿”的文学特色。
一、“花儿”的结构与形式
“花儿”在比兴、结构、单韵、语言等方面与其他民歌有共性,“花儿”也有她突出的特征(即个性)。经过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创作、流传、演唱等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她特有的结构与形式。就我们民和地区来说,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花儿”有三种形式:
一是三句式的,如流行在我县土族地区官亭、中川一带的:
大红裙子水红花,绿色的袄儿配红花,
什娜姑好比一朵花。沙子坡上撒拉拉,
我的心上花拉拉,心上的花儿唱上吧。
这三句式的“花儿”字数是三二三、三二三(或二二三、三二三)一首普通韵,有时三句一组、六句一首。还有流行在其他地区的:
这么大的庄子这么多的人,
这么大的姑娘不给人,
娘老子坏了良心。
它的结构形式是四二五、四二三、三二二。
二是四句式的“花儿”,在我县我省是大量的。
果子树栽到灌沟上,
果花儿漂到个水上;
相思病得到心肺上,
血痂儿做到个嘴上。
它的字数一般是第一句三二三(或三三四、三二三),二句是三三二,三句是三三三,四句是三三二。
三是六句式的“花儿”,群众管叫它是“折断腰”。这是在四句式“花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众说的“对四六句”就是这个意思。
雄黄一撮酒一蛊,
谢恩情,
白蛇把药酒哈饮了;
恍惚一阵醒一阵,
没精神,
许仙把白蛇哈哄了。
这种“花儿”,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听起来舒服,富有强烈的节奏感,长于抒情。它的句式结构是一句二二三,二句是三(或四、五),三句是三三二,四句是二二三,五句是三,六句是三三二。从以上的例子中看出,“花儿”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人们在创作、演唱过程中,使“花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固定了下来。这就是在音乐上分上下两句,同一曲调,反复轮唱;在文学形式上,上句的落句必须是三个字(即三字尾的单字),下句(即二、四句)的落脚必须是两个字(即双字句),这是与其他民歌四句都是二二三形式又不相同的独特个性。在结构上这一点要求非常严格,就好比是各种词牌的填词一样,不可随心所欲地破坏它的格律。
黄芽菜朵朵儿大,
绿韭菜,
嫩闪闪儿的长了;
千留万留的留不下,
临走开,
泪涟涟儿的想了。
生铁俩铸下的二号锅,
钉疤儿多,
铲头俩刮不尽了;
旧社会里的人难活,
难心儿多,
针眼里透了命了。
这种折断腰的“花儿”的二、五两个短句必须是对称押韵的,也不能有二句没五句,或是有五句没二句。这样的“花儿”是残缺不全的,有失于它的完整性的。例如发表在《青海湖》1979年九月号上的几首“花儿”就是这样的:
荷包绣下的双鸳鸯,鸳鸯戏水情意长,
阿哥情深把花儿唱,甘露儿,
甜甜蜜蜜洒在妹心上。龙王山上的不老松,
六月六这天最威风;四化的宏图绘心中,
阿妹呵,要攀个科学高峰。
这些“花儿”无论从句式结构、语言风格上都不像是“花儿”的,所以有的同志编出“花儿”来批评它:“阿哥尕妹多喜爱,有风味、对唱时顺口么畅快,‘俺、‘阿妹塞到花儿里来,见‘阿妹,唱把式摇头者走开。”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虽然热爱“花儿”,但不写“花儿”,怕惹麻烦引起祸端。我曾向一位热爱“花儿”的打问:“花儿到底讲不讲究格律,受不受字数的限制?”回答是:“不按旧的“花儿”形式写,写多长都可以。”这也许是煽了风,说的堵气话。我心里想,这算什么“花儿”?诚然,硬是那样唱也能唱上,语录还不是编成歌曲在唱吗?问题是要不要“花儿”的特色,有没有“花儿”的味道?“四人帮”横行时,报刊上出现了不少不伦不类的所谓花儿,有的甚至印在初中课本上,贴上“花儿”的标签,成为“规范化”的“花儿”教给学生,让“花儿”家乡的人民群众和业余作者们来“欣赏”,岂不成了笑话?最近报刊上仍然有这类的所谓“花儿”,真使“花儿”羞着不开了。群众见到这样的“花儿”都说“四不像”,摇头说“听起来别扭,唱起来戳口”。我们在七八年编写“花儿”的过程中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有一首“花儿”:“花树花海花满满山,大寨是花中的牡丹;毛主席把花来浇灌,大寨花开红了高原。”“花儿”是有它的格律的,结果有人一改呢,把三、四句改成“毛主席亲自把花栽,大寨花开红艳艳”。要说诗,何尝不可呢,要说“花儿”太别扭了:一是把“花儿”的正句(即二、四句)改成了二二三,把“浇灌”改成“把花栽”,把“高原”改成“红艳艳”。这里的“红艳艳”显然不合乎双句两字句结尾的要求,既失去了格律,又失去了“花儿”押韵的美,读起来别扭得没法儿了。
二、“花儿”的韵脚
“花儿”属于口头文学,她的创造者是广大劳动人民,各族人民是她真正的主人。“花儿”虽不像格律诗那样的讲平仄,但在创作、演唱时十分注意她韵脚的完美。“花儿”的节奏、韵律方面总是有她特殊的要求,语言上也十分注意音乐性,遵循她形象化、地方化、音乐化、口语化的规则。
一对儿白鸟山顶上过,
我当了半山的雾了;
这一个尕妹塄坎上坐,
我当了白牡丹树了。
这首“花儿”一三句的“过”和“坐”是一韵,二四句又是一韵,猛看起来二、四句的韵脚押在“了”上,其实不然,它的重点韵脚却押在“雾”和“树”上。“雾”和“树”的末句又加了“了”,又是两个相同的音韵,听起来是很美的。
尕妹是风匣阿哥是火,
火没有风匣时不着;
尕妹是肝花心就是我,
心离了肝花时不活。
这首“花儿”一句末的“火”,二句末的“着”,三句末的“我”,四句末的“活”都是同一声韵。
洪水漫了个河滩了,
清水俩洗了个脸了;
一碗茶喝成半碗了,
清眼泪添给者满了。
这首“花儿”四句末字均是“了”字,看来似乎都押在了“了”上,其实都押在“了”字前的“滩”、“脸”、“碗”、“满”上。
贵德出哈的长把梨,
好不过碾伯的果子;
东瞅西瞭的望啥哩;
好不过跟前的妹子。
这首“花儿”一句的“长把梨”,三句的“望啥哩”都是同声押韵,听起来十分美气;二、四句末均押“子”上。
铜伙里好不过高丽的铜,
青铜俩铸哈的簪儿;
人伙里好不过心上的人,
想开时不停个点儿。
这首“花儿”第一句“高丽的铜”、第三句“心上的人”是对句,虽然四字不是相对押韵的,但念起来唱起来顺口;二、四句是“儿化”韵的“簪儿”和“点儿”别有风味。
麘子吃草着青山上转,
枪手们看,
大麘子把麘娃儿领了;
长走的大路哈我俩人盼,
仇人们看,
脚踏的江山儿稳了。
这首折断腰的“花儿”,一二四五句同韵,三六句的韵脚却押在“领”和“稳”上。
麻杆俩搭下的闪闪桥,
我过时牢,
你过时牢里么不牢;
你把我闪下的这一遭,
我你哈饶,
老天爷饶里么不饶?
这首“花儿”六句通韵。在一般情况下,六句式折断腰的“花儿”二五两个短句的韵脚跟着一、四末句的韵脚押韵;也有时,这两个对称的短句可以脱开一、四句末的韵脚而独立押韵,但韵脚必须是一致的。
路边的渠水抬头看,
十里外,
刺玫花笑破了脸蛋;
东方红一路上洒花瓣,
车头上,
麦穗儿扎哈的牡丹。
这首“花儿”的形象当然十分优美了,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两个短句的韵脚各奔前程,互不相关。发表在《青海群众演唱》第四集的《长征路上争贡献》六首十一节折断腰“花儿”中,每节短句不同一韵脚者有七节。我个人认为,这是美中不足。“花儿”离开韵脚的美,也就显得逊色了。
三、“花儿”的比兴赋
“花儿”运用民歌的一般表现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她善于运用比、兴、赋的手法,严格地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在青海“花儿”中,同样“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青铜的锣锅白帐房,
荒草的滩儿里下上;
出门的阿哥们太孽障,
离开了个家的地方。
这首“花儿”既是比,又是赋。过去不论修路值夫,抓去执行,总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拿“青铜的锣锅”是要吃饭的;在荒无人烟的荒草滩里下上“白帐房”是要避雨露风寒、酷热暴晒的。可见,出门的人孽障的。“在家千日好,出门当时难”嘛,你还要起鸡叫睡半夜,洗锅抹灶,热身子爬冷地,头痛脑热没人照顾不说,每天还要挨打受骂,受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欺侮,轻则受罪,重则送命,这当然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太孽障”。
琵琶弹来三弦子响,
三弦子没有个码子,
晚夕里哭来着白天想,
睡梦里哭成个哑子。
上两句的比兴,可以说成是类比。第一句是在动的状态中,这种弹琵琶又拉二胡的热闹劲儿却勾起了人们的心事:人家们成双成对,热热闹闹,而“我”却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因而牵动了思念情人的心事,又是哭,又是想,这同样是在动的状态中。第二句呢“三弦子没有个码子”这是写静。没码子就弹不成,弹不响。紧接着就是“睡梦里哭成个哑子”这写三弦子没有码子而没声音,她有声音却哭哑了。这是有它内在的联系的。因而互相映衬,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丫豁里修下的四郎庙,
扁柏叶,
摘上着煨了个桑儿;
想者你哭到个鸡儿叫,
眼泪儿,
泡塌了打泥炕了。
在民间,把煨柏扁叶和柏树枝叶的叫“净香”,煨着叫“煨桑”,表示敬神。这与“青石砖头铺了个廊檐了,调细泥,和上了面衣子;不见的阿哥哈又见了,头见你,隍庙里抽签去了”是一个意思。为求俩人团圆,焚香煨桑,求神拜佛,祈祷神佛保佑。这是既写景,又写情,写出了内心的活动。可是敬了神之后想得越凶了,这就不是哭下的眼泪把打泥炕泡塌了嘛。为什么把打泥炕泡塌了呢?这是因为一是眼泪多,二是我们青海人的打泥坑又不像石板炕,用泥打的炕除了上面铺几根大头棒棒和毛儿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来支撑,正如泥坯,一见水就烂散的道理是一样的。
“青稞出穗头勾下,青燕麦出穗着吊下;
黑头发陪你成白头发,手柱上拐棍了罢哈”。
青稞和大麦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而青稞出穗成熟时,穗头儿老是勾着的,大麦的穗头是往上长的。这里面有个生活问题,你若对生活不熟悉,不观察、不研究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特征,比也好,赋也好,总是比不到像上,就会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而写在“花儿”中是会闹笑话的。
比喻就是通过丰富的想象,把两种事物或现象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善的艺术形象。这就要求比喻要准确。
灶火里烧的是老麦草,
手拿者火棍儿搅了;
睡梦里梦见时你来了,
起来者满炕儿找了。
麦草见火就失去了它的本性而化为灰烬了。但是用麦草当燃料做饭,没有火棍搅是不行的。因为搅的过程,是不断供给氧气的过程,使火着得更旺。这一个“搅”却使烧火的人想起了亲人,勾起了心事,睡梦里也就“搅”得不安然了,她梦见她所想的心爱的人来了,一轱辘翻起来满炕找,结果呢?像麦草成为灰烬一样地不见影像。
进去个园子者拔白菜,
双手儿拔了个刺盖;
双胛儿找者个空皮袋,
重里么重者个厉害。
为什么进去园子拔白菜的人,却双手儿拔上了满身长刺的刺盖呢?这当然是她心没在菜上,连手扎了都不知道。这既是写实,又是夸张,通过两种形象来反衬拔白菜的人的心理状态。他思谋什么呢?这是描写失恋后的情景和神态。大家知道“皮袋夹上棍捞上,出门者要饭去哩”。皮袋是夹着走的,皮袋里装上东西是背着走的;而他一个空皮袋却为什么用双胛儿扛呢?东西不重,人们习惯于用单胛背,空皮袋却用“双胛儿扛”,说明“重里么重的厉害”这是隐喻。这个“重”字是重叠词,前面的“重”字,渲染了后面的“重”字,而且重得非常厉害,非得用双胛儿扛不行。这和“连走了三年西口外,没走过同仁的保安;连背了三年的空皮袋,没装给一撮儿炒面”是一个意思,而在选择用字的准确性上,却是异曲同工,绝不雷同,这种绘声绘色简单朴素的“花儿”语言,体现了创作者的本事。
除了比兴之外,“花儿”的另一个特色是夸张。
大雨下了整三天,竹子雨下给了两天;
淌下的眼泪哈担桶俩担,尕驴儿驮给了两天。
洪水漫了个河滩了,尕树树跟水者淌了;
没吃没喝的腿软了,眼泪把鼻子哈淌掉。
你说眼泪多不多,难心多不多?淌下的眼泪,又是担,又是驮,甚至把鼻子都淌掉了,这种夸张确也是来源于生活的,说明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们,不但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连自己的爱情婚姻也受到排斥打击,干扰破坏,不难心,不淌眼泪是没办法的。这种夸张也是被人们所接受、所喜欢的。
风趣、幽默、讽刺、调皮也是“花儿”当中常见的:
星星出来挤眼睛,明月亮照了个路了;
大佛爷伸手摸观音,娘娘她吃了个醋了。
塄坎上长出的毛儿刺根,我当了长虫的尾巴;
脚尖尖踏者脚后跟,心硬了你把我撩下。
“花儿”的语言都是符合群众的口头语,是见景生情,脱口而出的,它朴实优美,形象生动,不是生硬苦涩的、干巴巴的、概念化的语言。这个我们在学习传统“花儿”的过程中去加深理解,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向民间学习、向歌手们学习,学习“花儿”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生动活泼的地方特色。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花儿”,如“花归了大海者马脱了缰,金凤凰展开了翅膀;华主席还我银铃儿嗓,端唱个百花儿齐放。”这里我用一个“端”字,一来表达关于双百方针的赞扬之情,二来表现我们搞文艺工作者的“牛劲”。但是有的报刊发表时却把“端”字改成“要”字了。这就改掉了地方的土味,使“花儿”松了劲道。落实党的各种政策,深得亿万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称,我写了“三星高照七星明,南斗里牛郎星出名;党的政策是一杆称,公平者亿万人赞称。”这里我借用了北斗七星、南斗六郎、三星三个不同方位、不同形状的星星来比兴,不明白的人看起来与下面的句子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在过去,我们使用的十六两的老称就是根据这十六个星星定的,上句的比喻,实际上就是说称。“天凭日月,人凭良心”,“人心不公使戥称”。党的政策最公平,因而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这也是我学习传统“花儿”和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我的意思是希望写“花儿”的同志们很好地推敲、选择每一个用字,让它十分熨贴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赋予每一个对象以新颖美妙的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给“花儿”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生命,用她来歌唱我们美好的时代,歌唱党的英明伟大:“画上月亮画太阳,长青的松柏哈画上;要唱毛主席要唱党,贴心的话儿哈唱上。”赵存录同志写的《尕马儿拉回来,台湾》是一首好的抒情“花儿”。“北京的烤鸭味道鲜,南京的枣糕么真甜,茅台酒来葡萄干,正等着奶尕儿回还。”奶尕,是做父母最后生养的一个孩子。“天下的老儿,痛的是小儿。”不论从台湾的土地、人口说,他是最小的。祖国人民为台湾人民准备好了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一切礼物,正殷切地盼望着远离膝下的小儿回来,形象地表达了人们欢迎台湾人民回归大陆的思想感情,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较好地结合,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全省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中得到了创作奖。
总之,比兴也好,夸张也好,总是离不开生活真实和自然真实的土壤的。
四、关于“花儿”的衬词问题
“花儿”的衬字、衬词、衬句问题,关乎到文化创作和演唱方面的效果问题。在文学创作中,要特别注意“花儿”语句中的介词、助词,如“者”、“哈”、“嘛”、“价”等(这种字、词在“花儿”中常以衬字、衬词出现的),我粗略想了一下,它的作用是:
(一)是“花儿”这种口头文学形式与结构上的需要,使“花儿”更加突出其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如“大河沿上牛吃水,牛见了鱼儿的尾巴;端起个饭碗者想起了你,吃上的麦叶哈吐哈(下)”。
(二)加强了语气的感情色彩。如“想吃个鱼儿了拿钓杆,钓杆上拴一条线哩;想起了个花儿者连夜赶,两站哈沓一嘛站哩。”
(三)起承上起下的作用,烘托气氛,使“花儿”意境优美动人,情调发人深思,从设问句和自问自答中得到否定或肯定的回答,给人以联想遐想的余地,幽默风趣,动人心弦。如:
“清水河里洪水扰,河里的鱼娃儿闹吵;
尕妹的睡梦里你搅扰,你说是牵者嘛忘掉?”
“正是杏花三月天,马儿上备的是银鞍;
尕手里抓住者问几遍,心儿里酸里嘛不酸?”
我们不要因运用衬词不当而乱加楔子,使语法混乱,逻辑不清,致使词意含糊。更重要的是在演唱上的问题。“花儿”的曲令来自衬词,如用《尕马儿令》演唱时,就会出现“尕马儿拉回了来,哎哟,回拉了缓来呀肉儿”的衬句,用《山丹花》曲令演唱时,衬词(衬句)中出现“尕妹山丹红花儿开”;用《水红花》曲令演唱时,就会出现水红花的衬句等等。在以往演唱新“花儿”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因衬词不当而伤害“花儿”词意,使正词与衬词脱节,情调完全成了两样的情况。(在唱传统“花儿”中,这种衬词仍起着别的衬句所代替不了的作用)过去在演唱新编“花儿”的过程中,我们和歌手们一道,解决了“花儿”词与衬词不当的矛盾,弥补了配合、反衬不当的缺陷,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年六月,我们民和的歌手谢明芳、李桂兰二人在唱《水红花》时正词唱的是:
“松柏根连土者土养了根,根深嘛叶茂的翠青;
党的政策是心里的灯,点着了旺盛的干劲。”
而在用《水红花》曲令演唱时,衬句却用“我的水红花大眼睛,尕妹连手走哩嘛坐哩呀,领上了就浪走。”这与“花儿”词恰恰成了不相容的两回事,与新的词儿完全失调,在演唱效果上会起大的副作用。因此,我就动手改写成了“我的水红花儿开了呀,水红花的叶叶儿嫩了呀,就谁不嘛就爱了”的衬句,交给两个歌手试唱。起初她们还不习惯,我教给她们几遍后,她们就接受了,唱起来也很顺当。她们高兴地说:“这样一改也受听。”我想,水红花本来很美的了,以她来比所唱的事物,也好似成了一朵很美的水红花,两种形象都是美丽的,而且还不损于水红花的曲令,为人们所喜爱。这当然是我粗糙的、简单的尝试,能否改得更理想、更美好,有待于专家们去下手。我觉得改造衬词,是要花一些心思的,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和歌手们结合在一起,就会收到好的效果。又如把“阿哥的肉”的衬词改为“好花了儿”、“社员们听”之类的代衬词也是个办法。当然在歌唱领袖的“花儿”中,总不能唱“阿哥的肉”的衬词吧。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大量的,只要有一颗忠于“花儿”的心,付出心血,加以钻研,我想就能写出好的衬词来。
五、关于传统“花儿”的借鉴问题
数以万计的传统“花儿”,是文艺宝库中留下的珍贵财富,是广大劳动人民精神产品的结晶,口传心记,代代相传,为我们提供了写作“花儿”的大好条件,是有新的借鉴意义的。很多同志本着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为写作“花儿”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有的人在搜集、整理、研究探索和踏实学习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了新的创作,这是积极的,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但是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花儿”,小看传统“花儿”,独出心裁地在那里搞什么所谓的“破格”和“提高”。结果呢?写出的“花儿”就有了“念起来别扭,唱起来戳口”的现象。“提高”后的“花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不向传统“花儿”学习,又不顾及群众的演唱。
秃尾巴黑狗咬月亮,空中里没有个堵挡;
一来是咱们的方向明,二来是走路稳当。
冰冻三尺口子开,雷响三声雨来;
天安门城头红旗飘,新法律定下的真美。
新打的墙头十八板,头上再打上两板;
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好花儿给节日敬献。
作者在三首“花儿”的前两句比,都是套用了传统“花儿”的句子。在第一首“花儿”中,“秃尾巴黑狗咬月亮,空中里没有个堵挡。”这两句都是贬义的。黑狗是令人生大厌的,何况它又汪汪地咬着人们喜爱的明月亮;而且任凭它咬,空中里连一点堵挡都没有,这就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作者紧接着又写“一来是咱们的方向明,二来是走路稳当”这两句是褒义的,而“一来是咱们的方向明”这句是含糊不清的。是谁的好处“方向明”呢?“二来是走路稳当”是什么样的道路上“走路稳当”呢?再说,青海“花儿”中找不出个“咱们”来的。我认为这首“花儿”的毛病主要是褒贬混乱,逻辑不清。根本不同属性的几个形象(后者无所谓个形象)怎么能够成比赋呢?第一句末的“咬月”与第三句末的“方向明”又不是同韵脚,失去了“花儿”结构对称、对仗工整与音韵要求严格的特色。
第二首“花儿”“冰冻三尺口子开,雷响三声雨来”,这是传统“花儿”“冰冻三尺口子开,口子里牛卧下哩”和“青天上铺下了黑云彩,雷响三声者雨来”两首“花儿”的上句比兴拼凑在一起的。这两种形象怎能与下面的“天安门城头红旗飘,新法律定的真美”联系起来呢?“冰冻三尺口子开”是写“三九四九,闭门洗手”的滴水成冰的寒月时节,而“雷响三声者雨来”是写夏至以后的事,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寒暑相对的时间怎能生硬地拉在一起呢?再说“冰冻三尺口子开”又怎能与“天安门城头红旗飘”这一壮丽的图景互相联系呢?这种比,给人的又是怎样的感觉呢?“雷响三声雨来”(这三声的后边又缺了一个“者”字),大家知道,过雨(暴雨、冰雹)是从古到今对自然界特别是对庄稼带来灾害的祸根,对这种妖魔人人厌恶透了,它又怎能与“新法律定下的真美”相比而生呢?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对的。党中央制定的法律是赏善罚恶,扶持正义的,这又怎能与“雷响三声雨来”相比而言呢?
再说“新打的墙头十八板,头上再打上两板。”且不论下面的立意与这两句的联系,而这两句本身又是经过作者改编了的。原话是“新打的庄廓十八板,嫌低了再打上两板。”他却别出心裁地把庄廓改成“墙头”。墙头又怎能新打呢?更不妥当的是“头上再打上两板”是什么“头”,显然是没有限制词,使人难以捉摸。我不客气地说,像这样乱改乱编,是对“花儿”的一种糟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两首传统“花儿”:
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
天河口,
七星儿摆八卦里;
尕妹好比是冷石头,
怀揣着走,
捂热时咋丢下哩。
以上三句的比,说的都是天上的月亮星辰,贴得这样紧,像一口气呵成的,它不是东拼西凑的破烂货。又如:
一天下给了三场雨,
廊檐水淌到个院里,
案板的跟儿里想起你,
清眼泪跌到个面里。
这里把雨比作泪,把廊檐水淌到院子里和眼泪淌到面里连在一起。“花儿”是长于联想的,而这种联想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陈词,而是具体形象的描写。所以对传统“花儿”的借鉴与学习,应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