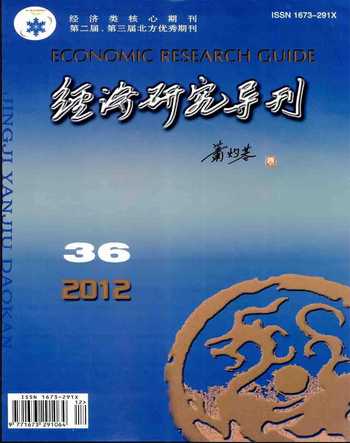要防止把社会主义搞成民粹主义
李文顺 夏寒松 李和顺
摘 要:社会主义的追求是高尚正义的,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追求好的结果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在化理想为现实的过程中,要防止社会主义跌入民粹主义的误区,避免在社会主义好的名义动机下闹出不利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主义;误区;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243-02
人们的信仰是不同的。在价值取向上,是为个人、少数人谋福利还是为大众、所有的人(社会)谋福利,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论在这方面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选择前者,例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公然宣称利己主义、非道德主义,论证剥消、压迫、不平等的合理性,诬蔑大众,认为“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人民群众不过是“超人”手中的稀泥、培育自己的肥料、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墨索里尼承认自己深受尼采的影响,说“他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1]。这种只顾自己强大自己快活不顾别人死活与众人为敌的观点是反社会的主义。有人选择后者,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表白自己“为人类而工作”、“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类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中的一种。正面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造福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不过,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指那些自认为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思想和主张而不论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不是讲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主义。
很早把马克思观点介绍给中国人的梁启超就看到了这一区别,1902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18号发表了他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还引述颉德的话说:“今日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Marx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Nietzsche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人的本性既包括自然性又包括社会性,相应地自然性表现出自利的一面,社会性表现出利他利群的一面,己与群各有其界,二者不可偏废。自利性发展到极端类似于动物、可能危害社会导致犯罪;热衷于利他利群者是人群中的高尚者,古时称圣人贤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市场行为,而假公济私则是伪君子。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似乎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有关联,马克思主义推崇人的社会性,我们认为,社会这个共同体就像大树,每个人就是它之上的枝叶,大爱无疆比冷酷自私好,因此,多数社会主义就其愿望来说是高尚的、正义信仰。但是,观点不能极端,行动不能走偏,良好的愿望并不是一定能带来良好的结果,为了保证良好的理想得到良好的结果,就要防止在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时跌入民粹主义的误区。
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有:借“群众运动”之名而“运动群众”,崇拜自发性,“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离开宪政理性设计的全民公决和投票万能论、搞“大民主”,打倒一切权威,简单化地把多数神圣化而把少数贬义化,迎合一些人不正当的“平等”心理,人为抹煞差别,一些地方形成“多数人暴政”等等。其错误在于:只要结果不要程序,只顾多数人权利忽视少数人权利,只讲群众性不讲精英性,甚至以“多数”的名义围攻围剿精英,把自己当成群众的“救星”,其结果是:在良好愿望遮蔽下使人丧失理智,盲动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和破坏。
有人认为投票就是民主,其实投票可能是民主,也可能是民粹;民粹主义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但法西斯主义包括民粹主义。有人这样描绘当年的希特勒这样搞“国家社会主义”:演讲也好,宣传也罢,都是为了掌握群众。没有群众的运动定将一事无成,这是希特勒早年就获得的政治经验之一。
希特勒发展出这样一种绝招,对某些重大问题必要时直接诉诸舆论,进行全民公决。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就是“选举!选举!直接诉诸人民!”极端的独裁绕个圈子在另一头和最“民主”的形式直接沟通了。
1933年10月,希特勒突然宣布,德国立即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它需要得到全体德国人的支持。希特勒毅然决定:解散国会,退出的决定交付全国公民投票来认可。希特勒十分相信自己动员民众的能力,他知道公决会有怎样的结果。他把公民投票和国会清一色纳粹党员的新选举定在1933年11月12月,这是德国人记忆犹新的国耻日——1918年停战纪念日的后一天,希特勒在表决前几天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鼓动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
希特勒这回又号准了德国人民的脉搏。在经过对战败后果怀了十五年的愤懑以后,德国人民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合格选民中有96%参加了投票,其中95%赞成希特勒“退出”的外交政策。至于赞成国会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的则有92%。十分可悲的是,甚至在达豪集中营中,被拘禁的2 242人中也竟有2 154人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关起来的政府!希特勒获得惊人的胜利。这当然不仅仅是其外交内政的胜利,而且是其掌握群众的胜利。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又一次使用全民公决,在95%合格选民中90%的人的支持下,他篡夺了总统的权力[2]。
张维为论选举说了这样一些话,有参考价值,兹录于下: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还不破产呢?其实冰岛已经破产,希腊也破产了,还有不少国家处在破产的边缘。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国家过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搞普选的。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 [3]。
我们并不赞成他的所有看法,这是因为:其一,由一个公司不能靠选举产生CEO、一支军队不能靠选举产生统帅这点,不能由此就推导出一个国家也不能选举出总统的结论。公司、军队是一回事,国家是另一回事,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就国家层面来讲,选举总比世袭、指定要好。问题是该选则选,不该选就不选;大范围(国、省或州)选,小范围(一校、一厂)不选。假如人们弄反了,不该选乱选(比如让系主任推举校长),而且把大小混淆了,那效果是不会好的。其二,张维为所讲的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妇女30岁才能参加选举、素质高的人有双倍投票权等,这不是人家不好,相反唯有如此才避免了民主的短处(如抑制精英)和民粹化倾向,倒值得我们思考。你想,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落后国家,一个政治学博士和一个文盲家庭妇女都投一票就合适?一个政治学博士和一个生物研究方面的博士对国家大事的理解上深度相同吗?其三,条件具备后,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为社会的主义,那社会就是人群,人群和谐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人,人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普选制使大众手中有了选票,从而能够影响国事,改善了自己的境遇,成了候选人讨好的对象,这是民众地位的提高,是民众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实现。能一人一票搞选举,是好事不是坏事,不该尽从负面去嘲笑。
我们也赞同张维为所表达的某些意思,我们也借此作一下发挥:其一,选举并不万能,也不应迷信,不能动不动就投票,视投票为手段、民主为游戏,甚至只是为了转移矛盾。有治国之才但不善沟通不会忽悠不招人待见的人不见得能在选举中有胜算,平庸之才掌握了技巧有人帮衬倒可能胜出。选举并不能保证一定选举出才俊,滑头政客长袖善舞、庸者得意的事是难免的。其二,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是有条件的。没有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没有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中产阶级,没有工业化城镇化科教文化发展培育出高素质的公民,泰国那种红衫军和黄衫军对立的情形就会在他国上演,这于国于民决非幸事。其三,民主并不等于民粹,不分场合一律搞多数票胜出是荒唐可笑的。“文革”闹剧和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被多数票表决处死的精英悲剧昭示我们:有时多数并不必然有理正义;民主并不是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还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效果检验形式。
民粹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不会生财只热衷于“杀富济贫”或“劫富济贫”,不分青红皂白去“均贫富”;福利国家拖垮了某些国家的财政,导致懒惰病发作和生产效率下降;为讨好大众而寅吃卯粮等等。其错误在于:离开效率讲公平,离开生产讲分配和消费。其结果是:当“会下金蛋的老母鸡”老化或被杀死时,共同富裕就成了一句空话。
由此而言,都讲“多数”、“大众”或“人民”,把握不好,社会主义就会跌入民粹主义的泥坑中去,值得人们小心啊!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98.
[2] 罗云力.世纪奸雄、德国耻辱——法西斯魔怪希特勒极权极霸的疯狂[G]//谭英州,杨双.政坛首脑治国韬略.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1993:2-386.
[3] 张维为.中国震撼[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49.[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