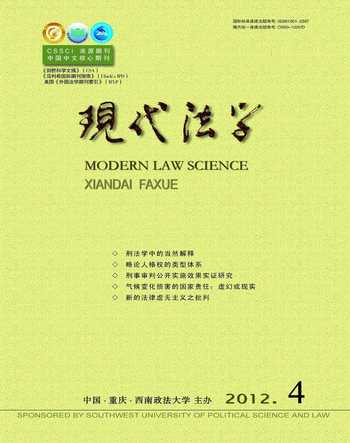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
摘 要:一般来说,当然解释是法条的适用方法,但在刑法中,当然解释应当作为一种解释理由。举重以明轻,是就出罪、处罚轻而言;举轻以明重,是就入罪、处罚重而言。当然解释的依据是事物的本质与法条的旨趣。由于刑法并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故在适用举重以明轻的原理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时,不需要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不能将刑法的处罚漏洞作为举重以明轻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故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后,还要求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范,但是,不能将对案件事实的缩小评价当作对刑法规范的类推解释。
ス丶词:当然解释;概念;性质;依据;规则
オブ型挤掷嗪牛篋F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4.01オ
文章编号:1001-2397(2012)04-0003-15
一、当然解释的概念与性质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刑法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的文字,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论理解释,就是按照立法精神,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当然解释、扩大解释与限制解释。”[1]这种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扩大解释与限制解释并不是论理解释,只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扩大或者缩小刑法用语含义的一种方法。扩大或者缩小刑法用语含义本身,既不是理论根据,也不是逻辑方法。其二,这种分类所列举的解释方法是极为有限的。例如,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当然解释等,在刑法理论的通说中都没有地位。
笔者也曾按照通说的观点,将刑法解释方法区分为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论理解释主要包括扩大(扩张)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并认为,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参见: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7.)但是,这种区分并不严谨,至为明显的是将形式的分类与实质的分类相混淆。
日本学者笹仓秀夫将解释方法分为解释的参照事项与条文的适用方法,条文自身的含义、条文之间的体系关联、立法者的意思、立法的历史背景、法律意思(即正义、事物的逻辑、解释的结果),属于解释的参照事项;平义解释(按文字字面含义适用)、宣言解释、扩张解释、缩小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类推、比附、反制定法的解释(变更解释或者补正解释),则属于条文的适用方法。相当清楚的是,在解释法律规范时,可以同时参考法律条文自身的含义、条文之间的体系关联、立法者的意思、立法的历史背景等;但是,不可能同时采取平义解释、宣言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等等。换言之,在对一个法条(或法条用语)进行解释时,解释的参照事项是可以并用的,而条文的适用方法则不可能并用,只能采用其中一种方法。( 参见:笹仓秀夫.法解释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4,25.
不难看出,上述解释的参照事项实际上是指解释理由。因此,对刑法的某个条文或者用语得出某种解释结论,可以基于多种理由。上述条文的适用方法,可谓解释技巧,对一个法条或者用语只能采用一种技巧。例如,对《刑法》第275条的“毁坏”概念,不可能既作平义解释,又作扩大解释;也不可能既作平义解释,又作缩小解释;更不可能既作扩大解释,又作缩小解释。解释者采取其中哪一种解释技巧是需要解释理由支撑的。不管人们是采取物理的毁坏说(物质的毁坏说),还是采取效用侵害说,抑或采取有形侵害说,都需要解释理由。但是,解释理由不可能只有一种,也不可能仅限于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四种,除了目的解释外,也不可能要求在任何一方面都具有理由。
在解释技巧中,类推、比附显然是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但是,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故类推解释、比附是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技巧(当然,有利于被告人的除外)。于是,称某种解释为类推解释或比附,就成为人们反对该解释的理由,或者说成为该解释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当然解释(当然推理),也是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亦即,在所面临的案件缺乏可以适用的法条时,通过参照各种事项,从既有的法条获得指针,对案件适用既有法条的一种解释。当然解释有两种样态:就某种行为是否被允许而言,采取的是举重以明轻的判断;就某种行为是否被禁止而言,采取的是举轻以明重的判断。例如,倘若法律允许在林中骑马,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理,人们当然可以在林中徒步旅行。再如,如若法律规定禁止将狗带入公园,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当然禁止将狮子带入公园。( 参见:笹仓秀夫.法解释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96.)显然,举重以明轻,是从重的、大的方面向轻的、小的方面推论(可谓缩小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是从轻的、小的方面向重的、大的方面推论(可谓扩张当然解释)。(参见:增田丰.语用论的意义理论与法解释方法论[M].东京:劲草书房,2008:220.)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当然解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与类推解释、扩大解释等不同的是,当然解释本身就能提供一种解释理由。(例如,认为“结婚”包含通奸的类推解释,以及认为“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扩大解释,都只是一种技巧,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之所以能成为解释理由,主要是因为当然解释是基于类比得出结论的。“类比在道德和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用途。……在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相同的案件同等对待时,其基础就是在不同的案件之间作比较。例如有两个类似的案件:两个人在类似的条件下做出类似的行为,褒奖其中一个而贬损另外一个在道德上就是值得怀疑的。法律上遵循先例的原则也是在案件之间作类比,在当下的案件和曾经已经判决的案件之间作类比。”[2]郑永流教授指出:“在寻找相似性的意义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也属类比,而不是所谓‘当然解释。它们的共同含义为,某一条文的内在依据(如事物的本性),较条文明确涵盖的事实,更可适用于条文未明确涵盖的事实,不过,二者的发生相向而行。”[3]这一观点强调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是一种解释理由。但在本文看来,将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称为类比和称为当然解释并不矛盾。因为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中的轻重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当然推理,亦即,当刑法不处罚某种重行为时,得出对较之更轻的行为也不得处罚的结论,或者当刑法处罚某种轻行为时,得出对较之更重的行为更应当处罚的结论,是合乎事理、情理或者理所当然的。(由于刑法存在漏洞,所以,理所当然并不意味着“法”所当然。)将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作为解释刑法时应当遵循的一项原理,具有重要意义:法官在解释刑法时,必须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使案件之间的处理结论协调一致。因此,法官不应孤立地解释任何一个刑法条文,而必须将一个条文作为刑法整体下的一个部分进行解释。在此意义上说,当然解释也是体系解释的表现或者要求,因而是一种解释理由。
另一方面,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一样,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当然推理形成解释结论的一种技巧。由于民商法等法律并没有像刑法那样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法理学者与民法学者便将当然解释视为解释技巧或者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例如,前述日本学者笹仓秀夫就是以一般的法解释为根据,将当然解释归入解释技巧(法条的适用方法)的;他就当然解释所举之例,都是民商法、行政法等领域的解释例,而没有刑法领域的解释例。(参见:笹仓秀夫.法解释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96.)再如,王利明教授指出:“当然解释仍然属于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因为当然解释的结论仍然处于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之内。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并不限于其字面含义,而是指其射程范围。在当然解释的情况下,虽然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不能包括待决案件,但是,通过对其进行‘扩张,就可以适用,而且此种‘扩张还处于法条文义的可预测范围之内。当然解释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立法者为了节约立法资源而有意遗漏的条文。”[4]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在民法上或许是成立的,但却难以运用于刑法。首先,扩张解释时,解释结论仍然处于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之内,但当然解释时,解释结论并不必然处于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之内。如上所述,法律禁止将狗带入公园时,认为也禁止将狮子带入公园属于当然解释,这显然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因为“狗”的文义无论如何不可能包含狮子。所以,当然解释的结论会超出法条文义的可能范围。其次,在刑法上,当然解释本身是一种理由,但扩张解释本身不可能成为解释理由,故二者处于不同层面。即使运用当然解释时,需要对法条文义进行扩张解释,也不能将二者混同。例如,拐骗儿童的行为成立犯罪,人们习惯于将拐骗解释为“欺骗”。发生行为人使用暴力夺取儿童的案件时,当然解释所提供的理由是:既然使用非暴力手段拐走儿童成立犯罪,使用暴力手段夺走儿童的行为更应当成立犯罪;扩张解释所采用的方法是:将《刑法》第262条中的“拐骗”扩张解释为包括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当然,这一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则是另一回事。)在此,让解释者得出扩张解释结论的理由,是当然解释。
在适用刑法上,举重以明轻意味着,如果刑法没有将更严重的A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比A行为更轻微的B行为,就应无罪;如果更严重的A行为不应当受到重处罚(在广义上而言),那么,比A行为更轻微的B行为,也不得受到重处罚。举轻以明重意味着,如果刑法将较轻的甲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比甲行为更严重的乙行为,应当构成犯罪;如果刑法对较轻的甲行为规定了重处罚,那么,比甲行为更严重的乙行为,也应当受到重处罚。显然,举重以明轻,是就出罪、处罚轻而言的,或者说,是就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而言;举轻以明重,是就入罪、处罚重而言的,或者说,是就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而言。(如后所述,将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仅限定为出罪、入罪并不合适。)
成文刑法总会存在漏洞,完全可能出现已将轻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象。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故不得直接采取当然解释认定某种重行为构成犯罪。换言之,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进行当然解释时,也要求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范,而不能简单地以案件事实严重为由定罪处刑。亦即,当然解释的结论能为刑法用语所包含时,才能最终采纳这一当然解释结论。但如后所述,当然解释的结论是否为刑法用语所包含,不是当然解释本身的问题。所以,在刑法解释中,尤其是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时,当然解释只能成为一种解释理由。亦即,在某种轻行为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时,对性质相同的重行为以犯罪论处,成为一种解释理由;同样,在某种轻行为依法应当受较重处罚时,对于性质相同的重行为应当处以更重的刑罚,也是一种解释理由。但是,有理由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例如,采取类推解释技巧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具有充分理由,但是,类推解释本身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 参见: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M].东京:有斐阁,1972:77.)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因此,在适用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时,则不需要当然解释的结论为刑法用语所包含。(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理得出的解释结论不能被刑法用语所包含时,其中的举重以明轻,则既是解释理由,也是解释技巧。)
由此可见,当然解释虽然可以作为刑法的解释原理,但是,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的适用条件或者要求是不相同的。
二、当然解释的依据与规则
作为解释理由的当然解释或者当然推理的依据,并不是形式逻辑。换言之,由形式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并不需要借助于当然解释的理由。例如,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薛瑞麟教授指出:“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当然解释。刑法虽然没有规定对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但它是死刑中缓期执行的一种制度,并依存于死刑。既然对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不能判处死缓也是《刑法》第44条(指旧《刑法》——引者注)的应有之义。”[5]其实,死缓与死刑是种属关系,死刑当然包括死缓,故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缓,如同汽车包含公共汽车一样。“但这种解释显然不是轻重相举,而是文义解释,文义解释可解决种属关系。”[3]198换言之,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缓,并不是根据事物本性的理所当然的道理得出的结论,因而不是当然解释。倘若刑法仅规定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缓,那么,得出“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结论,才是当然解释。
陈兴良教授指出:“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事理上的当然是基于合理性的推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解释之概念与被解释之事项间存在种属关系或者递进关系。仅有事理上的当然,而无逻辑上的当然,在刑法中不得作当然解释。”[6]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就入罪与处罚重的情形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时,只有具备逻辑上的当然,亦即,只有当待决案件与某刑法规范相符合时,才能适用某刑法规范。就此而言,本文完全赞成陈兴良教授的观点。然而,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是两个不同的要求。在一般的法律解释中,倘若禁止牛马通行,那么,据此得出禁止骆驼通行的结论,就属于当然解释,而且是最终完全可能被接受的解释。在刑法学上不可能被接受,并不是因为这一解释不是当然解释,而是因为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亦即,刑法学对逻辑上的当然的要求,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不是当然解释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存在逻辑上的当然,“解释之概念与被解释之事项间存在种属关系或者递进关系”,就不一定再需要事理上的当然。例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的对象是他人,由于他人包含男人,故侮辱男人的行为符合侮辱罪的构成要件。就此而言,不需要借助事理上的当然。又如,根据《刑法》第110条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构成间谍罪。如果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并且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就更加成立间谍罪。就此而言,也不一定需要借助事理上的当然。概言之,在刑法学中,得出某种结论所借助的是何种解释方法,与该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又如,只要是限制刑法用语的文义、缩小刑法用语外延的解释,就是缩小解释;至于这种解释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则不是缩小解释本身的内容。诚然,笔者的观点与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不同的只是:陈兴良教授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纳入到当然解释之内;笔者仅将当然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理由,至于这种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则是需要判断的另一问题。之所以存在这种分歧,是因为陈兴良教授将当然解释视为与缩小解释、扩张解释并列的解释方法(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笔者将当然解释视为一种并非与缩小解释、扩张解释并列的解释理由。
郑永流教授主张以规范宗旨为基础,用“事物的本性”这一表达作为轻重相举的内在依据。“事物的本性是指基于事情本身的内在要素,这一内在要求是在解决某个问题时令人非同意不可的、不可辩驳的力量。”[3]198本文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事物的本性(本质)与规范的宗旨并非完全等同。大体而言,之所以“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是基于事物的本性;之所以“应当”得出当然解释的结论,则是基于规范的宗旨。
在对刑法进行当然解释时,既需要将事实与规范进行类比,也需要将待决事实与基本命题中的基准事实(参见后述内容)进行类比。之所以可以进行类比,并得出合理结论,是由于存在一个第三者——事物的本质(natura rerum、本性、事理)。“从法律意义上说,‘事物的本质这一概念并不指派别之间争论的问题,而是指限制立法者任意颁布法律、解释法律的界限。诉诸事物的本质,就是转向一种与人的愿望无关的秩序,而且,意味着保证活生生的正义精神对法律字句的胜利。因此,‘事物的本质同样断言了自身的权利,是我们不得不予以尊重的东西。”[7]事物的本质,可能源于某种固定的和必然的人的自然状况,可能源于某种物理性质所具有的必然的给定特性,可能植根于人类政治、社会生活制度的基本属性之中,也可能立基于人们对构成某个特定社会形态之基础的基本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的认识。(参见: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55.)存在与当为、现实与价值的互相联系,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的相互对应,都离不开事物的本质。“从事实推论至规范,或者从规范推论至事实,一直是一种有关‘事物本质的推论。”[8]
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9.)所以,违法本质相同前提下的违法程度的轻重和责任的轻重,成为当然解释的依据。一方面,当行为侵害的法益相同,轻微侵害该法益的行为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时,严重侵害该法益的行为,就更应当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严重侵害某法益的行为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那么,轻微侵害该法益的行为,就更不可能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在违法本质相同的前提下,如果责任较轻的过失行为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那么,比其更重的故意行为,就更应当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故意行为不受处罚,性质相同的过失行为就更不可能受刑罚处罚。
在刑法中,违法与责任是由具体的要素体现出来的,亦即,构成要件要素都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各种责任要素都是表明有责性的要素。所以,解释者必然会通过具体要素的轻重相举进行当然解释。例如,既然使用非暴力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可能成立盗窃罪,那么,使用暴力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更可能成立盗窃罪(至于该行为是否触犯抢劫罪,则是另一回事)。又如,既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18条第3款),那么,完全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犯罪的,更应当负刑事责任。再如,既然刑法对于故意伤害罪的成立没有规定特定动机,即使出于可以理解的动机伤害他人的(为了让儿子戒除赌博习癖而砍掉其一个手指),也成立故意伤害罪,那么,出于流氓动机伤害他人的,更能成立故意伤害罪。(因此,认为出于流氓动机伤害他人的案件仅成立寻衅滋事罪的观点,并不成立。(参见: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64.))
但是,根据事物的本质能够得出当然解释结论,并不意味着应当得出当然解释的结论。人们之所以进行当然解释,就是为了实现规范的宗旨。“任何法律均有其目的,解释法律不仅不能偏离其立法旨趣,且应以贯彻实现其立法旨趣为主要目标。立法旨趣,乃系个别规定或多数规定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判断。个别规定立法旨趣,较为具体,而多数规定所整合的‘全体立法旨趣,则较为抽象。个别的立法旨趣为实现全体立法旨趣之手段,而形成一完整之规范目的。苟法律仅就个别立法旨趣而为规定,某一事实虽乏规范明文,惟衡诸该条立法旨趣,尤甚于法律已为规定事项,自更有适用余地。此时即应为当然解释。”[9]所以,当然解释首先是一种目的性推论,而不是演绎性推论。在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进一步对刑法规范进行扩张解释或者缩小解释时,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轻重比较,而是为了实现刑法规范的目的。例如,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的,即使没有造成伤亡结果,只是剥夺不法侵害人人身自由的,当然也是正当防卫。因为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刑法》第20条的目的。但是,法官不能因为刑法某个条文对某种犯罪规定了死刑(杀害),就采用当然解释的原理(既然允许杀害就当然允许伤害),对被告人判处“轻于”死刑的身体刑(伤害)。(参见:增田丰.语用论的意义理论与法解释方法论[M].东京:劲草书房,2008:241.)因为这种做法明显不符合刑法的目的。
运用当然解释原理时,实际上先将事实A与法条进行符合性的判断,得出某种结论后,再将事实A1与事实A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对事实A1应否适用该法条的结论。在这种场合,事实A可谓基准事实,对事实A是否适用某法条的结论不仅是确定的,而且是正确的(基本命题)。事实A1可谓待决事实,将待决事实与基准事实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是否适用基本命题的结论。以举轻以明重为例,按照法条的明文规定,某行为构成犯罪,事实F1明显符合法条的规定,因而应当以犯罪论处。但是,事实F2与事实F1具有相同性质,而且其程度明显重于事实F1。所以,对事实F2也适用该法条的解释结论,成为一项重要理由。例如: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放火行为,构成《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这是一个基本命题,前一句所描述的事实是基准事实(F1);待决事实是,行为人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放火行为,但该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不能查明(F2);待决事实至少不轻于基准事实,甚至可能重于基准事实;因此,对待决事实(F2)应当适用《刑法》第114条。
不难看出,运用当然解释的原理,应当遵守以下规则:(1)必须以基本命题为基础或者前提。(参见:周兴志.“当然逻辑”试探[J].江汉论坛,1983,(8):17.)亦即,对基准事实如何适用法律是确定的、正确的,其结论是非同意不可、无可辩驳的。(2)基本命题中存在可能提升或者降低违法、责任程度的要素,因而能够推导出另一个规则。(参见:Ingeborg Puppe.法学思维小学堂[M].蔡圣伟,译.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138.)(3)待决事实与基本命题中的基准事实的性质相同,在事物本质上没有差异。在刑法上特别要求两个事实侵害的法益相同,均存在责任。(4)待决事实与基本命题中的基准事实存在轻重之别,因而能够进行比较。亦即,在法益侵害与责任方面,能够确定孰轻孰重。(5)当然解释结论必须与轻重相举相吻合。在入罪、处罚重方面,只能是举轻以明重; 在出罪、处罚轻方面,只能是举重以明轻。(6)就一个方面的情形(如违法事实)得出的当然解释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于另一方面的情形(如责任)。
三、举重以明轻
联系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从定罪的角度来说,举重以明轻原理的适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法官必须确定哪些与案件相关的行为在刑法上没有被规定为犯罪;然后,将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与自己所面临的案件事实(待决事实)进行比较,判断孰轻孰重;再不断对构成要件进行(限制)解释,将待决事实排除在犯罪之外。
例如,《刑法》第124条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纯从文字表述与形式逻辑关系上理解上述两款的规定,就会得出如下结论: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成立犯罪。但这样的解释结论,明显违反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至为明显的是,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电力设备、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等罪的违法性,重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法定刑就能说明这一点。相应地,过失损坏交通工具、过失损坏交通设施、过失损坏电力设备、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等罪的违法性,也重于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但是,过失损坏交通工具、过失损坏交通设施、过失损坏电力设备、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等罪的成立,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参见《刑法》第119条);如果认为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成立,不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就导致其与上述几种过失犯罪不协调。换言之,既然过失损坏交通工具、过失损坏交通设施、过失损坏电力设备、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等罪的成立,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成立,更应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或者说,既然过失损坏交通工具、过失损坏交通设施、过失损坏电力设备、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成立犯罪,那么,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更不可能成立犯罪。由于《刑法》第124条第1款后段所规定的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前段是指不需要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所以,应当认为,《刑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前款罪”仅指过失犯前款后段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当然解释的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导致解释者只能对《刑法》第124条第1款中的“过失犯前款罪”采取缩小解释的技巧。这种缩小解释不仅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实现了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6.)
再如,《刑法》第280条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第3款规定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居民身份证原本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一般不会发生出卖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或者购买他人真实身份证的现象,单纯盗窃、抢夺、毁灭身份证的行为也不值得科处刑罚(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入户盗窃身份证、携带凶器盗窃身份证、扒窃身份证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盗窃罪。),所以,《刑法》第280条第3款将居民身份证从第1款的国家机关证件中独立出来,从而缩小了处罚范围。
但是,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将行为人购买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共犯。这种做法的理由往往是,购买人提供了照片,预付了现金,而照片是伪造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要素,预付的现金实际上是伪造居民身份证所需的成本,故购买人客观上为伪造者提供了帮助;此外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伪造居民身份证的共同故意。因此,完全具有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共同行为与共同故意。
然而,上述做法违反当然解释的原理,导致刑法条文之间不协调。因为一般来说,出卖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远远重于购买行为。正因为如此,刑法分则的许多条文只处罚出卖行为,而不处罚购买行为。例如,刑法只处罚贩卖毒品、淫秽物品的行为,而不处罚购买毒品、淫秽物品的行为;再如,刑法处罚销售侵权复制品、间谍专用器材的行为,而不处罚购买侵权复制品、间谍专用器材的行为。既然《刑法》第280条第3款将居民身份证独立于国家机关证件之外,而不处罚出卖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由于《刑法》第280条第3款将居民身份证独立于国家机关证件之外,所以,将购买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直接认定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也明显不当。),那么,较之更轻的购买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就更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
事实上,当然解释的原理可以为许多行为不受刑罚处罚(或者不成立重罪)提供理由。例如:(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必须是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既然某种燃放鞭炮的行为不成立爆炸罪,当然就不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能否构成其他犯罪是另一回事)。(2)既然故意轻伤的未遂不受刑罚处罚,那么,故意轻伤的预备就更不可能受刑罚处罚。(3)既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241条第6款),那么,主动劝说被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的,更加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4)违反配偶意志的非公开的通奸行为不成立犯罪。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理,征得配偶同意的非公开的换偶行为,更不应当成立犯罪。所以,将非公开的换偶(情人)行为认定为聚众淫乱罪,并不妥当。(5)刑事被告人不可能成为伪证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正犯,亦即,刑事被告人作虚假供述或者亲手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的,不成立犯罪。正犯行为是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而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是通过正犯行为侵害法益的,既然刑事被告人不能作为伪证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正犯受到处罚,那么,当其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者毁灭证据时,就更不应当受处罚。(6)行贿罪的违法性比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罪更为严重,具有明显差异的法定刑就表明了这一点。既然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成立行贿罪(《刑法》第389条第3款),那么,因被勒索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就更不应当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如此等等。
第二,当待决事实与基本命题中的基准事实存在多个方面需要比较的事项时,不能仅根据其中一个方面的轻重比较得出最终结论。
待决事实与基准事实既可能只在一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也可能在数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但是,每一次只能就一个程度差异得出当然解释的结论,或者说,对此方面的程度差异得出的当然解释结论,并不当然地适用于彼方面的程度差异。由于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所以,在刑法学中,就违法方面得出的当然解释结论,并不直接适用于责任方面;不仅如此,就违法或者责任中的一个要素得出的当然解释结论,并不当然适用于另一要素。
例如,根据刑法规定,成立A罪仅要求客观方面造成危险即可,但责任形式必须是故意。待决事实是,客观方面造成了实害,但责任方面仅为过失。在这种场合,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只能得出待决事实的违法重于基准事实的结论,但不能得出“对待决事实更应当以犯罪论处”的结论。
再如,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被告人故意参与被害人的故意自杀或者故意自伤的行为(教唆自杀与帮助自杀),原则上不受处罚。德国学者罗克信(Claus Roxin)据此推论:既然如此,被告人参与他人的故意的自己危险化的行为,同样也不能受处罚;比之更轻的过失参与他人的自己危险化的行为,就更不应当受到处罚[10]。换言之,既然故意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在构成要件的作用范围之内,那么,过失教唆、帮助自己危险化的行为,就不可能符合构成要件。但是,这一当然推论并不成立。诚然,从被害人实施行为的角度看,被告人参与的自己侵害(他人的自杀)比参与他人的自己危险化更为严重。但是,如果从被害人的自己决定的角度来看,前者的被害人不仅认识到侵害结果,而且期待、希望侵害结果的发生,后者的被害人只是认识到行为的危险,而且反对结果的发生。(参见:曾根威彦.刑事违法论の研究[M].东京:成文堂,1998:169.)亦即,在参与被害人的自我侵害的场合,被害人放弃了法益;但在参与被害人的自己危险化的场合,被害人没有放弃法益。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在客观违法层面参与被害人的自我侵害比参与被害人的自己危险化更为严重。
第三,基本命题虽然是将基础事实与刑法规范对应后形成的命题,但是,成文刑法具有不完整性(断片性)的特点,这种不完整性同时也是刑法的局限性。所以,当刑法分则明文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时,不能因为刑法存在处罚漏洞或者因为行为罕见而未将其规定为犯罪,而将应当处罚而没有规定处罚的行为作为比较对象,进而将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例如,《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其对象明显包括男性。解释者不能认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非法拘禁罪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明显轻于拐卖妇女、儿童罪,既然《刑法》第240条没有将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非法拘禁成年男性的行为也不成立犯罪。再如,《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其对象显然包括男性。解释者不能认为,侮辱罪侵犯的只是他人的人格、名誉,强制猥亵成年男性的行为,更严重地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名誉;既然《刑法》第237条没有将后者规定为犯罪,那么,对于侮辱成年男性的行为也不得当作犯罪论处。刑法将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排除在《刑法》第240条之外,显然是一种处罚漏洞,而不是因为该行为原本不值得处罚;《刑法》第237条没有将强制猥亵成年男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只是因为这种行为罕见,也不是因为这种行为不值得科处刑罚。所以,进行当然解释时不能将处罚漏洞或者因行为罕见而缺乏规定作为推理根据。否则,被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许多行为,都可能以无罪论处,从而不能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
由上可见,从定罪角度来说,一方面,解释者应当善于适用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避免解释结论之间出现不协调的局面,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解释者应当掌握具体的比较对象与判断方法,要知道待决事实应当与何种规定相比较、相对应,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只有当某种行为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是因为其法益侵害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而不是处罚漏洞或者因为行为罕见而未被规定为犯罪时,才能据此适用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
从处罚的角度来说,举重以明轻原理的适用,首先要求法官确定哪些典型的情节并没有被刑法规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然后,将刑法没有规定的这一典型情节,与待决案件和情节进行比较,判断孰轻孰重;如果待决案件的情节更轻,则不得从重处罚。
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其中之一是“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不管是犯后罪未满18周岁还是犯前罪未满18周岁,其行为均不构成累犯,不成为法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概言之,如果前次犯罪未满18周岁,对于后次犯罪,就不得以行为人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大为由而从重处罚。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毒品犯罪的,不得适用《刑法》第356条从重处罚。《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众所周知,这是关于再犯的规定。与再犯相比,累犯的特殊预防必要性更大。既然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可能成立累犯,那么,当然也不得适用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否则,会导致刑法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在这种场合,解释者不可单纯根据字面含义说,“既然《刑法》第356条没有排除不满18周岁的人,就应当从重处罚”;也没有必要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在修改关于累犯的规定时忽略了《刑法》第356条关于再犯的规定。“法律解释的古典规则早就指出,对规范的解释应尽可能避免使规范之间出现冲突。”[11]在根据字面含义得出不当结论的场合,解释者不能以“刑法规定原本如此,解释者无能为力”为由,维持不协调、不正义的局面,而应当通过各种解释途径,得出协调、正义的结论。即使《刑法》第356条并未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排除在外,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也完全能够将其排除在外。而且,由于这种“排除在外”的结论是对被告人有利于的结论,故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第二,犯罪人在18周岁之前的过失犯罪、一般违法行为与其他不良表现,都不得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也是当然解释的原理决定的。亦即,既然18周岁之前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处罚的故意犯罪,都不能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不成立累犯),那么,18周岁之前的较之更轻的过失犯罪、一般违法行为和其他不良表现,就更不能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第三,既然18周岁之前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都不再作为特殊预防必要性大的从重处罚情节考虑,那么,对于一个18周岁之前没有犯罪的被告人,即使在18周岁之后的一贯表现并不良好,也不得从重处罚。
举重以明轻原理在处罚方面的适用,并不仅限于狭义的从重与从轻处罚,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处罚轻重。
例如,《刑法》第63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问题是,当行为人具有可以(或者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而又不宜免除处罚时,如何减轻处罚?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收受20万元贿赂,妻子乙实施了帮助行为,因而成立受贿罪的从犯。根据《刑法》第385条、第383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甲应当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对乙应当适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但是,乙是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既然有免除处罚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认为对乙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过重,就可以在5年以下量刑。
又如,《刑法》第232条对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规定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对大义灭亲的故意杀人,一般适用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倘若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大义伤亲致死的案件,则面临着如何处罚的问题。例如,父母不希望儿子继续为非作歹,打算将儿子打成重伤,让其一辈子没有犯罪能力,并养活其一辈子,但在伤害过程中过失导致儿子死亡。如果父母实施更重的杀害行为,反而能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现在,父母实施较轻的故意伤害行为,却要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这明显不当。在这种场合,将父母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并无根据,因为父母并无杀人的故意;将父母的行为仅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则没有做到全面评价,也不妥当。合理的做法只能是,适用《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根据《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减轻处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由上可见,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理,并不只是适用于定罪(出罪),而且适用于处罚。在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时,不需要以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范为条件,但不能将刑法的处罚漏洞作为举重以明轻的根据。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量刑一直较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随意确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善于运用当然解释的原理,善于将案件情节与刑法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则会减少许多所谓的从重处罚情节,从而有利于量刑的合理化。
四、举轻以明重
从定罪的角度来说,举轻以明重原理的适用,要求法官确定哪些与案件相关的行为在刑法上被明文规定为犯罪;然后,将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与待决事实进行比较,判断孰轻孰重;如果做出应当以犯罪论处的预判,就应反复对犯罪构成进行解释,不断地将犯罪构成与待决事实相对应,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将待决事实以犯罪论处。
在定罪方面运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进行当然解释形成有罪结论的预判后,还要求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而不能简单地以案件事实比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更为严重为由直接以犯罪论处。换言之,在根据当然解释形成有罪结论的预判之后,又能肯定犯罪构成符合性的,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某种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即使该行为比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更为严重,也不得以犯罪论处。这是因为,刑法具有不完整性,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并非没有遗漏地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所以,一个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与一个行为是否已经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于是,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即使依据当然解释得出的有罪结论具有合理性,也不一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在这一方面,明显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适用当然解释原理形成待决事实构成犯罪的预判,与犯罪构成符合性的肯定判断相吻合。
例如,《刑法》第225条将“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一种行为类型。据此,甲未经许可经营香烟买卖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那么,乙未经许可经营香烟买卖业务,但所销售的均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香烟,但乙误以为自己销售的是真品,是否成立非法经营罪?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理,既然未经允许经营合格香烟的成立非法经营罪,那么,未经允许经营伪劣香烟的更应成立非法经营罪。但是,在本案中,还必须论证伪劣香烟也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显然,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困难。因为香烟属于专卖物品,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香烟以及其他伪劣香烟,都属于香烟。(在这种场合,解释者不能先限制解释法条所规定的物品,然后否定乙的行为成立非法经营罪。)
显然,在根据当然解释原理形成待决事实成立犯罪的预判之后,一般要对刑法规范进行扩张解释或者缩小解释。如果只进行扩张解释或者缩小解释,便能与预判相吻合,那么,就能采纳当然解释的结论;如果只有通过类推解释,才能与预判相吻合,则不能采纳当然解释的结论。
第二种情形是,适用当然解释原理形成待决事实构成犯罪的预判是合理的,但由于不能肯定犯罪构成的符合性,最终不能以犯罪论处。
例如,《刑法》第227条第2款规定了倒卖车票、船票罪,而没有规定倒卖飞机票罪(以前也曾发生过倒卖飞机票的行为)。应当说,倒卖飞机票的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更为严重,似乎可以由“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来说明其构成犯罪。但是,车票、船票的概念不能包含飞机票,所以,不可能根据《刑法》第227条第2款的规定处罚倒卖飞机票的行为。如有可能,只应在其他《刑法》条文中寻找处罚根据。
再如,《刑法》第341条第1款前段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伤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虽然比杀害轻微,但比猎捕、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行为严重。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既然对猎捕等行为适用《刑法》第341条,对伤害行为更应适用《刑法》第341条。但是,单纯的伤害,既不属于猎捕、杀害,也不属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因而不符合第341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不能适用该条。如有可能,只能在其他《刑法》条文中寻找处罚根据。
在这种情形中,对上述行为不能适用相应的法条,不是当然解释存在缺陷,也不是当然解释的理由不成立,而是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如果不采取罪刑法定原则,也可以采纳当然解释的结论。
第三种情形是,适用当然解释原理形成待决事实构成犯罪的预判是合理的,但对于犯罪构成符合性的判断存在分歧,或者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是平义解释、扩张解释、缩小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问题,也可能只是事实归纳与犯罪构成符合性的判断方法问题。
例如,《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倘若行为人让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自己从事危重劳动,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付报酬的,应当如何处理?通用词典对“雇”的解释是“出钱让人给自己做事”,“出钱使别人用车、船等给自己服务”;对“雇用”的解释是,“出钱让人为自己做事”[12]。据此,单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而不“出钱”的,不是雇用。可是,与给付报酬让未成年人从事危重劳动相比,不给付报酬让未成年人从事危重劳动更为严重。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对后者更应以犯罪论处。质言之,对后者以犯罪论处的结论,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这一结论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说,能否肯定后者符合“雇用”这一要素?倘若认为,可以将“雇用”一词中间加一个顿号,将其分解为“雇”与“用”,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其中的“用”,就可能肯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雇用”这一要素,因而具备犯罪构成符合性。但是,这一解释能否被普遍接受,就不是当然解释的问题,而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问题。(这与对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的能否适用《刑法》第263条关于“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存在相同之处。(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8.))
再如,《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问题是,醉酒驾驶飞机的,能否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显然,与醉酒驾驶汽车相比,醉酒驾驶飞机的行为更为严重地危害了公共安全,更应以犯罪论处。运用当然解释原理形成的这一预判,具有合理性。问题只是在于,飞机是否属于机动车?跑道与空路、航道是否属于道路?倘若认为飞机是机动车(如人们普遍接受“空中客车”的说法),并且认为跑道是道路(对此当无疑问),那么,驾驶员醉酒在跑道上滑行的行为,便成立危险驾驶罪。如果这一结论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便出现另一问题,既然醉酒驾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醉酒驾驶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由于对公共安全的危险更为严重,更应以危险驾驶罪论处。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形成的这一预判虽然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在空中飞行属于“在道路上驾驶”的解释,是平义解释或者扩张解释,抑或是类推解释,则是另一问题。
还如,徐某深夜到叶某家向叶某求婚,叶某拒绝并大声吆喝、张扬,徐某气愤,遂用手卡叶某脖子(本人供述大约10分钟),认为叶某已经死亡。后又对叶某实施“奸尸”行为。经法医鉴定,叶某系被他人扼压颈部窒息身亡,叶某被奸淫时尚未死亡(属生前)或处于濒死期。对于徐某的第二行为,在在不同观点(强奸既遂、侮辱尸体未遂、不成立犯罪)[13]。首先,认定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是不当的。徐某的行为虽然符合强奸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徐某误以为叶某已经死亡,因而没有强奸的故意,只有侮辱尸体的故意。其次,认为徐某的行为构成侮辱尸体未遂显然违反当然解释的原理。这是因为,倘若叶某当时已经死亡,徐某的行为肯定成立侮辱尸体既遂;在叶某当时并未死亡的情况下,徐某的行为更为严重,却反而认定为侮辱尸体未遂,这显然不当。最后,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徐某的行为不成立犯罪的观点,更不符合当然解释的原理。显然,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认定徐某的行为构成侮辱尸体既遂才是合适的。问题在于,如何论证徐某当时侮辱的是“尸体”?这主要涉及事实归纳与符合性判断问题。所谓的犯罪构成或者构成要件符合性,并不是指客观事实与构成要件的描述完全相同,而是指客观事实并不缺乏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要素。活体并不缺少尸体所要求的要素,只是比尸体多一些要素。但是,多于构成要件要求的,并不影响构成要件符合性。例如,当公园“禁止将狗或者猫带入公园”,而行为人同时将狗和猫带入公园时,不能认为该行为并不违反公园的规定。(事实上,侮辱尸体中的“尸”实际上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只是区分强制侮辱妇女罪与侮辱尸体罪的要素。(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5.))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明确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应当肯定的是,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都是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所作的解释。但是,当然解释不仅能得出某种解释结论,同时也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理由;类推解释本身并不提供充分理由。当然解释的结论既可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而不是类推解释,也可能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而是类推解释。因为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换言之,在刑法学中,当然解释如同沿革解释、比较解释,只是一种理由,也可以说是一种论证方法,重在说明、论证结论的合理性。但是,结论的合理性,不等于待决事实当然符合刑法规范。所以,根据当然解释形成待决事实成立犯罪的预判之后,在事实与规范对应的过程中,所要做的是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缩小解释)。
杨寿仁先生认为,当然解释处于立法旨趣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内,而类推解释则处于立法旨趣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外。( 参见:杨寿仁.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2,173.)其实,这一区分并不成立。类推解释超出了法条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但未必超出立法旨趣。倘若认为类推解释超出立法旨趣,那么,即使在民法领域,也不能采用类推解释,因为任何超出立法旨趣的解释,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杨寿仁先生也认为民法上可以进行类推解释。可是,说民法上可以进行类推解释,并不意味着民法上可以做出处于立法旨趣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外的解释。
薛瑞麟教授指出:“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的……主要区别是:(1)适用的前提不尽相同:当然解释中的某事实虽然未被刑法明文规定,但它已为刑法有关条文的含义所包容;类推解释中的某事实不仅刑法无明文规定,而且刑法有关条文的含义也不能将其包容。(2)方法不尽相同:当然解释中的某事实与刑法有关条文的含义具有包容关系,因此,它可以直接推论,无须借助于类似性;类推解释中的某事实与援引条文的规定无包容关系,因此,它须借助于两者间的类似性进行推论解释。(3)解释的结果范围不同:前者的解释结果在刑法条文的原意范围之内,而后者的结果则超出刑法条文的原意范围。”[14]在本文看来,这些区别基本上都难以成立。因为:(1)待决事实是否被刑法条文的含义所包含,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有时,待决事实能够被刑法条文的旨趣所包含,却不能被刑法条文的文字含义包含;有时,待决事实能够被刑法条文的文字含义所包含,却不能被刑法条文的旨趣所包含。(2)当然解释或者当然推理,需要借助类似性,需要将待决事实与基本命题中的基准事实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3)“原意范围”是无法确定的。倘若认为原意范围是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那么,当然解释的结论既可能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也可能没有超出该范围。
陈兴良教授一方面认为刑法上的“当然解释之当然,是事理上的当然与逻辑上的当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指出:“当然解释根据事理上之当然与逻辑上之当然,与类推解释的关系有所不同:事理上的当然解释是类推解释,逻辑上的当然解释则非类推解释。”[15]按照这一表述,刑法学上的当然解释是类推解释与非类推解释的统一。但是,这一结论恐怕难以被人接受。其实,事理上的当然解释不是类推解释,而是类比推理。
第二,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时,其中的轻重比较应限于性质相同(至少重合的部分性质相同)的行为。因为性质不同的行为,是难以进行轻重比较的,因而不可能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
例如,《刑法》第353条规定,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构成犯罪。吸食、注射毒品对身体有害,但在通常情况下,不会立即导致身体伤害。与之相比,教唆他人自伤身体的,比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更为严重。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似乎对教唆他人自伤的行为,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但是,这种结论并不妥当。因为《刑法》第353条规定的教唆他人吸毒罪,是对社会法益(公众健康)的犯罪,而故意伤害罪是对个人法益的犯罪。由于法益性质不同,所以,难以通过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原理,将教唆他人自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第三,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时,要区分对事实的归纳与对刑法用语的解释。换言之,不得将对事实的缩小评价或者部分归纳,当作对刑法用语的扩张解释或者类推解释。例如,将故意杀人行为评价为故意伤害,并不是对《刑法》第234条进行了类推解释;将15周岁的人绑架他人后并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并不是对《刑法》第17条的类推解释。这是因为,前一事实并不缺少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素,后一事实并不缺少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素。至于评价是否充分、全面,则是另一回事。具体案件事实总是相当丰富,解释者在归纳案件事实时,必须以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犯罪构成)为指导,进而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刑法规范;而不应当脱离刑法规范,先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然主义的归纳,或者将案件事实固定化,再判断刑法是否规定了这种案件事实。
例如,《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倘若行为人以暴力相威胁“抢劫”国有档案,应当如何处理?或许人们会解释道:“既然刑法只规定了抢夺,而没有规定抢劫,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当然应以无罪论处。”可是,既然抢夺、窃取国有档案能成立犯罪,比之更严重的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也应当以犯罪论处。但这只是一种解释理由,如前所述,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如果解释结论不能为刑法用语所包含,即使是当然解释的结论,也不能被采纳。从规范意义上说,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窃取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抢夺、窃取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当然,如果以国有档案也具有财物的属性,而且抢劫罪不要求数额较大为由,主张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以抢劫罪论处,也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只是以抢夺与抢劫的关系为例,说明可以通过当然解释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至于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是认定为抢劫罪,还是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在这种场合,不是说抢夺、窃取包含了抢劫,而是说抢劫行为并不缺少抢夺、窃取的要素。这与“禁止牛马通过”时是否禁止大象通过的问题,并不相同。因为“牛马”的概念不包含大象,大象也不可能被评价为“牛马”。但是,抢劫行为则能够被评价为“抢夺”。
再如,《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只有“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才可能进而成立事后抢劫。那么,能否将部分普通抢劫评价为盗窃,使其也可以“转化为”事后抢劫?或许不少人认为笔者的以上问题很荒唐,因为盗窃与抢劫是不同的犯罪,既然《刑法》第269条并没有规定普通抢劫可以转化为事后抢劫,怎么能认为普通抢劫还可以转化为事后抢劫呢?
但是,日本刑法理论界的确讨论过此问题。日本《刑法》第238条规定:“盗窃犯在窃取财物后为防止财物的返还,或者为逃避逮捕或者隐灭罪迹,而实施暴行或者胁迫的,以强盗论。”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事后强盗罪中的盗窃犯“不包含强盗犯。强盗犯人为了逃避逮捕等目的实施暴行造成他人伤害的,另成立伤害罪”[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可以认为强盗罪包含了盗窃罪,所以,没有必要做出这样限定的理解。”[17]
其实,只要对相关案件进行比较,权衡定罪量刑是否协调,善于运用当然解释的原理,就可以得出肯定结论。例如,甲傍晚侵入某大厦的办公室,窃取现金5000元后,刚出办公室门即被大楼保安抓获。为抗拒抓捕,甲当场使用暴力,导致保安重伤。甲的行为无疑符合《刑法》第269条的规定,成立事后抢劫;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对其适用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乙傍晚侵入某大厦的办公室,原本打算盗窃,但发现办公室的职员还在加班,便使用暴力导致职员昏迷(事后鉴定为轻伤),抢劫5000元现金。乙刚出办公室门即被大楼保安抓获,为抗拒抓捕,对保安使用暴力,导致保安重伤。倘若认为,不能将乙先前的普通抢劫评价为盗窃,因而不能对乙适用《刑法》第269条,就意味着乙的行为成立普通抢劫与故意伤害两个罪。数罪并罚的结局是,对乙可能判处的刑罚为3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乙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有责性轻于甲。换言之,既然对甲的行为最低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那么,对于更为严重的乙的行为的处罚,就不应当轻于甲。人们习惯于说,对乙的处罚轻于甲的处罚是法律问题,不是解释问题。但本文认为,这是解释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只要妥当地理解盗窃的含义,只要认为盗窃与抢劫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容关系,亦即抢劫中包含了盗窃,就能将乙的行为评价为事后抢劫,进而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从而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甚至还有可能将乙先前的暴力致职员轻伤的行为,另评价为故意伤害罪,对故意伤害罪与事后抢劫实行并罚。这样的做法既实现了全面评价,也没有重复评价。)同样,本文并不是认为《刑法》第269条的前提犯罪包括了抢劫,更不是将《刑法》第269条中的盗窃类推解释为包含了抢劫,只是将乙的前抢劫行为中符合盗窃罪犯罪构成的部分行为评价为盗窃,从而为适用《刑法》第269条提供事实依据。
从处罚的角度来说,举轻以明重原理的适用,要求法官确定哪些典型的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然后,将刑法明文规定的这一典型情节,与待决案件的情节进行比较,判断孰轻孰重;如待决案件的情节更重,则可以将该情节作为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不过,在现实案件中,几乎难以遇到这样的情形。
处罚方面的举轻以明重,也适用于其他对被告人不利的情形。例如,《刑法》第77条第2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另一方面,刑法并没有禁止对数罪并罚后符合缓刑条件的情形适用缓刑。问题是,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期考验期限内,实施轻微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其他条件的,能否再宣告缓刑?答案是否定的。既然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仅违反行政法律或者禁止令,就必须执行原判刑罚,那么,当其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犯罪时,就更应执行原判刑罚,结局是不可能再宣告缓刑。
综上所述,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原理,并不是只适用于定罪,而是也适用于处罚。在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预判后,应当进一步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刑法规范,但不能将对案件事实的缩小评价视为对刑法用语的类推解释。
おお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
[2] 布鲁克?诺埃尔?摩尔,理查德?帕克.批判性思维[M].朱素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231.
[3] 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8.
[4] 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3.
[5] 薛瑞麟.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J].中国法学,1995,(3):75-76.
[6]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
[7]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M]. 严平,编选.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95-196.
[8] 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吴从周,译.台北: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103.
[9] 杨寿仁.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1-122.
[10]Claus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M].C.H.Beck, 2006:402.
[11] 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7.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 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94.
[13] 刘飞.徐某的第二行为应如何定性[N].检察日报,2006-01-16(03).
[14] 薛瑞麟.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J].中国法学,1995,(3):76.
[15] 陈兴良.罪刑法定原则的本土转换[J].法学,2010,(1):7.
[16] 大谷实.刑法各论讲义[M]. 3版.东京:成文堂,2009:2330.
[17] 山口厚.刑法各论[M].2版.东京:有斐阁,2010:227.
Natural Interpretation in Criminal Law
ZHANG Ming瞜ai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Whil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methodology, natural interpretation is a method applicable to laws, in the criminal law it should be deemed as an interpretation reason. A principle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 that where a judge wanted to incriminate an act that was not provided so, he might illustrate some acts punished but in nature were not so serious as the present one and where he wanted to decriminalize an act, he might illustrate some acts that were not punished as a crime but in nature by far serious than the present one. The foundation for that natural interpretation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 teleology of relevant laws. Since the criminal law does not prohibit analogy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while applying the principle to decriminalize the accused, no express provision is required. Nevertheless, no criminal law loophole can be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for such natural interpretation. Since the principle of nullum crimes sine lege prohibits analogy against the accused, while applying the principle to incriminate the accused,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fact of the case should fall within the ambit of the criminal law. However, narrow evaluation of the fact of the case cannot be taken as analogy of criminal norms.
Key Words:natural interpretation;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foundation; principle
おけ疚脑鹑伪嗉:李晓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