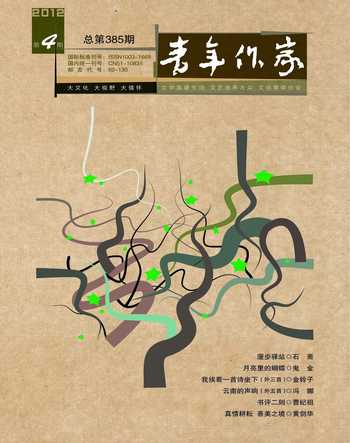难忘雪山那杯水
老韩叫“韩会堂”,部队的老战友都亲切地叫他“韩团长”。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我们一同穿上军装从关中平原奔赴西藏高原的老乡,当时被分在了条件非常艰苦的西藏空军雷达部队。今年春节老战友聚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畅述高原军营的岁月。用餐后洗手时,我刚要把脸盆中用过的水倒掉,老韩忙拦住我,说这水还可以用别浪费了,原来他一直保持着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三十多年的高原军旅生涯中,他有十多年是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雪山雷达阵地度过的。他从当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直到担任雷达部队团长,一直没有离开雷达部队。秋夏时节站在高山顶上,头顶是蓝天白云,远处是茫茫雪山,山下是開满鲜花的草地,牛羊遍地,一幅草原牧歌的美丽图画。可每当他想起在高原的军营生活时,最难忘的仍是雪山上严重缺水的情况。他说在高山上做饭要用水,洗脸洗衣要用水,最关键的是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的油机一刻也不能缺水。高山上紫外线特别强,人体皮肤容易干燥,嘴唇容易干裂,必须要多喝水补充水分,人对水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他常说:“你们无法理解啊!在雪山上,关键时刻,真是水比油还珍贵!”尽管他现在已调往内地,转业后分在省级机关工作,可他还一直保持着每天早上只用两杯水洗漱——一杯水用来刷牙、一杯水用来打湿毛巾洗脸——的习惯,不管是在家中、单位还是出差住旅馆都是这样。他一直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人。
雪山雷达阵地的严重缺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雪山,每年都有长达六个月大雪封山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雪山完全变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这意味着“滴水贵如油”的雪山雷达阵地饮水更困难——每一次取水都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每一次取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记得在老韩所到的第一座海拔近五千米的雷达阵地,一个风卷雪飘的冬日,两位战士上午拿着麻袋下山背水,直到黄昏还不见归来。焦急等待的战友们下山四处寻找,晚间找回了迷路的背“冰”战士——他们已经变成了“雪人”。山上的战士们又冷又饿,有的等不到冰水烧开,就一口干粮一口冰水地吃开了。
有一次,一场罕见的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连队的水早已用完,战士已吃了几天的雪水。上午,大雪刚刚变小,二十出头的老韩就加入了由连长带领几十名官兵下山抢水的战斗。
他们挥动铁锹和十字镐,一点一点挖通了阻碍着通往山下公路上的积雪,到山下几公里外的湖中取水。湖面被封冻了,上面结着两尺多厚的冰!大家轮着用钢钉打眼,在眼里装上炸药,把冰炸开了一个窟窿;接着大家排成一行,把水一桶一桶地往车上传递。突然,战士袁满春脚下一滑,一个跟头摔在地上,被磕掉两颗牙齿。就在大家扶起小袁时,战士张金明也摔倒了,嘴巴撞在水箱上,不但碰掉了两颗牙齿,鼻子也出血了。小袁和小张忍着疼痛,不顾同志们的劝阻,继续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水车在返回途中,陷进了一个深雪洼,任凭油门再大,车轮仍在原地空转打滑。战士们只好再次铲除积雪。山上的同志还拿着木板,把麻袋垫在车轮下,有的套上绳子在前面拉,有的在后面推。水车一米一米艰难地向前移动着,直到黄昏,总算把水拉上了山。
水拉回来了,人却变成了“雪人”——眉毛上是霜,背上是雪,胸前和裤管全是冰,用棍子敲会“邦邦”直响。拉回的水存放在蓄水池,不过三天又结上了冰;冰越结越厚,到头来水全都变成了冰。用水时要用铁锤砸、用钢钉撬,然后再放到锅里烧化。一次,炊事员小张好不容易弄下一大块冰,准备化水做饭,结果冰块太重,他脚下一滑,一失手,冰块“咚”的一声把铁锅砸了个大洞,更遗憾的是把那块冰弄脏了,小张被气得蹲在伙房里伤心地大哭起来。
尽管山上的雪很多,却不能食用。有年冬天,通向湖边的路上积雪太厚,无法到湖边取水,同志们吃了一个月雪水。谁知雪中缺乏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全连官兵个个全身无力,有的还出现了浮肿。全连三分之二的人病倒了,给战备值班带来了很大困难。
每座雪山雷达站,吃水难,洗衣更难。连里规定,冬天一般不准洗衣服,若要洗须经过批准。拉一车水,官兵们要喝、要做饭,油机转动还要用。万一大雪封山时间长了,做饭的柴火很难保证,战备油料更不能动。每逢冬季,大家早就作好长期忍耐的思想准备,不洗衣,不洗澡,衣服实在是太脏了就用雪揉揉。
老韩印象中最深的,仍是在海拔五千三百七十四米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战斗的日子。那里缺氧程度达百分之六十,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但那座雷达站却肩负着每天从山脚下的拉萨机场飞往全国各地的所有航班的导航任务。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宁和西藏的航空事业,这里一直驻守着一批祖国的忠诚卫士。他们的英雄事迹多次被中央级媒体报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被空军授予了“甘巴拉模范雷达连”的荣誉称号。
1991年,从10月22日起,由于拉水车几次发生故障,水没有能及时送上山。阵地用水告急,除了仅有的一点油机用水外,生活用水已停止供应。
26日晚饭后,官兵们围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每个人的嘴唇都已干裂,然而,一杯普通的凉水在十几名官兵中传了一圈,几乎还是原样。
由于几天来饮水严重不足,官兵们动不动就会流鼻血。操纵班副班长谢刚在两天之内已流鼻血十余次,脸色变得乌青,可他用纸团塞住鼻孔,一直坚守岗位。副连长和战友们劝了几次,也没能把他拉下岗位。
官兵们又忍饥挨饿度过了一天。几天来,不少同志出现严重高原反应:体质下降,感冒咳嗽,发高烧,头痛,拉肚子,流鼻血,全身无力。战士梁池新已拉了四天肚子,早已筋疲力尽,然而他一刻也没离开工作岗位;战士容国合病情日益加重,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连走路都很困难,痛得整夜失眠,可也一直坚守岗位。
傍晚,山风“呼呼”地刮着,战士们登上阵地主峰朝山下公路张望,还是不见送水车上来。
怎么办?战友们的体力和战备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油机员杨少喜和战友向开远决定打着手电下山去找水。
一束微弱的手电光朝山下挪动。他俩跌跌绊绊地在山坡上行走,终于在三公里外的一个低洼处打到了一桶浑浊的雪水。
这里平时走路都很困难,然而他们俩却要抬着水在没有路的山坡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上山。
直到晚上十点钟,在战友们的接应下,他俩才一步一步喘着气爬回了阵地。因为一路的磕磕碰碰,一桶水仅剩半桶。望着水,不少战友的眼睛湿润了。
为了尽量延长油机的工作时间,官兵们把水池底的冰碴全部撬起来化成了水。每天,官兵们每两人仅能补充一听水果罐头的水分。
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朝霞满天,阵地上巨大的雷达防风罩球体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那绿色的雷达天线在油机的轰鸣中正常运转着.把红色电波不断传向远方。
关于此事的报道在《空军报》发表后,在军营引起很大反响。官兵们纷纷称这是“和平时期的上甘岭精神”,表示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争做当代合格军人。
老韩说为了水,战士们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献出宝贵的生命。
荡拉山雷达阵地下有座孤坟,每逢战友们拉水归来,总忘不了往它上面洒几滴水。
1973年10月13日的一场大雪,把荡拉山头围困了约半年之久。第二年4月3日,连队组织人力下山拉水,连队的“秀才”丁琦第一个报名参加。谁知冰雪路打滑,拉水车在途中不幸发生意外,年仅十九岁的丁琦那颗年轻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追悼会是在悲壮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遗像,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使人心碎的抽泣声。
水,在荡拉山显得如此珍贵,但是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战士们却又表现出无私的慷慨大方。
老韩一直记得在雪山上吃了多年的柴油、汽油味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刚上雪山阵地,因为缺少蓄水设备,大家只能想办法用水桶、脸盆蓄水。他们把两百升的大汽油桶顶部锯掉,想扣在大火上烤掉汽油味,可不管怎么烧,用汽油桶装的水,上面总是漂着一层五彩六色的油花,喝起来有一股让人反胃的汽油味。老韩说喝平原的水,如同喝了放了糖的水——格外甜。
而且,高山的雪水缺乏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如果长期饮用,会影响视力并导致严重脱发。我们的许多高原战友就是因为饮用了大量的雪水,即使回到内地多年也严重脱发。
或许现在高山连队的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可严重缺水给老韩的记忆是永远难忘的。
尽管我们大多数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区,但珍惜每一滴水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应该像老韩一样,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水源,珍惜每一滴水。
郭中朝,1953年生于陕西岐山,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主席团委员。已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百余万字,短篇小说《姑娘的心》获“西藏自治区文学奖”,长篇系列散文《高原雷达兵散记》分别获空军、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