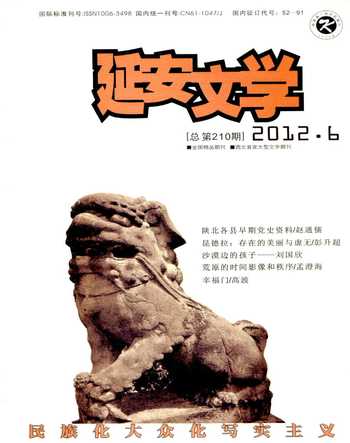识物十二章(选六)
范剑鸣
万物各从其类,
在心灵的枝条长成硕果。
——题记
歌 声
一只鸫鸟骤然起唱
它的歌声
让荒坡上纠结的荆莽,散漫的茅草
顿时获得生命的尊严
万物改变了秩序
瞬间承认了新的中心
我孤独的身影
也突然有了代表人类的理由
一只鸫鸟戛然而止
它的歌喉,如此热烈,蓬勃
造就一条通往神祇的新途
这歌声,纵是春风十里吐露华章
纵是涧水千回,高处日出,低处月落
也不可媲美
当我默默走开
重新走向荒坡边的火车站
却无法把它带给如旧的人潮
无法说出:生命的原理另有所在
琴 瑟
向低音致敬。向低音之外
更广大的沉默致敬
三弦。六弦。五十弦。声音的界线
纤指们涉过的河流。要多少崇山峻岭
才能成就她们的浪花奔腾
低八度。再低八度
就是盲歌手周云蓬的
墨镜和谣曲。就是一匹黑骏马
在灯红酒绿惯坏的耳朵里,踉跄嘶鸣
高八度。再高八度。就是残雷和崩霆
是谭嗣同晚清的肝胆和血
就是一棵大树,接受闪电的裁决
——呵,在不为承认的时代
宁为焦桐,不作栋梁
曲终人散数峰青。我曾是一个弦上之音
但喑哑是音乐的归宿,而孤独
是琴身的命运。仰望星空
多少星辰一声未发……
风 筝
好风是神的呼吸。青云
是梦里花开
攀爬一生,只为安慰天地间
那根松松紧紧的线
安慰那小折叠凳上的久坐
和白发下的望眼——
忽然就过了奔跑的年段
想着栖落,允许敛翅
接受室内墙壁上的一枚钉子
打断地平线的牵挂,和蓝天的惦念
一颗苍老的心,从此顺从风雨
岁月已证实:肉身无法飞翔
只有把内心的块垒掏空
把往事的线轴绕大
在广场,在河滨,在草地
起起落落,都合乎意愿
夜 幕
大街上,酒徒收拾好往事和歌喉
喑哑的影子被月光接住
更远处,星辰在群峰之上
对寂寥的灯火发出最后的邀请
夜已阑。风吹前尘,吹霜
吹铁轨上的笛孔,吹归去来的足音
思想者仍在橱窗寄寓
改换队形,呼吁“养吾浩然之气”
子时已过,喜炮传来乔迁者的宣言
报警器如犬吠于深巷
灵台上,爱的神像悄悄撤回
又悄悄摆上……哦,卧听所得
我可以说出更多,我不敢说出更多
长久以来,一些事物总是在暗中滋养
而我无以回报。现在,就让我报以黎明
报以岁月之初蛋糕一样的光华
报以生之欣幸
花 径
落英打下来。蚂蚁的触角上
微风遇到不可言说的美
花枝的呼吸,让小草
拥有向上的力量
多么欢迎单纯的脚步
无爱,无欲,无思
受缚于造化,又超脱了自然
仿佛蚯蚓的履痕,那样酥轻,低温
从虚线到实线,模仿星宿的轨迹——
这正是我的希望:被人工改变的地表
没有哪一个物种是主角
或者,谁都成为了主角
包括隐伏地表之下
那根茎和土层里潜行的时节
包括,我内心跃动的
一个人类童年的影子
墓 地
遗传和消逝,仿佛大地与天空
如此对立,又如此统一
这是两只惟一掌握时光奥秘的
神灵之手——我多次听到
如此平静的描述:接纳死亡的土地
永远比生存的现场更博大
正如有转化为无
实转化为虚
一切智慧和经验,在这里
转化为情感和青草
有一刻,我从亲情和家族中
超拔自己,立即发现阴阳两界
是如此失衡:我们面向空无
诉说丰富的内心,自始至终忘却
墓地是宽容的盲人和哑巴
多年以来,我们的到来和离开
并没有增加冥界的一点分量
——探究李斯特钢琴曲《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