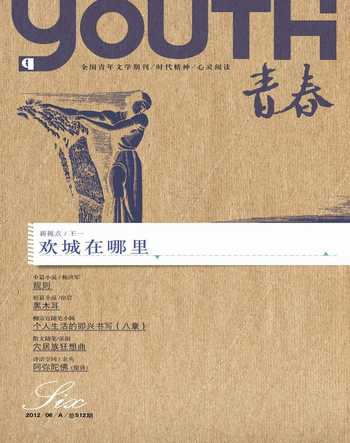幻肢痛
梁熠
那是某一年冬天,我坐在这座城市的酒吧里喝酒,灯光变幻着掠过每个人的脸,麻木和疯狂,交织出现。身边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染了银白的头发,美瞳,浓妆,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幻觉感。还好她们说的是人类的语言,我还能听懂。
我以手支着下巴,看着杯中酒微不可察的一点波动,耳边是嘈杂的音乐和她们的大声的谈话,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她们的谈话内容,似乎有关一具不知名的尸体,没了双手,在这个寒冷到了极点的冬天,被活生生冻死了。发现这尸体的正是其中一个少女,她夸张地叙说着当时她有多么害怕,但末尾她却又补上了一句:“他还那么年轻。”
一个无名尸的消息不足以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却想起了很久之前那个同样没了双手的年轻人——他曾经是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靠着他的双手打破了校队尘封已久的比赛记录,但是一场意外事故让他失去了他的双手。那个孩子来找我的时候带着满脸的无助和恐惧,他额头,眼角的纹路和倾斜的眉毛都告诉我他很悲伤,而他的手,我注意到,还剩下一点可怜的,不忍目睹的残肢,就这样在外面晃荡着。
没有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只是轻声询问他是否感觉还好。他摇了摇头,却又像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似的,望着我,最终还是他的父亲回答的:“他说他还痛,不,不是伤口痛,他还觉得他的手会痛。”他默默点了点头,目光游移着,当他看向我桌上冒着热气的茶杯时,我恰好端了起来,此时他乍然一缩,好像是他而不是我端起了这看上去很烫手的茶杯,随即眉毛上扬,全部挤在了一起,目光越发焦虑了。
“这是幻肢痛……”随后我又进行了询问和测试,完全肯定了他得的就是这一种病。鲜为人知,但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截肢病人术后伴有幻肢痛,并且,没有有效的缓解手段。大家都说这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但要求失去手或者脚的普通人立刻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确实太难了。
发呆和回忆都很消耗时间,总之,当酒不知不觉被我喝完之后,我就起身走出了酒吧。我是这里的常客了,一年零三个月前,我第一次来这里,从此每周必来两次,无特殊情况从未间断过。也许是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吧,熟悉的调酒师,熟悉的桌椅分布,熟悉的舞台,甚至连卫生间的摆设我都能闭眼想象出来。
看了看表,时间是午夜,可是这座城市无眠。大街上跌跌撞撞的酒鬼和夜班归来的疲倦妇人,正在变身恶魔和已经变身恶魔的上班族,还有阴暗角落里娇小妖艳的诱人黑影,一切都刚刚开始,夜未央。我礼貌地推开了一只冰冷的手,并及时拦下了一辆橙色的的士。司机留着络腮胡子,还戴墨镜,我正在惴惴不安怀疑是否坐错车的时候,却听见了广播里温柔轻灵的“心灵之约”,一档以柔情,温婉,纠结著称的节目,遂安心入座,说出了那个有点遥远的目的地,然后习惯性地开始闭目养神。
作为一个医生,或者曾经的一个医生,我很懂得及时休息的重要性,有时候五分钟的睡眠抵得过十二个小时的恶睡。无数车灯在我眼前闪过,思维又开始转回酒吧里那两个少女说话的一幕。关于那个可怜的男孩。
他或许曾经是球场上意气风发的少年,听说他也拥有优秀的成绩和不错的家境。然而到我这儿时,他已经是个可怜兮兮的小男孩了,失去了他的双手,还被莫名其妙的疼痛所困扰,失眠,神经质,喜怒无常,自杀倾向,这些都毁掉了他。第二次来时,是他一个人来的,或许是还保留下来的那一点点骄傲吧,总之,他坚持晃荡着断肢走过两个街区来到我这里,并试图掩藏眼里的痛苦和愤怒。
我所能做的只有给他针灸。针灸,还是针灸。他慢慢开始跟我交流,问我下手狠扎的是什么穴位,什么地方没事最好别碰,什么地方平时还可以多揉揉——最开始我总习惯性地吩咐他“回去之后每天坚持按摩这里……”然而有一天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医生,我爸妈很忙。我暗自叹息一声,以后也就延长了他的就诊时间,算是暂时代替他或者他父母的手,给他做做按摩。这男孩是感激我的,虽然治疗的成效很缓慢,他总是会在不定时刻感受到本不应该存在的撕裂似的疼痛感,治疗不过是减轻了一点儿。
有一天他问我,黑褐色的眼睛里充斥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感情:“医生,我还是觉得我的手还在……”那天半途中下了暴雨,他从头到尾都淋湿了,这是他冲进来之后的第一句话。我知道他有多么想以为他的手还在——这样他就可以自己打伞,吃饭,穿衣,洗漱,看书,上网,打DOTA或是其他,和同学挥手打招呼,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用力地拥抱,击掌,愤怒时可以有力地推搡或是击打对方。
这些我们毫无困难也毫不珍惜的一切,是他此刻最渴望的东西。所以,他还会有疼痛的感觉,也许潜意识里,他仍然坚持,这一切都还在,还没有失去。那天我像个父亲,帮他擦干了身体,吹干了头发,洗了个脸,他眼角渗出的液体也被我擦去,闭着眼的他真像个孩子。可怜的,孩子。
自此之后他好像坚强了许多,也听从了我的建议,去和一些跟他情况差不多的病友玩玩,有一次我看他推门,带着掩饰不住的微笑进来,忍不住打趣了一句,“谁让你这么开心啊?”他居然开始羞涩,只说是在我介绍的那个俱乐部玩得很开心——我也就不再细究了。那个时候治疗终于见了点成效,觉得疼痛的时候变少了,至少我终于可以在他过来的时候喝我的西湖龙井,不必担心他的幻觉了。他的父母很开心,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反而开始有点抗拒我的治疗。有一次我扎针的时候他居然动了,虽然我及时收住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生气。我们互相瞪了半分钟,他投降了,“医生……我不想治了。”“为什么?”他沉默了半天,说:“我……不想没有手。”
那一刻,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到了,二十三块。”络腮胡子的声音倒是很粗鲁,我从回忆和假寐中惊醒,摇摇头,数钱,下车。面前是我半辈子积蓄买下来的小套房,不大,但是够舒适。上楼之后我发现楼道里的灯泡坏了,在黑暗里摸索了半天之后终于把钥匙和锁眼对上了,一扭,房里依然一片漆黑。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点眼眶发热,但是不到一秒之后,我打开了灯,立刻就扑向了书房,习惯性开了电脑又后悔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它关掉。
看着电脑屏幕亮起来,出现一只黑色的小猫,那么安静地望着我,点击,输入那个熟稔于心的密码,小箭头,蓝色的大海,身后跟着猫的男孩的背影,仿VISTA的系统,桌面上没有一个图标。以前想过人死了电子遗产会是什么状况,现在,终于好像明白了。对于一个陌生人,这台电脑将是一个死疙瘩,但对于那些知道密码的人来说,这像是那个人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虽然微小,微不足道,但仍然充满了曾经主人的记忆,冰冷而带着不可侵犯的威严。
屏幕是那样熟悉的蓝色的大海和苍白的月亮,男孩背对我奔跑着,凝固在这一刹那。蓝黑色的猫静静地立着,像是在这个世界里唯一无动于衷的存在。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只想这样看着,手虚按在键盘上,却止不住地颤抖。
一年零三个月,嗯,不,一年零三个月零一天。已经过了零点了。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但是我仍然……觉得痛苦,像那个男孩子一样的痛。虽然真正引起痛楚的东西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仍然无法遏制。很自然地就接着回忆下去,关于那个男孩子,我曾经以为他不能再悲惨了,但是人类的想象力看来真的很有限……
我们对视的那个瞬间,他有点儿惊慌,但更多的是一种绝望的倔强。我终究没法沉默下去,咳了咳,试图说些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了。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那么不想失去他的双手,即使最后残留给他的也只不过是本不应该存在的痛苦。“……它不痛了,就好像,我真的失去它了……从灵魂到肉体……”他喃喃诉说着,虽然别扭得简直像个诗人,我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一震。他好像也很意外,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抬眼盯着我,气氛变得不那么僵硬。我摊了摊手,试图跟他讲明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大堆话在喉间酝酿时,他突然就松了气瘫下来对我说,“我知道,我错了。叔叔,你继续扎吧。”我只能看到他松懈下来的肩膀和往后仰着的脑袋,男孩的头发仍然那么蓬松,一如往日青春,两侧垂下来的无力残肢此时那么触目惊心,我竟然有别过头去的冲动,直到我下意识握紧了拳。从医这么多年来所有曾经被淡忘的感慨和悲哀都在这一刻翻涌上来,我目睹了那么多失去肢体的患者,他们的生活在那一刻像被死神的镰刀划破,从此,一切不再。而这少年,我猜他一定是哭了,也许只是在他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