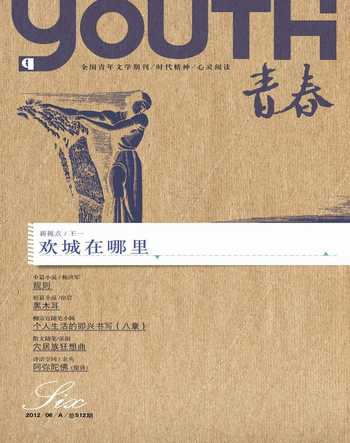黑木耳
徐岩
老范跟自己的女人进山里有两个多月了,头一个月他整天都鼓捣那些木耳菌子。就是把菌种放进封好的罐头瓶子里,或者拿塑料袋扎紧。单等着雨季来临时让其发酵。
后一个月他就锯木头,把从红旗林场伐木组买来的半车木头一点点的锯成段,备着生木耳菌子用。他一天锯几根,排在向阳的山坡上晒着。几天下来,那些木耳段就有气势了,一大片,又一大片,横竖都能数得过来。
两人住的木窝棚比去年的盖得要结实,棚顶特意码了成排的粗木头,是清一色的黄玻璃树杈子,压两层泥才铺了油毡纸的。油毡纸上面又被老范砸了层草皮。离远了看,像罩了张伪装网似的。
老范很为自己在几年前揽下的这桩活计得意。纯粹的手艺活,又不是重体力劳动,每天跟大自然接触,花啊草啊,加之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空气,活得神仙一般。
老范的女人比他小四岁,是后嫁过来的,有模有样的,跟他相看的时候,只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得供她的娃念书。老范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自己身边缺啥也不能缺了女人。拿他自己话讲,这么多年来他亏大发了,再不能对自己不好了。二十几岁就在城里干苦力,扛过麻包,蹬过三轮车,帮人家挖下水道,吃进了辛苦,可到头来自己的原配老婆还是跟人家跑了。原因太简单了,不就是跟着他,日子过得苦吗?
老范没子女,后找的女人年轻,长得还挺有模样,供人家个娃娃念书,是理应做的事情。
大山很清峻,除了树还是树,有着永远都抹不掉的绿色。这绿色其实对于老范来说,那就是一种倚托,一种真正的踏实。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白天在向阳的山坡上干活,不厌其烦地鼓捣那些木耳菌子,淋水、翻包子、植菌种,渴了喝从山根根处泉眼子里接来的水,饿了升火让女人给他捞面条吃。到晚上炖一小铁锅山野菜,放一丁点的咸肉借味,一壶白酒就不在话下了。
老范刚进山的时候,他跟林场的人说,能不能把张广财岭北坡那块林子包给他,哪怕是多加些钱也中。可林场的人没答应他,说采伐的文件上没批那一段呢,是自然林,留做资源的。老范知道那块林子好,树大林密,有利于他的木耳菌子生长。
他在山里通常要住五个半月,经历三分之二的雨季,他种植的木耳菌子会像新出生的婴儿般成长,采摘后晒干,最后拿到城里的集市上去卖,好耳子每斤至少能卖上一百多块钱,多实成呀。
老范在山里这段日子是快乐的,他并不寂寞,离他木耳养殖场不远,还有几个从关外来的养蜂人。他们头上脸上要经常涂抹上新鲜的黄泥,或者扣一顶纱网帽子,在蜂箱旁穿梭。让老范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趣。老范就管他们叫养蜂人,路过时跟他们打招呼,说客气话。还幻想着哪一天能坐下来像一家人一样喝顿酒。
老范管他的女人叫小满。人家其实不叫这个名字,是他在女人过门那天晚上给起的新名。老范跟身材丰满的女人鼓捣完那件有趣的事之后,就跟还处在娇羞状态的女人说,你的名字是你娘起的吧,好模好样的一个女人,咋就叫个那般艳气的名呢,不好不好,俺给你改一个吧。外面不是下雨了吗,雨季来了庄稼好生长,干脆就叫小满吧。女人也没有怪他,想叫啥都一样,有饭吃有衣穿就中。女人原先的名字是艳了点,是一个婶子给她起的,叫马春花。
老范娶了她的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带她到山上来了,两人一块种木耳菌子。
老范先去镇上给她的娃交了学费和伙食费,再购置了在山上生活用的一些用品,就带着新婚的女人离开了村子。
两个人到山上之后都有了新鲜感。老范是觉得身边有了个女人,能在干活疲乏、夜色降临后有人给他做饭,陪他打发寂寞时光;小满则是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大山,一下子就被满眼的葱绿震撼了。她在心里想,这日子是辽阔的,不像那些个她曾经经历过的土里刨食的日子,这绝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老范突然觉得自己浑身好像有了使不完的力气,整日不停地在长满了青草和榛棵的山坡上奔走,伐木头做木耳段,检查菌子的繁殖,去山根根下的泉眼子里背水。累了就坐下来抽纸卷的叶子烟,喝女人给他泡的凉茶水。
有时候老范是盼着天黑的,天黑了他就可以跟自己新娶的女人做那件事,他真想要一个娃,属于自己的娃娃,到老了好养活他。
我曾经以为在大山里搭窝棚住下,种木耳菌子是一份简单轻快的活。其实则不然,那也是一份苦差事。大山是不通火车的,雨季来时雾气也大,树叶子淋了雨,能发出淅淅沥沥的响声。老范早在两年前开始种木耳菌子时就从镇上买了张地图,拿油笔把他所在的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圈住,上面印着的四个小字是红旗林场。
从红旗林场往东,清一色都是逶迤的山脉,其间分布着一些个大大小小的林场和伐木作业点,如大王家林场、韩家园子林场、小孤山林场,大乌苏和小海林伐木作业点。就是这些座座相连的大山,使老范突然间就有了气魄,甚至于说是男人般的精气神。
谁也不知道老范除他刚娶的这第二个女人外,心里还有一个女人,一个已经失去了自由的女人。她对于他来说是重要的,而且相当重要。他们的爱情用一个词可以做概括,那就是昙花一现。老范和那个女人只有一次短暂的身体间的接触。女人姓姜,在镇里开饭馆,一个很小的饭馆,只有三张小木桌。因为买他的黑木耳才熟识了,才对她好。
起初的好只是生意上的接触,女人买老范的黑木耳,老范顺便坐酒馆里喝几杯。女人做生意精明,每次买老范的黑木耳都要讨价还价。老范则略微显出男人的大度来,少一块钱就少一块钱,也掉不了多少肉。自己的心里该有个平衡,人家要是不占你点便宜,干嘛买你的木耳呢。
小饭馆靠山,在山根底下,一条沙土路横穿其间。来小饭馆吃饭的人多半是赶山拉木头的大货车司机,个个都胡子拉碴的,脸上满是倦容。可他们的口袋里有钱,钱装在帆布工作服的里面,一掏出来就是一沓。这些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挣钱是一把好手,喝起酒来也是爷们。他们从不吝惜钱,也不吝惜自己的身体。玩方向盘是没有保险的,何况他们跑的又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安全系数哪说得准呀。
红烧肉和黑木耳炒白菜片是两道叫得响的下酒菜。大货车的司机们从大山深处的伐木场里开车下来,隔老远就听到了大马勺叮噹作响的敲击声。他们的肚子也跟着响了,停车打尖吧,别的事情哪还管得了。
老范跟女人卖了半面袋子晒干的黑木耳,也不急着讨钱,他就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前喝酒。那会儿他的老婆刚跟一个倒腾粮食的男人跑了,心里面正有无禁的哀伤翻来倒去的,不喝点酒咋能消化得了呢。半碗红烧肉、一碟咸菜条,能喝上一两个钟头。反正老范有的是时间,他也需要消磨时间。他喝着酒看着女老板娘的脸,他把女人的脸比做是一朵桃花,快要谢的桃花,可快要谢的桃花也好看啊,也比自己跟人家跑的老婆强呀。
老范喝着酒也等着小饭馆的女老板娘给她付钱,是刚卖的半面袋子黑木耳钱,当然,女人给他结帐时是要刨去酒菜钱的。
那时候女人对他好,是看上了他种植的黑木耳,方圆百里都挑不出来的好耳。肉厚质好,吃起来筋斗又有营养,实乃降血压的纯绿色食品。
那时候女人所谓的对他的好,就是多给他打半两酒,再送他一小碟咸菜,拿新杀的猪肉切细丝炒的卜留克,拌葱花和辣椒油,吃起来特爽口。虽说不值几个钱,但也是女人的一份心意,不是有句话吗,千万别不拿女人的好不当回事,女人不敬早晚是病。
后来两个人就有了那一次昙花一现,有了一次肌肤之亲,那自然是后话,有空闲时还要说的。
红旗林场的人把山看成资源仅仅是两年前的事。
他们把山成亩的包给了承包人,还把一些坡地、沟岗也包给外来的打工者,允许他们种黄烟、种人参、种木耳菌子,让他们养蜂酿蜜,在搞活林区经济的同时,也得到一些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