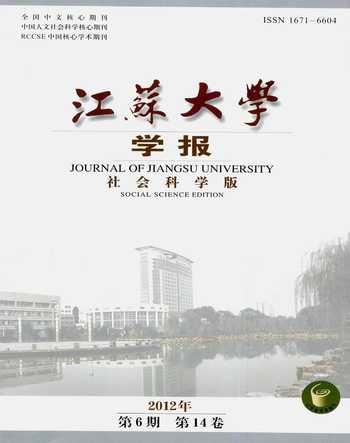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观考论
沈茹
摘要:只有观念意识上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还原其本性,人才能把自然界看成是自己的认识对象,人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自然科学水平才能得到很快的提高。王充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系统的“天人相分”自然观的第一人,他的天人相分思想、“知物由学”的态度以及新“神秘主义”偶会论隐喻虽然没有能在中国开科学精神之先河,但是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词:王充;独立自然观;科学精神;认识论;新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B23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6—0041—05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创立的庞大的两汉“新儒学”,作为汉朝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被奉为儒家的正宗。在认识论上,“新儒学”要求清晰的是人事,而非自然,人事的有机整体性决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于大一统观念下的有机整体性思维,也确定了整体的自然观念,人与自然不分,人与万物不分,一切都在统一中理解,因此理解也只能是混沌的、没有确切的理解,这对逻辑要求严谨、对象性要求确定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当然有正宗就不乏异端,王充就代表着这种异端。
王充(公元27—100年前后),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的细族孤门,“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后汉书.王充传》)。王充“仕数黜斥”的遭遇造就了其鄙视传统十足的孤傲性格和对世俗迷惘的批判精神,其主要思想倾向是“疾虚妄”,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论目的论体系、整体自然观以及当时流行的谶传和纬书,建立了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蕴含着珍贵的独立观念的种子,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一、人的自我觉醒——“天人相分”自然观的形成
汉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从“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以及“天地故生人”推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赋予“天”以人之美的道德品德,并认为“天”的仁爱之德是通过春生、夏长、秋生、冬藏来体现,并实现天、地、人完美的统一,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人感应,以此达到天人合一。王充反对这种天人感应说,认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论衡.明雩篇》),主张“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论衡-自然篇》)。天与人分离,天与人根本无法达到感应沟通与合一。
首先,王充从人和天的量的差异来论证天无法感应人的事实。比如,他在批判君主能引来寒温之气的观点时说:“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不能鸣钟,而萤火不能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论衡.变动篇》),主张天大人小,不能相通。又如,他在《论衡·感虚篇》中说:“夫燠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能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巨也”(《论衡.感虚篇》)。与微火不能沸水,尺冰不能寒夜一样,“人在天地之间,犹虮虱之著人身也。如虮虱欲知人意,鸣人耳傍,人犹不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论衡.变动篇》)?由此。王充认为天能感应人的说法都是俗儒的妄言,不可信。
其次,王充认为天无法感应人的原因还有人与天属性的差异。即天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没有口目,因此无法感应人,他说:“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论衡·自然篇》)?针对有人认为天有如同人的行动,他反对说这只是自然罢了,“曰: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动气也,体动气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气也,非欲以生子,气施而子自生矣。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篇》)。既然天没有意识、无为,那么是没有办法感应人的行为的。
王充还谈到了人与其他万物的区别,他认为虽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但“夫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论衡.辨崇篇》)。人是万物中唯一有智慧的物种,并“好道乐学,故辨于物”(《论衡。别通篇》),所以“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论衡.自然篇》)。他用这种思想解释了杞梁之妻哭倒长城以及蝗虫不侵南阳卓公的荒廖,认为“……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城,土也……无心腹之藏,安能为悲哭感恸而崩”(《论衡.感虚篇》)。物“无心腹之藏”,没有人的情感,所以哭不能使草折断使树裂开,也不能使水冒出来灭掉火,同样哭声也不能感动城的泥土。他认为“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此又虚也。夫贤明至诚之化,通于同类,能相知心,然后慕服。蝗虫,闽虻之类也,何知何见而能知卓公之化”(《论衡·感虚篇》)。在王充看来,蝗虫是“闽虻之类”,显然是无法和人一样具有知晓和判断卓公德化能力的。
王充将人与天和自然万物区别开来,形成了其“天人相分”的自然观,这种“天人相分”是针对人来讲的,可以视为人作为单独个体的自我觉醒。王充对自然无意识、无为的解释使得自然界不再具有人们无法掌握的神秘特征,从而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兴趣,投身于对自然界的探索,一批科学实践家在此时出现,比如蔡伦、华佗、张仲景等等。同时,王充将人和自然界有效地分开,将有意识的自我和无意识的自然界明显地区别开来,认识到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界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自然界成了一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人们有机会把自然界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来观察,从自然界本身寻求对它的解释,并以此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
二、限制与自觉——规律性与能动性的统一
王充认为自然界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但有着自身运动的规律,“日月行有常度”,“寒温自有时”,“雨雪皆由云气发于丘山”,“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论衡·变动篇》)。也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是不会因人的主观感情的“精诚”而改变的,王充断言“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论衡.变动篇》)。他举例说:“荆轲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论衡.变动篇》)。又说“天道无为,听恣其性,故放鱼于川,纵兽于山,从其性命之欲也。不驱鱼令上陵,不逐兽令人渊者,何哉?拂诡其性,失其所宜也”(《论衡·自然篇》),这些都表明了王充对自然界规律性的肯定。
有学者认为,“王充的自然观只强调人的自然性,强调自然客观性对人的制约和规范,……没有看到人在自然客观性面前所显示出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王充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觉的活动认识、把握规律。王充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体现在对自然和对社会两个方面,关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他举例说:“夫肥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论衡.率性篇》)。在讲到人利用水和治理水患的时候,王充说道,“雒阳城中之道无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驰流,水工之功也”(《论衡.率性篇》);“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论衡.顺鼓篇》)。王充说:“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夫,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论衡-自然篇》)。这无疑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统一关系的最好阐释。
在人对社会的能动性上,王充主要关注的是对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道德品行、理想信念的建构。“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自纪篇》),表明了王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德汪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而泉出,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乃吾所谓异也”(《论衡·自纪篇》),这是王充对德行高尚、智慧深厚的理想追求;“身尊体佚,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论衡.自纪篇》)体现了王充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可贵品质;有人讥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论衡.自纪篇》)。王充反驳道:“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膀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杨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通出君山。更禀于元,故能著文。”(《论衡·自纪篇》)这是王充与命运抗争、努力向上进取的精神展现。
王充对自然界的能动性表明了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和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对人类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为人之为人的追求,至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规律的探索,则落入宿命论的泥潭。比如他说“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豁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偶二子命当绝,子兰、宰豁适为谗,而怀王、夫差适信奸也。君适不明,臣适为谗,二子之命偶自不长。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实自然,非他为也(《论衡。偶会篇》),认为所有社会事件都是神秘的“偶合”,这是王充思想中的一大缺陷,当然这种局限性也不应夸大,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王充不知也不可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上、从阶级的现实关系的根基上去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最终实现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偶合”论对科学发展来说,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后面会谈到。
三、学知、考心、效事——认识论
在王充看来,人是万物之中有智慧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上。王充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进一步论述了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一基本观点,并且对认识的两个阶段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做了辩证分析。
(一)“知物由学”
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不仅把天神化为造物主,而且把儒家思想宗教化,把孔子奉为教主,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原因是他先天的智慧,极富神学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针对流行的“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论衡-实知篇》)的观点,王充认为都不可信,“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何以明之”(《论衡.知实篇》)?在《实知篇》中王充用16条证据来证明圣人不能先知。他说“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论衡.知实篇》)”,又说“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论衡.实知篇》),认为所谓圣人所表现出来与常人不一样的才华都是因为得到了很多的经验,运用了推理的方法得到的结论。这些经验和结论都是通过学习得到的,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王充非常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篇》);又说:“实者,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论衡.实知篇》)。
(二)“任耳目、开心意”
王充重视“耳目之实”,即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任耳目以定情实”,可说是中国古代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感觉经验告诉人们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张三看见白的颜色,李四看见也是白的,不可能相反,因为白色本身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人的主观而改变。
他同时又注意到理性思维的作用,“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篇》)。他提出“必开心意”的主张。“耳目之实”是一切认识的客观基础,“必开心意”则是知性的问题。王充认为人们往往是通过感觉经验来判断将要发生的事情,原因是因为通过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运用推理来知道他们的结果。他说:“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论衡.实知篇》)贤人能够先知预见到未来的事情,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视力和听力,都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论得来的。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篇》),从中可以看出王充对认识的总体概括,主要强调了两层意思,一是认识立论要严谨,要合乎逻辑。王充的著作读起来说服力很强,原因就在于他很注意逻辑的严密。王充主张著书立说必须“得实”,而不应该“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要经得起推敲。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丝乱”,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篇》)他举出15个典型事例,逐一加以驳斥。比如他认为儒书记载的“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燋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论衡.感虚篇》)是经不起推敲的。“夫人之射也,不过百步矢力尽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万里数,尧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尧之时,天地相近,不过百步,则尧射日,矢能及之;过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伤日何肯去?何则?日,火也。使在地之。”(《论衡。感虚篇》)由此他认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论衡。自纪篇)。大凡天下的事情,不能夸大与缩小,要考察它的前前后后,其真相就会自然表现出来,那么是非的真实情况就能判定了。认识论中的另一层意思是注重证验,这一点王充曾多次强调,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又说:“凡论事者,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篇》)。对于道家讲自然不讲客观性,他就提出了批评:“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论衡.自然篇》)。《自然篇》明确要求把“论自然”和“引物事”结合起来。这种重严整的方法论“实有科学精神,惜其后起之无人也”。
王充重视逻辑和证验、强调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的思想对科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种思想后来启发了许多思想家,使人们的认识途径更加多样,认识水平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四、偶会——新“神秘主义”
王充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王充在肯定“同气相成”和“异性相截”这类必然性的同时,认为自然界也充满了偶然性,“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论衡.物势篇》),虽然自然界由客观规律支配,但是必然的因果系列之间“二偶三合”产生了偶然,“世谓秋气击杀谷草,谷草不任,凋伤而死。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盛,与之会遇。何以验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极也”(《论衡.物势篇》)。与必然性不同,偶然性是无法预计的,“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论衡·幸偶篇》),也是无法通过感性和理性认识把握的,但是王充认为这与神和上天没有关系,这样王充就给了人认识活动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偶然世界。久而久之,这种神秘主义必将内化为人的精神特征,当然,新“神秘主义”与传统的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反对迷信。
新“神秘主义”起因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不透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在有一天变得完全透明,由此,人类思维永远都会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特征,而它向外探索的本性又决定人类只要生存一天,总要探索不已,追求不止。这种神秘主义“比人性更加崇高,人们不是凭借人性达到这种生活的境界,而是凭借某种神圣的东西进入这种生活境界,有些人要求我们遵循人的思想而生活,我们不能听信他们,我们应该根据存在于人身上的最高尚的东西而生活,虽然这种东西颇为细小,但是它的力量,它的价值远比其他的一切重大”。它体现了这样的特征,即同绝对、无限和不朽联系在一起,直觉、灵感和信仰的因素变得突出,绝对与无限本身就是超理智、超经验和超常识的,直觉和信仰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只要人相信自己以某种不可理喻的方式把握了绝对,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意义。新“神秘主义”与理性并不矛盾,它直接信仰无限、永恒,反对迷信,理性同样反对迷信,二者都鼓励直接面对永恒,勇敢追求真理。新“神秘主义”很快成为人的世界观的一部分,科学家头脑中的神秘主义与科学精神一起是其世界观的内在要素,与世界观中其他的部分构成有机的系统,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协调。
新“神秘主义”是王充自然观中区别于科学精神的另一端,这种神秘主义在王充剔除了迷信的天人感应之后,亟待着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人之为人的冲动的爆发,超出自身的有限、相对与短暂,把握无限、绝对与永恒,追求真善美与自由,把自己的有限存在同具有绝对意义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的行动获得一种意义感和价值感。可以说,这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契机,王充也试图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遗憾的是,王充没有向前一步。
王充不像汉代以及前后的大多数思想家那样被人们广泛关注,因为王充的风格是解说和重复式的,因为“疾虚妄”又导致了王充理论的极端性。但是王充自然观并不会因为被人们忽视而变得不重要。在理论界,有的学者将古希腊自然观的建立作为科学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那种自然观具备了这样的特征:“首先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内在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就从自然观来说,王充的“天人相分”自然观念绝不比古希腊思想逊色,但是命运却迥异。古希腊文化肇始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观思想特征与其他文化形式孕育着使近代西方人受益无穷的科学精神,而王充的自然观思想随着历史的演进却被人们遗忘,最终没有在中国开科学精神之先河(这一原因的探索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尽管如此,王充所建立起的“天人相分”自然观所表现出来的成就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探索自然奥秘时形成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责任编辑张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