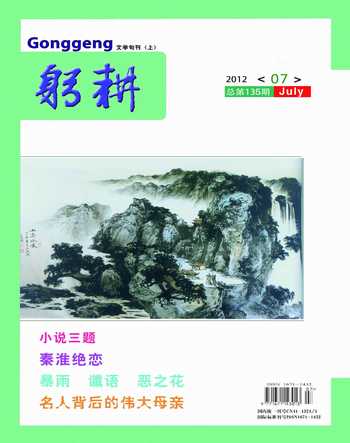小说三题
余显斌
黄花那个黄
1
端午一过,山里草木就显得苍翠起来,一种清新,一种湿润,就缓缓地荡漾开,晕染着整个小村。这时,人家的门前户口,一星一簇的黄色就冒了出来,是黄花。
黄花,这儿叫金针花。
金针花的骨朵,修长,洁净,如一个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羞羞答答的,怕得见人。夏季一到,风一吹,雨一淋,一朵一朵就开了,如一个个怀春的少妇,水嫩嫩的,很是耐看。
女人的金针花,开在田头地角。
这些金针花,是男人栽的。
男人走时,把田头地脚都整平了,每一个土坷垃都敲碎,每一个坝豁子都砌好。田里种着的是麦子,麦苗儿青绿一片。田边地脚呢,就种上金针花,一担一担的水浇上,然后,拍拍巴掌,站在旁边,吸上一根纸烟。看得高兴了,也吼上一嗓子:哎,什么子弯弯弯上天?什么子弯在大江边?什么子弯在长街卖?什么子弯在姐跟前——
歌,是这儿的山歌,唱起来有些粗野,有些沙哑。
女人听了,红着脸,一双毛眼眼就水了,就润泽了,一颗心也就飘起来,一直飘向远处,飘向山的那边。眼睛前的,就有一个货郎子,开着一辆三轮车,突突突的,向远处开去,一直开到夕阳里。
货郎是个俊眉俊眼的后生。
货郎也会唱歌,甚至,比男人唱得还好,还入耳。那时,女人还不是女人,还是个女孩时,就认识了货郎。
女人那时十八、九岁,也是端午前后,天气潮潮的,润润的。女人背着挎篮,摘着金针花,一边摘着一边哼着山歌。女人嗓子很好,像银子,清亮亮的:什么子红红红上天?什么子红在大江边?什么子红在长街卖?什么红在姐面前……
歌刚唱罢,一个声音就接上了:太阳红红红上天,荷花红在大江边,辣椒红在长街卖,胭脂红在姐面前……
女人忙回头,一个小伙子站在地边不远处的路上,是货郎。经常的,他会开着三轮车进山,收木耳,收草菇,收桐籽。因此,女人认识他。
货郎住在黄家墩,离女人这儿也就五十来里。黄家墩那地方,女人去过一次,路过那儿,一沟的活水,一坡的人家,还有一山的桃花。
没想到,黄家墩还是出好小伙子的地方哩。
2
女人爱吃金针花。
金针花一摘,开水一烫,下锅就捞出来,不要烫得时间太长,不然,这么娇嫩的花儿,禁不住的,会烂在锅里。
烫过的金針花,捞起来,薄薄地摊在竹席上,放在房子里,慢慢地阴干,那颜色,就像刚从枝上摘下来的,金黄亮色。要吃时,抓一把,放在洋芋片中,热醋一烹,就是一盘,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很香,很脆,也很筋道。
当然,木耳炒黄花,或者凉拌黄花,都很好吃。
货郎爱吃,货郎吃着,咯吱咯吱的,吃罢,说,梅子,蛮好吃的哩。
她笑,说,不是好吃,是好吃吧?后一个好吃,是说人嘴馋的意思。
她娘在一边,就嗔怪,笑骂她,这女娃子,牙尖嘴快的。
她一笑,甩着长长的辫子跑了出去。外面,一对尖嘴子黄羽儿的雀雀在树枝上跳上跳下,互想啄着羽毛。
远处山上有人唱歌:高高山上一树槐,妹在树下望哥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槐花早就开过了,一树青绿。金针花才刚刚开,一溜儿一溜儿的,开在地脚,开在田边。有的人家,在门前空地边上,用青竹打一道篱笆,土一松,移栽来一丛一簇的青绿,端午前后,风一吹,雨一洒,就有金黄色冒出,一天一个样,开始是小黄点,接着如小指一般,几天后炸开,一朵一朵,金黄金黄的。
这时,村里人就忙开了,摘起了金针花。
女人也忙开了,摘起金针花,做出各样的菜,用磁盘装了。爹爱吃,娘爱吃,村人也爱吃,吃了还夸,梅子这巧手,以后不晓得哪个小伙子有口福。
有小伙子在旁边,吃了金针花菜,还想得便宜,涎着脸说,谁?我哩!
女人脸红了,啐一口,说做梦哩你。
那时,十八、九岁的女人,就如一朵金针花,含苞待放。里面含着花蕊一样的心事,很细很嫩的心事,谁也不知道。
一切,本来都商量好好的,女人和货郎计划了:再一次,货郎来到村子,就向女人爹娘叫明,然后提亲。
再然后,两人就结婚。
可是,世上的事咧,咋就那样多变。
就在货郎来到女人家,吃下第一顿饭后;就在女人和货郎商量好婚事后,货郎开着车子,突突突地走了,一直走出女人的视线,走出山垭口,走到山的另一边。
女人每天站在村口,等啊望啊,望穿了眼睛,再也没有等到货郎来。
货郎让人捎来了话,嫁人吧,我结婚了。
女人不信。女人不信不行,这样的话,谁敢拿来开玩笑?
女人没去问,女人也不会去闹去叫。女人的泪水哗哗地流,她劝自己,那人都那样了,自己何苦?人家把自己当泥巴一样,一下子扔了,自己为什么把人家放在心上?
女人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做,可就是做不下来嘛,就是想哭哩。
女人在床上睡了半个月。半个月后,爬起来,红着眼睛,打点起精神,去了她姨那儿,假装走亲戚。
在她姨那儿,她才晓得,货郎真的结婚了。
货郎娶的,是一个残废女孩。
那个女娃是个好娃哩!她姨说,会挑花会绣朵,也会侍弄地里的活。这女娃喜欢上了货郎。这女娃痴,为了那小伙子,险些丢了命哩。
女人听了,睁大了眼。
她姨告诉她,那次,货郎出去购货了,货郎老娘病了,医生后来说,是急性阑尾炎,不是送得快,会送命的。那女娃是邻居,晓得了,骑上自行车,带上货郎老娘就向医院去,到了医院才想起来,当时心急火燎的,忘记带钱了。于是,又骑上自行车,回去拿钱。回去的路上,骑得急,撞上了车,一只腿残了。
她姨叹口气,一个好女娃,一只腿一瘸一瘸的,咋找婆家啊?
女人听了,也叹口气,眼圈红了。
货郎回来,到女孩家去,看见女孩捂着被子抽抽噎噎地哭,谁也不见,饭也不吃。货郎坐下来,轻轻地说,小芳,如果你不嫌弃我,就嫁给我吧。
女娃一家都不信,睁大了眼。一村人听了,都不信,也睁大了眼。
货郎牙一咬,几天后,推着女娃一块儿到了乡上,扯了结婚证。
女人听了,坐在那儿,咬着唇,咬着咬着,两滴泪落下来,沿着长长的睫毛滑下。她姨不知道内情,就说,瓜娃,你哭啥哩?
她说,姨,那——两个人都是好人。
她姨叹息,好人哩,真是好人!
她本来准备送给她姨两包金针花,临了,改了主意,拿出来说,姨,你替我送给他们吧,这是我点心意。
她姨接过东西,叨咕说,傻女子,你又不认得他们,送的啥礼?再说,人家爱吃不?
爱吃……哩——她抽咽着,侧过头去。然后,跑出姨家,肩膀一耸一耸的,走了。远处山上,雀雀儿叫着,唧唧唧哩——唧唧唧哩——叫得一片欢实。
她姨站在那儿,一脸狐疑。
3
回家不久,女人就嫁人了,嫁给同村的一个小伙子。
她的男人不赖,地里家中,都是一把好手。结婚后,知道她喜欢吃金针花,把田头地脚都种上了。他说,梅子,我让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金针花吃。然后,就傻傻地笑。
她也笑了,说,那我还不吃得满脸黄,成了黄脸婆。
婚后的日子,就这么清淡如水。女人也缓缓开放,如一朵刚炸开的金针花一样,一身清爽,一身洁净。男人也让她上坡,但不让她种地。男人让她坐在前边,看着自己种地。村里的地,都是沙子土,半土半沙,时间长了会板结的。男人把猪粪背到地里,把地掏了沟,将猪粪,还有庄稼秸秆埋进去,一发酵,一块地就变得泡乎乎的,一场雨后,一锄头下去,半尺深。
她要动手,或者抓粪,或者挖地,可男人不答应,让她坐在前面。男人挖一下,抬起头望她一眼,笑一下。她脸红了,问他,望啥哩?
好看嘛!
丑哩!她说。
他说,真丑哩,比一朵嫩嫩的金针花还丑。
她“扑哧”笑了。有时,这个实诚人说起笑话来,也蛮逗人的。看她笑了,他更高兴了,扯开嗓子吼起山歌来:妹在院中摘黄瓜,哥在外面撒土巴,打掉了黄瓜花啊!打掉了公花不要紧,打掉了母花不接瓜,回去怕爹娘骂啊……
声音很粗,也很野,在山沟里飞出,远远飘开来。
她的眼睛,这时候就会望着远山,望着飘摇的白云,眼睛里又汪出一层水意,慢慢溢出来。男人见了,忙问,咋的,梅子?
她说,迷灰了。
他忙扔了锄头,跑过来。她揉揉眼,回头一笑,好了呢。说完,又抬起头望着远方,过了好一会儿,轻声说,金针花要开了咧。
他点点头,是哩,金针花要开了。
金针花一开,一个村子,就浮荡着一片花香,淡淡的,薄薄的。村子里的人,尤其女人,就忙起来。大清早的,踩着露珠,趁花儿正鲜时,提着篮儿,一朵一朵地采下,装进篮中,回家烫了晾干,放在那儿。
这时,货郎就会来,收下金针花。
金针花,近半年才有人收,是镇上的人收。
镇上人爱吃金针花,可又不会做,把金针花一切,和粉丝杂拌在一起一调,取了一个很高贵的名字,叫金银丝。货郎到镇里交货时,去吃了金银丝,连声咂嘴,说这是金针花呀,我们那儿到处都有。
老板听了,睁大了眼,说不会吧?咋会呢?
货郎呵呵地笑了,吃一筷儿菜,告诉对方,真的,晒干以后,挑木耳香菇,哦,对了,还有莲菜洋芋片,醋一烹,那个味,啧啧!
货郎又想起女人,想起五月的金针花,想起女人摘金针花时那笑笑的眼,那长长的头发,还有那亮亮的歌。货郎的心中,就有一丝痛疼,过电一样在心里划过,就喟叹一声,哎——
老板不知道货郎哎个啥子,望了望,递一支烟说,能卖给我不?
货郎眼一亮,行啊!
货郎知道,大家种那么多金针花,换不来钱,光吃,也不是个事儿。再说,生意成了,栽种金针花的人能卖得钱,自己也能从中间弄点小利,补贴一下家用啊。货郎当天就回来了,第二天,就开着三轮车,来到了女人所住的村子。
货郎没敢去看女人,货郎一想到女人,心里就麻缠得慌。货郎在心里想,甭想甭想,都是有家的人咧,别对不住婆娘。可是,自己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要想。
货郎想,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货郎开了价,一斤十五块,老板掏十五块二。货郎对每个人都说了这个价,不这样,他心里总感到对不起什么人似的。对不起谁啊?一时,他又说不出来。
第一次收了金针花,货郎走了,走了好远,回过头去望望村子,长叹一声。
第二次收了金针花,货郎长叹一声,望望村子,开着三轮车走了。
第三次,货郎再也忍不住了,打听到女人的家,去了,站在门外,大声咳嗽了一声。一会儿,一个水水白白的女人走出来,看见货郎,愣了一下,又愣了一下,說你——你来了,进屋坐。
货郎不进屋。货郎搓着巴掌,笑了一下,说不进去了,我是来收金针花的,十五块,不,十五块二一斤,好价钱哩。女人最近回了一趟娘家,老娘病了,照看老娘去了,一点儿也不晓得。女人又让货郎进屋坐。货郎摇着头问,兄弟在家啊?女人知道是问男人,女人摇着头,男人走了。男人整好地,种了庄稼,在金针花还没冒芽时,就去了镇上,给开饭店的表哥打下手去了。
货郎更不进去了,站在檐前,让把金针花拿出来,一秤就走。
女人白了他一眼,说我不吃人。虽然这样说,仍转身进去了,不一会儿拿了金针花出来。货郎秤了,找了钱,说,你这儿一斤十五块二,其余的十五块,我得挣点油钱哩。女人知道,货郎是怕她出去说错了价,和别人的两样,自己再来,就不好交代。
货郎要走了,扛起蛇皮袋,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有手机吗?号码给我,再来,我就不上门了,打个电话。女人晓得,货郎是避嫌。她摇摇头,想想说,我最近不回娘家了,你来了,我耳朵放精细点儿,就晓得了。
可是,话虽这样说,女人心中,很想很想有个手机。
女人看着货郎走远,软软地倚着门槛,像一朵雨后的金针花,纤纤细细的。
4
村里人都很惜地,命根子一样,好地平地都种上庄稼,绿乎乎一片。地边儿上遇着一窝儿土,也不能闲着,移一丛金针花,栽在里面。这样以来,田埂边,小路旁,去茅厕的路边,阶檐下,都是一片葱绿一簇嫩黄,天一暖,一只只蜂儿赶来,忙碌地嗡嗡嗡着,扇动着烟一样的翅膀。
跟着蜜蜂忙的,是村里的人们。
女人更忙,男人栽的金针花,本来因为女人爱吃,到处都是:井旁沟边猪圈边都栽上,就是院中一个破瓦罐,他也倒了一筐土,栽上几颗,端午一过,一片嫩黄。
现在,女人舍不得吃金针花了,那是钱哩。
女人把金针花摘了,烫过,晾干,收藏起来。
镇子离这儿不远,男人一星期回来一次。他表哥说的,屋里有新媳妇,那块地不能荒了。男人就回来了,放下东西,拿了锄头,到地里去走一趟。他说,走一趟心里就安生些。
晚上,熄了灯,男人仍不歇着,又把另一块地细细翻整一遍,一边翻整,一边还把表哥的话学说着。
女人说,我也是你的地啊?
男人说,你是我第一块好地,最好的地。一边说,一边气吁吁地喘,牛一样使劲。
第二天走时,男人一再嘱咐女人,吃好穿好,地里的活儿有我,甭瞎忙。女人知道,男人这是疼自己哩,可自己也不能好吃懒做呀,这样,自己成了啥人了?女人仍然上坡下地,喂猪锄草。每天早晨,第一个起来,踩了一地清亮的露珠,去了地边,采摘金针花。
金针花的品相,一般是开了的没有未开的好,未开的又比不上将开没开的。
男人不放心,拿了表哥的手机,打隔壁大嫂的电话,让女人接。女人接了,男人在电话里问,没下地吧?
女人忙道,没,听你的。那边,男人放了心,结束了,还忘不了嘱咐两句,吃好,穿好。然后嘿嘿一笑,挂了手机。
大嫂在一旁直乐,把女人嫩嫩的脸揪了一下,说,快告诉他,就说我欺负了你。
妯娌俩笑了一会儿,女人回去,又忙去了。女人心里,有一个暗暗的想法,想买个手机,然后,把号码给货郎,让他来收货时,给自己一个电话,甚至和自己说两句话。那次见面,她有很多话想问他,他现在过的好不?送去的金针花好吃不?新媳妇咋样?可是,见面了,都为了避嫌,都没说什么,就那么站了一会儿,货郎就走了。
有了手机,就能问了。心里,她觉得这样想不好,可就是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心,心里要想哩!
女人晒的金针花,已经有三十五六斤了。
每天,外面麻麻亮,女人就提着篮子走出去,到了地角边儿,一朵一朵摘起金针花来,细长的手指翻飞着。清晨的金针花上,沾着露水,一颗一颗晶亮晶亮的。露珠中的金针花,有一种洁净的黄,一点也不沾灰尘。
女人一边摘着花儿,一边向远处望着。
薄薄的雾漾满山谷,也遮没了林子,雀雀儿在叫着,嘀哩嘀哩——清清亮亮的。远处的雾中,不晓得哪个人在唱山歌,响亮亮的。歌声在雾中弥漫开,扩散到山的深处去了。
太阳出来了,雾慢慢散开了,一方方平展展的地块,一片片绿乎乎的麦苗儿,一线线的金针花,一间间的白房子,还有鸡鸣,还有炊烟,出现在眼前,把整个村子罩上一片祥和的光。
女人不断地抬起头,望着山外的路。
路上没有人,只有早晨柔柔的阳光在流荡着。一只狗摇着尾巴,在阳光下慢慢走过去,后面跟着几只小狗。
不见货郎,也不见三轮车。
女人想等货郎来,然后拿出金针花卖了,买一款手机。女人问了,一般的手机也就四五百块,不贵,不远处一家店铺就有。到时,女人卖了金针花,就能在手机中听到货郎的声音了。女人也可以在电话里轻声问他,那个——嫂子对你好不?甚至,她都想好了,叮嘱他,让他好好过日子,要对“嫂子”好。
5
货郎来的时候,是一个下午。
货郎不是一个人来的,三轮车上,还带着他的老婆。他老婆跛着一条腿,坐在车旁,拿着个包,给卖金针花的人找着錢。女人拿了金针花,也来到三轮车这儿。货郎低着头,不说话,秤了金针花,三十六斤五两。然后,给老婆报了斤数,他老婆给女人数了钱。
别人的,仍是十五块。
女人点了一下,说你多给了。
货郎老婆抬起头,俊眉俊眼地一笑,说还是按十五块二。过去,我当家的没少打扰你。
女人没说话,眼圈儿涩涩的,有点红。货郎老婆眼圈也有点红,拍了拍她的手,妹子,姐都知道。姐对不住你啊。女人忙低了头,抬起头时,说,姐,你说啥话啊?走吧,去我那儿喝口水。
货郎老婆忙,没功夫。女人轻轻拍拍她的肩,走了。太阳光已经斜下了,房屋,还有树的影子都斜铺在地上。女人心里很轻快,这一会儿,竟无一丝沉重感,太阳光好像照到心中去了一样。
离家老远,女人就看到一个黑点在门前晃动,走近了,是男人。
今儿个是星期六。男人又回来了,整理自个儿的地了。男人还带了一款手机,孩子似的,攥在手心中,猛地往外一亮说,给你买的,喜欢不?女人眼睛亮了一下,轻声埋怨道,你啊,花那个钱干嘛?
男人不回答,却笑着问,哪儿去了?
女人说卖金针花去了,一斤十五块二,值钱着哩。女人说时,眉眼亮亮的,一脸阳光。
男人一听,说吃亏了。
女人一愣,望着男人。
男人说,自己和表哥说好了,送去一斤十五块五。
女人脸色有些白,她不是心疼那点钱。她心里有种受骗的感觉,很是难受,可又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喃喃道,涨价了?男人马上否定了,没涨价,别处都是十五块二,只有表哥,因为是亲戚,照顾的。说完,转过身向村头走去。
女人想想,脸上又舒展开来,喊,去哪儿?
男人回答,找货郎,拿回金针花呀!
女人愣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男人没拿钱哩!咋找人要金针花?她忙也向村口跑去,心里却泛起一丝一丝的波纹,如黄昏夕阳下的水面,怎么也静不下来。
远远的,她看见了男人。男人站在一棵大白蜡树下。白蜡树的一片绿荫团团地罩着他。男人并没赶到三轮车那边,而是远远地望着三轮车。
太阳的斜照里,货郎已收起秤,装好了金针花。然后笑笑,走过去,轻轻抱起老婆,放在前排座位上。老婆头上不知粘了根草,还是别的什么,货郎很小心地拈起,扔了,又拍了一下她的肩,然后坐下,准备开车。
女人来到男人身旁,小声问道,咋的不找了?
男人长叹一声,他们也不容易,我这一喊一嚷,村人都晓得了,都来要,他们一天就白忙活了。
女人没说话,望着男人,过了一会儿埋怨,你啊,婆婆妈妈的。女人说时,白了男人一眼,心中,有一种自豪,更有一种满足。男人第一次被女人这样水汪汪的眼睛一瞥,嘿嘿笑了,很舒服。
女人悄声说,回吧,晚上做金针花拌木耳,你再喝几盅。
男人笑了,突然,转过身,准备向三轮车那边跑去。女人问,又干啥呀?男人说,天黑了,货郎又带着个残疾女人,行动不便,晚上就在咱家歇着吧!
女人不。女人拉着男人的胳膊,红着脸轻声问,夜里不整地啊?
男人嘿嘿笑了,说想哩,可——
女人腻声道,放心,人家是黄家墩人,摸不了黑儿。说完,轻轻一拉男人的胳膊,然后转过身,先自向家里走去。男人听了,张张嘴,也忙转回身,跟着女人走了。女人回过头,笑着骂声馋嘴猫。骂完,望着笑笑的男人,也笑了。
她想,明天,买款手机送给男人,自己有手机了,两个有时也好说说贴心话,用别人的不方便哩!
芹儿的伎俩
1
芹儿下山时,天已是黄昏,晚霞沁透了半边天。
远远看去,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芹儿如一只小小的虫儿,在慢慢地移动着。夕阳红红的,把山映红了,把路也映红了,把山路上的芹儿映成了一个半红半黑的影子。
羊回圈了,牛也回圈了,放牛的王老汉的咳嗽声也隐入暮霭中,渐去渐远。
夕阳照着山下一弯田,田地弯来弯去,抱着山根转。地边的树林中,高高低低地错落着一间间房子,黑瓦白墙,屋脊高高翘起。
这个村子叫冯湾,其实,并不是湾,是一个沟,一弯一绕的,老长。村里有二三百户人家,从沟头一直扯到沟尾,就是一个村。芹儿的家,就在村子的中间,旁边,是几棵高高大大的树,浓绿一片,如一滩绿水荡漾着。树林中,有个老鸹窝。
老鸹爱叫,尤其傍晚的时候,哇哇地叫着。
老鸹叫声中,还夹杂着人声,是芹儿婆婆的。
远远的,芹儿就听到了婆婆的声音,加快了步子。
芹儿的婆婆很麻缠,这点,芹儿是知道的。平常里,有一点儿不如意的事,婆婆都会叨叨咕咕半天。芹儿听了,只是笑笑。人老了,嘴就碎,话也就多。私下里,芹儿总是对根生说,劝劝娘,嘴少一点,左邻右舍受不了。
根生一笑,说,你劝吧,你是媳妇啊。
芹儿说,你是儿子,她听你的啊。
根生去说,可是,说过一遍,管不了几天。几天以后,婆婆仍是那样。没办法,几十年的性格。芹儿一边想着,一边快步向家走去。夕阳下,山风轻轻地吹着,很是凉爽,也吹乱了芹儿头上的头发。拐过一个山嘴,是一座土地庙,很小,但每年正月初一十五,烧香放鞭炮的人很多。站在这儿,能清楚地看见自己院中的柿子树,在夕阳下,一团黑红。婆婆的话也变得清晰起来,渐渐能听得清了。
婆婆说,咋就死了啊?
芹儿一听,身子一软,脚下一滑,险些歪倒下去。她撑着锄把,努力地支撑着自己,心里一忽闪一忽闪的,站在那儿。
婆婆的声音继续传进耳朵,好肥的芦花鸡啊,正下蛋啊。
芹儿吁了一口气,擦擦额头的汗,心里暗暗埋怨,真老了,有些犯糊涂了,说话也说明白啊,一惊一乍的。一边想着,芹儿一边扛起锄头,下了河,上了河堤,过了车路,进了自己家的院子。婆婆看见芹儿,举起芦花鸡让芹儿看,告诉芹儿,在路边那块地里捡回来的,夹子夹的。说着,用嘴呶呶那块地。
那块地,是秀子家的。
芹儿没说什么,放下锄头,打了盆水洗起脸来。婆婆生气了,说,我去找她,问她为啥欺负人?
芹儿擦净脸说,算了吧,都是一个村的。
婆婆不依不饶,一定要去。芹儿看勸不住,就吓唬道,根生可说了,你再闹一次,他的村长就没了。婆婆一听,愣了一下,立时没了锐气,放下芦花鸡,呆呆地望着,然后坐了下来,慢慢地摇着蒲扇。
芹儿见了暗暗好笑,心说,老小老小,老人如孩子,真没说错。她搬了个小凳子坐下来,摘了菜,刮了洋芋皮,进了灶房,“咝啦咝啦”的声音随即响起来,香气也飘出了厨房。
整个村子,炊烟也都一缕缕升起,已经到了做晚饭的时间。
2
根生去镇上了。镇政府离这儿有一段距离,五十多里路,隔着几条河,有几条街道,还有青石板的路。芹儿娘家在别处,没去过,但听根生说起过。
当了村长,根生整日忙得如风车一样,团团转。芹儿见了就笑,咋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根生说,是呀,第一把火先烧你。说着,瞅老娘没在家,拦腰一把把芹儿抱起来,抱回房中,一脚关上了门。结婚才一年的小两口儿,馋嘴猫儿一样,抽空就缠上了,可咋吃也吃不饱。
一般的,根生去镇上,天就是再晚,也一定踏着一地月光赶回来,抹着脑门子上的汗嘿嘿笑。芹儿就劝,天晚了,就在镇上歇着,那儿有旅社啊。
根生摇头,一脸坏笑,说不放心你。
芹儿很是不解,望着根生。根生说,这样美的媳妇放在家,怕打野食的。
芹儿就笑,就掐根生。两人打闹着,嘻嘻哈哈的。窗子外面,一片月光照进来,水一样清白,也水一样洁净,笑声,如水中盛开的睡莲一样。
可是,今晚根生没有回来,打电话回来说忙,事没办好,明天再说。
芹儿没问啥事。芹儿不像别的女人,把男人看的死紧。她也相信自己的男人,他说有事,就一准有事。所以,芹儿和婆婆两人吃着饭,稍微有些冷清。饭桌上,婆婆又谈起鸡的事,说真气人,给鸡下夹子,毒哩。
芹儿说,人家也不一定是给我们家鸡下夹子啊。
婆婆说,也只有我们芦花鸡去。
芹儿“咯”一声笑了,望望婆婆。婆婆很不满,说,傻女子,亏你还笑哩。芹儿说,娘,你知道芦花鸡去人家地里啄食,不拦着,怪谁!
婆婆说,那也不是她的地。
芹儿知道,婆婆顺不过气的就是这点。老人没事干,闲不惯,看见路边有一点地荒着,就去挖了,准备种点菜。秀子却不答应,硬说是她的,因为在她地边上。于是,扯上篱笆一扎,种上了庄稼。
婆婆一时气不过,芦花鸡去啄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它。
今天天黑,婆婆看芦花鸡没回笼,就一边叫着,一边到处找,找到那块地边,看见芦花鸡死了,被一个夹子夹着,夹子正夹在脖子上。
芹儿看婆婆还在生气,就说,你不是说你儿子累嘛?
谈到儿子,婆婆脸上松弛下来,叹息一声,管着三百来户人哩,能不累嘛?说着,一脸不满的样子。芹儿知道,婆婆心里高兴,心里悦意,脸上故意这样的。芹儿一边吃着饭,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要是有啥东西补补就好。
婆婆一下子想到了芦花鸡,说炖鸡汤啊,嫩鸡汤最补人。
芹儿说,你不是让秀子赔钱嘛,赔钱,鸡就给人家了。
婆婆不说话,吃罢饭,摇着蒲扇,过了一会儿,站起来,向房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随你哩,你说咋的就咋的。老人有些麻缠,但不糊涂,知道媳妇心里想啥:哎,邻里相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婆婆睡了,芹儿也回了房,躺在床上,可是怎么也睡不着。
男人一走,房子就显得空空的,没有了一点生气,也缺乏了一种喜气。芹儿翻了几个身,仍然睡不着。一片月光照进来,映在蚊帐上,白白净净的,如一团水色。窗外的阶檐下,传来土狗子的叫声,吱吱——,吱吱——,一会儿长,一会儿短的,乱着人的心。
芹儿听着虫声,眉头紧紧地皱着。
芹儿生气哩。
想起白天的事,芹儿不能不生气。
表面上,芹儿笑着,对芦花鸡的死,好像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那是做给婆婆看的,免得火上浇油,也免得婆婆生气。可是在心里,芹儿仍不悦意,对秀子的做法有些不满。
她想,秀子嫂,你也太不讲理了,咋能和一个老人一样?那点地,别说不是你的,就是你的,又咋的?你不是放在那儿荒着嘛,老人开出来了,咋的,就是肥肉了?就成了你的了?
芹儿想,欺负一个老人,你不害臊啊?不看我婆婆的面子,就不看看我们的啊?
芹儿想起那次下雨的事:好大的雨啊!山上涨了水,秀子的屋里进水了,看看快泡垮了,秀子一家急得直哭。当时,不是自己男人带着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去把东西抢出来的嘛?为这,自己男人的腿撞在石头上,鲜血直流,留下一条长长的口子,现在还结着痂。
好你个秀子,当时你和你男人感激得啥一样,转过身才几天功夫,咋就忘了呢?
芹儿的心中,奔马一样,咋样也静不了,咋样也睡不着。她想,明儿个,自己咋样也要去问问秀子,这样做,是人吗?人,能把良心一扔,啥都去做吗?
但是,迅即,她又否定了,自己劝自己,算了算了,都是好姐妹,抬头不见低头见,别把事情做绝了。再说,她错了,自己让她一步是对的;如果一吵,不也错了,和她一样嘛。
窗外的虫声渐渐稀少了,露珠一样,东一颗西一颗的。月光也渐渐西斜了,几片甘露叶子的影子映在墙上,风一吹,一摆一动的。
芹儿的心也如甘露叶影子一样,轻飘飘的。
慢慢的,芹儿睡着了。外面,虫声东一声西一声,已经十分零落。露水也上来了,一片雾罩着小村。小村也睡了,睡在一片月光一片薄雾中。
4
根生打电话来了。
根生一出外,就打手机,一天几个。芹儿埋怨,不怕电话费啊?嘴上这样说,心里甜甜的,这是男人在乎自己啊。每次接根生的电话,芹儿的眉眼上都是一片笑。
根生在电话中说,事办成了,就回来。
芹儿说,啥事啊。
根生很得意,用广告词回答,我不告诉你。
接了电话,芹儿就去了地边的水沟。水沟里,一片篙草,一片苇子,密密麻麻的。一到盛夏,篙草一人高,绿乎乎一片,人一进去,就没了影子。
水沟里,长了一片水芹菜。
芹儿经常去水沟里,把水芹菜采回来,一腌,放上辣椒丝,存在罐里。有时,有客人来,喝酒时,捞上一盘,又辣又酸又脆,很是上口。嫩水芹菜采回来,芹儿将它一切,用醋一烹,然后,再打两个鸡蛋,一搅一拌,做成汤,喝上一碗,酸酸的,鲜鲜的,很是解酒。
根生爱喝这汤,几天不喝,就闹着让芹儿做一碗。
这汤,芹儿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芹菜鸡蛋汤,可根生偏不这样叫,偏叫芹儿鸡蛋汤。喝酒了,芹儿问,吃点啥?根生说,来一碗芹儿鸡蛋汤,别的嘛,随便。说着,一双眼望着芹儿笑,贼亮贼亮的。
芹儿问,望啥哩,我脸上有花啊?
根生说,有啊,真的。说着,趁芹儿不注意,“啧儿”一声,在芹儿脸上亲一口,然后,一碗汤喝下去,出一头汗,又生龙活虎了。
今儿个,根生在电话里说,自己在下面喝了点酒。芹儿一听就知道,他想喝芹菜鸡蛋汤,关了机,就提了个篮子,去了水沟里。
虽然是夏季,可是沟里凉凉的,手伸进水中,一种凉意顺着指尖漫上去,浑身的汗意都没有了
芹儿专捡最嫩的芹菜采,不一会儿,就是半篮子。采的差不多了,她蹲下来,捡一个水塘洗起来。塘儿不大,瓷盆一般大小,水里有小小的几尾鱼儿,还有一张细眉长目的脸。手伸下去,鱼儿一惊,一甩尾,进了浮萍中,一波一波水纹就扩展开。
正洗着,河沿上传来说话声:一个是秀子,一个是王嫂。
芹儿本来想站起来打个招呼,可是刚起了这个念头又停住了,因为王嫂和秀子正在谈论昨天的事。
王嫂一边洗菜,一边说,秀子,昨天夹子到究竟是你下的,还是你男人下的?
秀子也在洗着菜,回答道,他?有那个胆?
芹儿的眉毛皱了一下,烟一样。四边静了,草丛中,虫儿振翅的声音传来,还有青蛙跳水的声音,“咚”一响,两个女人洗菜声也能听见。过了一会儿,王嫂悄声说,为啥啊?他们两个小的不差啊!
秀子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咋呢?王嫂问。
芹儿也侧起耳朵,生怕露掉一个字。
这儿的人把“咋的”问成“咋呢”,那个“呢”字拖得很长,一波三折,很是好听。才嫁过来时,芹儿一听到这个“呢”字就好笑,现在却一点也不想笑,只是咬着唇,静静地蹲在草丛中。
一般的,她不愛偷听别人的话,那样不好,爱扯是弄非。
可是现在,她却没有这种想法,她急于想知道原因。一直以来,她和秀子都不错,有说有笑的,亲姐妹一样,她就弄不清秀子这样做是“咋呢”。
我们盖房申请交到根生手上,现在还没批下来,他想咋呢?秀子一边洗菜一边说。
王嫂压低声音,没送点啥?
没!秀子说。
你啊,王嫂大悟似地点拨道,你光生气不行,得送点东西。我娘家侄子,洪垣的,知道吧?申请交上去,半年不见影,送了两条烟,一瓶酒,不几天申请就批了。
秀子听了就骂,说现在人都咋呢,芝麻大的官,就那样坏,那样贪财。王婶就劝,为了盖房,再犟,也犟不来申请,是不?两人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叽叽咕咕上了河堤,上了车路,走了。
芹儿抬起头,天上的几丝云轻悠悠地飘着,草中的虫儿噤了声,没了动静,天也快晌午了。她想,自己也得回家做饭了。
5
芹儿回到家,又到菜园中摘了些豆角,割了一把韭菜拿回来,刚坐下,秀子的男人刘记就来了。
刘记提着一个纸袋进了屋子。芹儿见了,让刘记坐了,忙擦了手,泡了杯茶拿过来,放在刘记面前,又递上一根烟。刘记站起来接了。芹儿说,刘记哥,你比我大,咋还这么大的礼性?
劉记连说应当的,应当的,然后坐下,点了烟,对芹儿还有芹儿的婆婆说,伯娘,妹子,我来,是给你们赔不是的。
芹儿没想到,这么快,刘记就会上门来赔不是,一时,她反应不过来。屋子内静静的,门外,只有雀雀儿在叫,叽叽喳喳的。风吹来,凉爽爽的。芹儿想了一会儿,说,刘记哥,都是一个村的,有啥啊?
刘记说,昨黑的,我就把秀子骂了一顿。
显然,刘记在说谎。这是个实诚人,不会说谎,脸红了,沁出了汗。
婆婆也说,没啥,都过去了。
婆婆就是这么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别人惹下了,一张嘴不让人,可是,见不得人服软,一服软,立马心就软了,一切记恨,还有别的什么气,都烟消云散了。
芹儿也说,真的没啥,别往心里去。
刘记不,仍然发恨,说这婆娘该打,回去了,看不揭她层皮。
芹儿听了“哧”一声乐了。刘记胆小,怕秀子,那是村里出了名的。一次,刘记和别人斗牌,村里一个小伙子开玩笑,跑去喊一声,快跑,秀儿来了。话没说完,刘记就没了影子。一直到上午吃饭时,秀子喊了几次,刘记才踅摸回去,在门外一躲一闪的。秀儿见了问,咋的不回来吃饭?
你——你不揪我耳朵呀?刘记捂着耳朵问。
无空无影的,揪你干啥?
刘记这才晓得,自己上了别人的当。这话传出去,一时笑倒了一村人。
听了刘记的大话,婆婆也笑了,说这孩子,又在吓我们了——好了,过去了,别再提了。刘记一听,忙“哎”了一声,站起来,拿起袋子放在桌上,说,这是给村长的一条烟,放这儿了。
你——这是干啥?芹儿急了,不收。
刘记说,为了我们的房子,给村长添了不少麻烦,应当的。说完,放下东西,几步走了出去,待到芹儿赶出去,刘记早走远了。芹儿想去赶,又怕传出去全村晓得了,好说不好听。
她站在那儿,眉头又拢起来,如烟一样。
太阳很大,一片儿一片儿照着村子,只有雀雀儿不怕,在叫着,一声又一声。站了一会儿,芹儿摇摇头,走进了屋子。婆婆看着桌子上的东西,看见芹儿进来,就问,这是咋呢?
芹儿有些不高兴了,说,咋呢?你儿子喜欢啊!
不会吧?婆婆说。
不会?咋不批申请?
婆婆坐下,不说话了,摇着蒲扇,摇了一会儿,长叹一声,不会吧,这个孩子?那话,仿佛是在问自己,又仿佛是在问芹儿;像在安慰自己,也像是在安慰芹儿。
6
根生回来时,正是晌午,太阳白花花的一片。蝉声稠密如雨,从枝叶间流泻下来,婉转而流畅。根生一脚踏进屋,汗也顾不得擦,就问他娘,芹儿呢?他娘指指厨房,摇着蒲扇,一句话也不说。
根生望望娘问,娘,咋的,生谁的气!
他娘摇头,说去端饭吃吧。
根生“哎”了一声,几步进了厨房。芹儿正在忙着,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根生悄悄走过去,在那细细的腰上捏了一把。芹儿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说,嫌人。
根生挠着头,大惑不解,问,咋呢,和娘拌嘴了?
芹儿没回答,拿起菜刀,把锅盔切了,放在盘中,让根生拿出去。然后,又拿了几盘菜,放在了桌上。一家三口坐在桌旁,吃起了锅盔。芹儿接着又去了灶房,给婆婆拿了一碗汤,然后又给根生拿了一碗,特意用的海碗。根生笑着说,还是老婆疼人。
芹儿说,说这话,娘会见怪的。
根生听了,赶紧说,娘也疼我。说完,拿起海碗,美美地喝了一口,皱着眉,慢慢咽下汤道,这汤味道不对啊,咋有一种香烟味?他娘不信,也尝了一口自己碗里的汤,说,胡说哩,喝酒了吧?
芹儿不说话,阖着眼睑,默默地吃饭。根生拿着筷子,在汤里搅了搅,汤面上,顿时浮起一些烟丝。根生看见,开玩笑说,芹儿,咋的,烟丝也能当调料啊?
芹儿停了筷子,说,你不是爱香烟吗?我就给你放在了汤中,让你吃个够。
根生说,我啥时候吸烟了?
那,你为啥害得刘记给你送烟?芹儿红了脸,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根生傻住了,瞪着眼睛望着芹儿。
芹儿不说话,走进屋去,拿了那纸袋和烟,放在根生面前。根生娘絮叨开了,你啊,人家交份申请,咋呢不给东西就不办哩?说着,连连摇头。
根生看看娘,又看看芹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大印的表,让她们看。芹儿认识,是刘记的盖房申请表。根生说,昨天去镇里,专为办这的,办这的人不在,所以等到了今天。
芹儿听了,忙拿起海碗,走进灶房,换了一碗汤。根生不喝了,拿起香烟,向外走去。芹儿赶出来,说,咋呢,生气啊?汤都不喝了?
根生说,还是把表先给刘记,免得他着急。说完,踏一地阳光,向外面走去。
身后,传来芹儿的娇嗔,快些回来,给你把汤热着,好好喝几口,冲冲烟味。声音清亮亮的,消散在阳光里,一片明净。
飘过小城的旗袍
1
走出门时,太阳很好,亮得如水洗过的一样。珠儿左右望望,没人注意她,用手轻轻抿了一下鬓角,轻轻地向楼下走去。院子里,花树一片一片的婆娑着,阳光下浓浓淡淡的影子,清凉凉的。
这花草,都是张舟闲下来时侍弄的。
张舟夸口说,自己会侍弄三样事,一是文章,二是花草,三是女人。当时,张舟正在侍弄着珠儿,嘿呀嘿呀的,让珠儿吐着舌儿,一翘一翘的,猫儿叫春一样。
珠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想回过身走上楼去,手机响了。打开来,是周天的。周天在那边急切地道,姐,来了吗?
珠儿说,算了吧,不好的。
周天说,姐,求你了。
珠儿脸有些发热,她摸摸脸儿,又向四边看看,没有人,甚至连蝉声也薄了一点。院内静静的,一只鸟儿飞来,望着她,叽哩叽哩一叫,又飞走了。手机那端,周天继续求道,姐,亲姐姐,来吧。
珠儿轻轻关上手机,眼睛又四周望了一下,转过身子,一步一步向院外走去。可是,她总感觉到有双眼睛在望着自己,像是张舟的。猛地回过头,什么也没有。她暗吁了一口气,骂自己疑神疑鬼,张舟去开笔会去了,半个月后才回来哩。
但是,她心里仍咚咚地响,敲鼓一样,有些不安。鬼使神差地,她还是走出了院子,一步一步,走向“香居阁”。
珠儿进城已经四年了,四年里的珠儿,无论是衣着,还是生活习惯,以及语言,都和乡下时的不一样了。
在乡下,珠儿有一块茶园,绿乎乎的茶树从山尖一直扯到山脚,像一匹缎子。茶园旁边有一条水,从一股泉眼里流下,弯弯曲曲亮得如银子。珠儿在茶园中锄草、剪枝,手胳膊一扬一扬地施肥。累了,就到溪水边洗把脸,水中,就会映出一张白白的脸儿。珠儿对着溪水中的人一笑,手上一滴水珠落下,一圈圈的水纹儿,会遮去水下的人儿。
采茶时,珠儿更忙,挎了篮子,在茶林里来往,长长的手指,捏住茶芽一拽,就是一枚鹅黄的茶芽,嫩嫩的,小小的,白米大。一天下来,能拽四五斤。茶芽不能用指甲掐,不然,掐痕处会变黑。经常的,遇见来采茶的游客,珠儿会解说,会翘着手指给大家示范。
可是,那些都是四年前的事了。
四年前,乡下的珠儿穿着花衫子,梳着辫子,在茶林间穿梭。现在不一样了,四年如水,已经彻底洗刷了珠儿身上的土渣味,洗掉了珠儿身上采茶女的痕迹。珠儿已经是城里人了,十足的城里人。
珠儿沿着街道走着,不时的,有眼光扫到她身上。珠儿的嘴角挂着笑,手上拿着个小坤包,缓步地走着,白色的高跟鞋叩在地上咯咯地响,素色的旗袍,在阳光下招展如水。
旗袍,是张舟买的。
高跟鞋,也是张舟买的。
张舟喜欢旗袍,尤其喜欢女人穿旗袍。在文章中,他塑造了很多美女,每一个美女都是一袭旗袍,一双高跟鞋。他说,旗袍高跟鞋天生就是为女人准备的,穿上它,女人会生色不少。
他说,尤其像珠儿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为旗袍高跟鞋长的身子,一穿,嫩如青葱。
他说时,在珠儿身上精耕细作着。珠儿呻吟着,一个身子招展得如一袭旗袍,波澜起伏。
她曾问过张舟,潘小杨怎么样,穿上旗袍?
张舟说,也好。
珠儿问,是人好,还是旗袍好啊?
张舟笑了一下,点着她的头说,瞎想什么?
她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了。
潘小杨是一个文学粉丝,一双眉眼漾漾地生着水色,很崇拜张舟,经常上门,或让张舟签名,或让张舟指点文章。有一次上门,特意穿了一袭旗袍,看见张舟,眼睛闪了一下,问道,咋样?
张舟笑道,很好!是吧,珠儿?
珠儿笑笑,也说真的很好。
潘小杨说,还是张老师指导的呢。说得珠儿一愣,张舟更是一愣。潘小杨见了,咯咯咯地笑了,忙解释道,是按张老师文中主人公的着装样式搭配的。张舟听了,才吁口气笑了。最近,他写了一篇小说叫《旗袍招展》,里面有个女主人公,果然是这样装扮的。他笑了后,就望了一眼珠儿。珠儿明白,这眼光里有责备,也有不满:人家都知道这样,你咋的就不穿那旗袍?这个意思,明明显显地望了出来。
今天,珠儿穿上了旗袍。第一次穿上这件旗袍,还有这双高跟鞋,镜子里,立时出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典雅女子。
这旗袍真是为女人生成的呢,一穿上,一个身子真就妖妖的媚媚的了。珠儿暗暗有点后悔,早知道这样,就早穿了,让张舟好好看看。张舟说,自己累死了,想松弛一下神经,就在珠儿身上纵马驰骋,狂野放荡。
可是,对张舟要她经常穿旗袍的要求,珠儿一直没有答应,她觉得旗袍太露,迈不开步,一迈步,白森森的大腿就露出来了。因此,这袭旗袍就一直放在衣柜内,没穿上身。
周天是在聊天中知道的,就一声声哀求,让她穿上,在视屏上让他看一下。
在家中,左右无人,再加上经不住这个小男孩一再姐姐、姐姐地哀求,她羞羞答答地穿上了,坐在视屏前。
周天的眼睛睁大了,道,姐,你不是人,是神仙。
她“噗”的笑了,問,对每一个女人都这样说?
他傻傻地摇头,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她。她又“噗”的笑了,心里漾满了满足,还有喜悦。结束时,他要求,以后这袭旗袍只穿给他看,别人都不许看。
为啥?她问。
你是我的。他说。
她脸红了,眼脸低下,道,霸道!
他说,姐姐,求你了,行吗?
看着他惶急的样子,她鬼使神差地点点头。那边,周天欢快地说,你真好,美女姐姐!这孩子,十八九岁的样子,嘴甜得抹了蜜。和他聊天,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又回到十几年前的十七、八岁,又回到早恋的时候。
所以,这次会面时,周天要求她穿上这身旗袍高跟鞋,她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临了,又剪了一朵百合花斜插在鬓边。
2
和周天相识,是在网上。
进了城后,珠儿无事,每天坐在电视机前,一部韩剧,看得又流泪又吸溜鼻子,雨打芭蕉一般。看过后,就去做头,逛商场,买菜,做饭。
电视看长了,也腻味了。
张舟说,上网玩吧。
珠儿不会,摇头说,不会,玩啥啊?张舟说,一上去就会了。然后放下手头的稿子,教她怎么上网,怎么玩游戏,甚至怎么聊天。
几天下来,珠儿就成了一只网虫。这是张舟说的。张舟讲课回来,珠儿在上网。张舟从书房的稿子堆中爬出来,珠儿仍在上网。开始,珠儿是游戏,不爱红装爱武装,爱上了四国军棋,可是,打一仗败一仗,以至于在网上几乎无人和她一伙儿,有的上去了,又把她踢出来。
珠儿很生气,也很受伤。
这日,周天和她一伙儿下了一盘棋,大获全胜。然后,又和她一伙儿杀了一盘,又一次大获全胜。她很高兴,说,今天全靠你了。
他说,你技术也不错啊。
她知道他在恭维自己,笑了笑。
以后,每天,他们都成了一伙儿,在网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她很高兴,也很满足。
他要加入她做朋友,她接受了。
他要她的Q号,她给了。
他要求她视频,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们由幕后的战友,终于走到前台。在视频前,是一个眉眼青葱的小伙子,自我介绍叫周天,然后就喊她美女妹妹。
她笑了,说,看样子,我比你大呢。然后说出自己的年龄,今年三十三。
他先惊讶于她的年轻,接着就笑了,告诉她,自己今年二十岁。
那我——就是你阿姨了。她说。
不,姐姐。他说,并马上喊美女姐姐,而且顺杆就上,让她喊宝贝弟弟。她不喊,他就固执地要求,一次两次三次,至到她喊了,他才高高兴兴地停止。
再上网,他们下棋少了,聊天多了。他告诉她,自己在这个城市打工,做头发的,有一天她去了,他一定好好接待她,给她做个头发。姐,你头发一盘,再插一朵花,百合啊什么的,一定美得如天仙。他说。
她笑着调侃,在别的女人面前也这么说吧?
他说,才不呢,给钱也不说,姐,我说的实话。
她不说话,但心里很舒畅。一个三十二三岁的女人,能让一个二十不到的小男孩倾倒,她的心中,有一种快活,一种悦意和满足。
“香居阁”在城的东边,绿树一抱,荫浓一片,很清雅的一个地方。
和周天在网上认识已经半年了,网恋时,该说的不该说的他们也说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开始,珠儿不,但是,架不住周天苦苦哀求,这孩子嘴甜,水磨功夫也老道,一番死磨硬缠,她抵挡不住。每一次上网,她都给自己定一条最后的防线,暗劝自己,怎么出格,也不能越过这个线。可是,每一次她都会在周天的姐姐长姐姐短下,最终,让这道防线土崩瓦解。
幽会,是她的最后一条防线了,然而,她仍没有最后守住。在周天的几乎跪求下,她走出碉堡,缴械投降。她知道,这样做对张舟不公平,可是,理智有时在冲动的攻击下,总是薄如白纸。
她最终答应了,去“香居阁”,在那儿,周天订了一间房子。
周天那一刻感动极了,连发了十句姐姐你真好!
她说,你真是我的小冤家。
这句唱词一样的话,是她无师自通甩出来的。过去从没用在张舟身上,现在却顺理成章地用在周天身上。
她觉得,如果正像张舟说的,自己的身子是为旗袍而生的,那么,周天这孩子的出现,大概就是为自己而来的吧!在他的甜言蜜语中,甚至在他的姐姐长姐姐短中,她昏昏沉沉,抛弃了所有的规则,还有道德底线。
她来到“香居阁”大厅,很担心,怕遇见熟人,左右望了望,然后走进去,问服务员,请问周天在哪儿?声音很轻,蚊子一样哼哼,以至于服务员没听清,问道,谁?
周天!她说,脸已全红了,鼻尖甚至沁出了汗。
服务员查了一下登记册,然后告诉了她在405房,一边说,眼睛一边审视地望着她。她鼻尖的汗更多了,几乎是逃一样地向405室走去。
周天的手机又响了,说姐,你在哪儿?
她没立刻回答,而是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又准备回头,回答说,算了吧,周天,这样不好。
周天急了,說姐姐,好姐姐,你要不来,我就跳楼。
她闭上嘴不说话了。周天焦急地问,姐姐,你在哪儿?
她告诉他,自己就在405门外。门“哗”一声开了,周天出现在面前,拉住她的手一扯,两人进了房。周天抱着她,一边喊着姐姐,一边亲着,一边用脚踢上门。这孩子手劲很大,箍得她透不过气来,头脑有些发晕,身子有些发软,迷迷糊糊如同做梦一般。
他喊,姐姐,美女姐姐。
她闭着眼,轻轻“嗯”了一声。
他的吻落下来,舌头很坚强,撬开她的唇。她体内关闭的火焰顿时冒出火苗,熊熊燃烧起来,也积极回应着。一刹那间,床上扭动着两具洁白的胴体。
一切结束,她又冷静了。
她坐起来,匆匆穿起衣服。他仍留恋不舍,抚摸着她的身体,问她,姐姐,下次——下次弟弟让你更高兴。
她不说话,穿上丝袜,高跟鞋,拢了头发,向外走去。他抱住她,姐姐,啥时候再这样?
她摇摇头,掰开他的手,低着头向外走去。
3
她收到一叠照片时,已经是几天后,正坐在家里看电视。打开照片,她顿时傻了眼,然后,脸又红了。照片上,是她和周天的床照,两人光着身子,极尽全力地扭曲着,表现出一种极度的亢奋。照片是信封送来的,好在张舟不在家,不然,她不敢想象会出现什么后果。
信封中,还夹着一张纸条,只有一行字:要想保密,赶紧打五万块钱来。纸条后面,是一串账号。
她头脑发晕,鼻尖上,汗粒又一次一颗一颗钻出来。
这照片是哪来的?她安静了一会儿想,那天出门,她总感觉到张舟好像就在背后看着她,不会是他吧?她拿出手机,给张舟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那边通了,是张舟的声音,轻声道,在开会呢,有事吗?
她忙一笑,说没事,想你哩。然后,关了手机,看样子,是自己多想了,张舟是去开会了。不会是服务员吧?她想,听说时下常发生这事,服务员拿了野鸳鸯的照片,索要金钱。可是自己去时,只有一个女孩啊,问了405室之后,那女孩就转身走了,咋可能?
她想到周天,会不会也收到了同样的照片,会不会是他受到了别人的跟踪,或者,是他说漏了嘴。现在的小孩子,不知轻重,爱拿着自己的情人到处夸耀,为这她没少嘱咐他,千万别说漏了嘴。虽然他信誓旦旦,可谁也保不住一高兴就“哇哇”出去,被人暗暗跟踪啊。想到这儿,她打开手机,拨了周天的电话。
手机里一片盲音,然后一个女声道,对不起,你拨的是空号。
她的心里有点发沉,有种上当的感觉。周天这孩子,人虽小,鬼却大,他讨好女人的手腕太熟了,熟得好像一个老手。过去,自己晕头晕脑的,被他的甜言蜜语罩着,喝醉了酒一样,分不清东南西北,现在一想,心里直发冷,而且,越想越觉得真有那么回事。
她上了网,去了Q上,周天的号一直黑着,黑得如她此时的希望一样。她留了几句话:周天,拿着那叠照片索要钱财的真的是你吗?请回话。
写到这儿,她鼻尖酸酸的,有种想哭的感觉。隐隐的,心灵深处,她感觉自己仿佛如一个弃妇。
Q上,消息像一粒盐撒在海水中,荡然无波。她急了,又去了游戏上,终于找见了周天,就发了一句话,你这样对我,公平吗?游戏上,头像一闪,周天消失了。从此,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一片,再也不见了她心中的那个小男孩了。
她知道,她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
她坐在那儿,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心很疼很疼,遍地鲜血。她甚至想,就这样纵身一跃,跳出窗外,一了百了。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她忙跑过去,拿起手机,并不是周天的,是一个陌生号码,恶狠狠地问,钱准备好了吗?
她说,让周天接电话。
说这句话时,内心里,她还在希望,希望对方说,啥,周天是谁?这样,她心中也许会好过一点儿,即便拿钱,她也会拿得心里舒畅一些。可是,对方并没这样说,连她最后一点自我安慰与自我哄骗,也让对方给击垮了。手机那边道,别做梦了,他没功夫。接着,是叽叽咕咕的笑声。
她停了一会儿,泪水奔涌而出,对着手机疯狂地喊道,告诉他,他不得好死。
对方笑了,说一定带到,不过,五万块明天汇不到账上,那些照片,我们就卖给你老公啦,他一定会出高价的。
手机“啪”一声关了,房内沉静如水。她坐在那儿,如水中一朵百合,不过,无精打采,有点凋谢的样子。
坐了一会儿,她浑身乏力地站起来,拿了折子走向银行。她必须这样做,她清楚,不这样做,将意味着怎样。她不愿回乡下,再也不愿回到山里,她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城里女人。
她不愿舍弃这个家。她更不愿意离开自己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老公。
拿起存折时,她心中有些疼痛,她又看到,张舟的眼睛透过厚厚的眼镜望着她。文字不值钱,他白天黑夜地爬格子,如一个无期徒刑的刑徒,这五万块钱,得他爬多少天格子?
她眼圈有些红。
到了银行,转了帐,回到家里,在手机中,她把周天这个名字狠狠地删掉,如同拿着手术刀,狠狠剜去心灵上的一个毒疮,连着肉带着血。她决定,从今天起,她要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像张舟文章中刻画的女子,一身素色旗袍,陪着他,一直到老,不离不弃。
她进了卧室,又一次找到那袭旗袍,还有那双高跟鞋,悄悄穿上。镜子中,是一个典雅的闺中少妇。张舟说过,她有一种古典味,像唐诗宋词中走出来的女人。她站在镜子前,向镜中的人笑着,只笑了一下,眉睫上就涌出一朵泪花来,沿着睫毛落下,清风雨露一般。
她擦了一下眼睛,想想,又铰了一朵百合花插在头上:白旗袍,白色高跟鞋,再加上白嫩的脸儿,雪人一样。
她笑了一下,打开手机,拨了张舟的电话。
张舟笑了,问,咋了,想老公了?
她说,咋的,不行啊?
他说,半个月后回来,让你吃个饱。
她又笑了一下,很媚的笑,说,我把你买的旗袍穿上了,很好看,回来时,我穿着让你看。那边张舟惊喜地说,真的?
她说,真的!
张舟夸张地说,我的心都飞回来了。
她笑笑,吻了一下他,这是在手机中第一次这样做。然后,她关了手机,心里略微轻松了一点,好像压着的一座山,被铲除了一点。她慢慢找来抹布,抹起茶几,然后是窗子,然后是书房。她想,他回来时,自己要做他最喜欢的糖醋鱼,吃罢饭,她会穿上旗袍、高跟鞋,对,再插一支百合,从房内袅袅走出,对着他一笑。她要把那天在“香居阁”405室内开放在周天身上的艳丽,全部开放给张舟,像一句歌词中说的,让他领略她的美,领略她的媚。
然后,她向他坦露自己的错误,请求他原谅。
他一定会原諒自己的,她想。
4
张舟是半月后回来的。她已经等不及了,穿着旗袍,还有高跟鞋,去车站接他。张舟望也没望她一眼,提着箱子向家走去。后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潘小杨。
她也是去开笔会的。
张舟送走潘小杨,然后拦了辆出租,他们俩一块儿上了车。张舟的脸很沉,冰一样。她把头靠在他肩上,他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让她坐直。她坐直,很不解地问,张舟,你怎么啦?
张舟眼睛望着前方,过了一会儿道,回家再说,好吗?
她心里有些不安,问,是不是你和潘……
张舟回头,瞪了她一眼,再一次说道,回家说好吗?
她不说话了,默默地坐着,心中很冷很冷,以至于忍不住打了个冷噤。车窗外,天阴沉下来,蝉声叫得更急了,车内异常闷热:看样子,要下暴雨了。回到家,她还没张嘴问,他已经“啪”的一声,扔出一叠照片。照片上,她和周天在床上撕扭着亢奋之极。她身子晃了晃,扶着沙发问,哪儿来的?
前两天,有几个人找到我,出卖这叠照片,我用四万元买下的。张舟望着她,眼睛喷火。她默默地坐下,反而没有了泪。她知道,她该走了,怎么来的,还得怎么离开这儿。
外面,响起了炸雷声,接着,豆粒儿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窗外,灰蒙蒙一片。她的眼前也灰蒙蒙一片。
她抬起头,抹了一把眼睛,把房内四处望了望,心里酸酸地想,如果没这事该多好啊。甚至,她想,要是不进城,在乡下守着那片茶园,该是多好啊。
可是,一切都发生了,再也拉回不到从前了。
她走的那天,张舟来送,还有潘小杨。潘小杨穿着一袭素色旗袍,荡漾如水,脚上蹬着一双白色高跟鞋。
她这才发现,这个女人穿上这些,竟然很美,很典雅。一时,她迷糊了,不知是潘小杨本来就典雅,还是一袭旗袍让她变得典雅。
她对潘小杨点点头,想笑,可两行泪却流了出来。
张舟没说话,递给她一张车票,长叹一声道,走吧走吧!然后,转过身。转身时,也有泪从眼角滑出。
她穿着张舟送的旗袍,向远处走去。她想,他不是一直想看自己穿旗袍的样子吗?就让他再最后看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