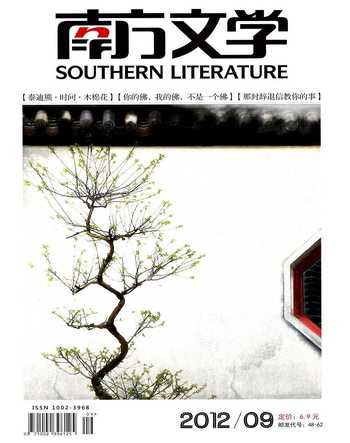被遗弃的人
肖涵
我悲哀地成了众人眼里的“恐怖拉里”,被所有人唾弃。
警官塞拉斯
我叫塞拉斯,但人们习惯叫我“32”或“警察”。“32”是我的棒球球衣号,“警察”则是我的职业。作为密西西比州夏博镇的执法者,我管辖着大约五百居民。
最近夏博镇颇不安宁。木材厂老板卢瑟福先生读大学三年级的女儿蒂娜失踪八天了,现在全州的警察都在寻找这个女孩;今天,我又在一个森林农场的沼泽地发现了莫顿的尸体。我没想到莫顿这小子会落到这步田地。高中时代,我是棒球队的三垒手,他是二垒手。此人既聪明又谨慎,从不吸毒,所以警察明知道他贩卖大麻,也因为找不到证据而无法起诉他。现在他居然死在这荒郊野外。
虽然我是夏博镇的警察,但我只处理一般性暴力事件,并附带指挥镇上的交通,稍微严重些的情况,我都要向我的上级法兰西汇报。此时,快六十岁的法兰西穿着防水长靴,像个渔夫,艰难却毫不犹豫地蹚进沼泽地,给被秃鹰和鲶鱼蚕食得支离破碎的莫顿拍照。
把残尸交给随后赶到的救护队和验尸官,法兰西跟我回到我的办公室。
“那天有人到诺曼?贝茨来找我。”法兰西点了根烟说。
“哦?”
“那人说,拉里?奥特说不定与蒂娜的失踪有关。”
“拉里?”
“这家伙总是跟失踪人口扯上关系,特别是失踪女孩,所以洗不清嫌疑。”
我明白他指什么。二十五年前,一个叫辛迪的女孩跟拉里约会后下落不明,因为找不到辛迪的尸体,他也没认罪,所以无法指控他就是凶手,但全夏博镇甚至整个密西西比州的居民都认为是他奸杀了辛迪。
“你认识这家伙?”法兰西问。
“我们是同学。”说这话时,我想我的脸色肯定不对劲。
“我今早去找过他,他没开店门。”
拉里在镇上有一家修车铺,是他父亲留给他的。虽然生意冷清,但他每天都准时开、关门,中午都不休息。这我了解。
我决定去找找他,虽然我一直回避见他。
修车铺果然没人。
拉里去哪了?也许他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宅在家里看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或者,干脆打算放弃这衰败的生意。但我心里隐隐泛着不安。
这时,我接到了救护队员安吉也就是我女朋友打来的电话。
“32?”
“嗯?”
夏博镇的电话信号总是不稳定。“32,”她说,“我们在拉里家。我的天啦,拉里他……”
怪人拉里
我以为我死定了。
那天我一回到家,就看到了桌上放着一个敞开的鞋盒,那是我装魔鬼面具的盒子。我倒抽一凉气,一回头,就看到了那张“魔鬼”的脸。这面具是我小时候的玩具,我把它藏得很好,这人是怎么找到的?
“大家都知道你做的事。”那“魔鬼”举着枪高声地对我说。
他说的应该是前些天蒂娜被绑架以及二十五年前辛迪失踪的事。但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我做的。
但那人没给我机会说明,将枪抵住了我的胸口。他的手抖动着,眼神中有某种我熟悉的东西。“去死吧!”他低声嘶吼。
死就死吧,我想。反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人误解、遗弃,活得像只孤独的老鼠。
枪响了,失去知觉前,我闻到空气里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
想不到我却在医院醒来。
“你能活下来是个奇迹。要不是塞拉斯警官及时叫救护车,哪怕只晚半小时,你就没命了。”看我睁开眼,医生对我说。
“塞拉斯?”
“就是32,他救了你的命。”我这才发现病房里还站着法兰西。
“现在我们该谈谈。”法兰西拿出录音机,摆开审问的架势。“蒂娜在你昏迷的第二天找到了。她被人奸杀在你家的小木屋里。”
“什么?不……”我欲挣扎着坐起来,一用力,胸口巨痛,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天已黑了,病房里空无一人。塞拉斯。我突然想起这个人,我少年时的朋友。自从他从牛津回来后,我给他家的电话留了几次言,也曾在修车铺等他出现,但他从不理睬。难道就因为二十多年前那次打架时,我骂他黑鬼,他耿耿于怀到如今?
认识塞拉斯那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1979年3月的清晨,周一,父亲开着他的福特皮卡送我去上学。我读八年级。
天极冷。在一个弯道处,站着一个瘦高的黑人妇女和她的儿子。那男孩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他们穿着单薄,冷得瑟缩发抖。看到我们的车过来,他们都往我们车里张望。父亲并没有停车。
“爸爸,载他们一程吧。”我叫他。
他马上刹了车,将车倒回,打开门让他们上来。
“爱丽丝,”父亲说,“给他们介绍一下。”
父亲居然知道这个黑人妇女的名字。
“拉里,这是塞拉斯。”听妇女的口气,好像早就认识我。
我没想太多,向塞拉斯伸出手。
从那天起,每天上学,这母子俩总在同一个地方等候我们。
这事后来我无意中跟妈妈说了。妈妈显得很惊讶,第二天执意要送我去上学。见到妈妈时,塞拉斯的母亲瞪大双眼,神色惶恐。
“嘿,爱丽丝。”妈妈取过带着的两件大衣,摇下车窗递给她,“这些给你们穿应该很合身。你从不介意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是吧?”然后她踩了油门,把这对母子留在寒风中。
“以后不要跟这个黑人孩子一起玩。”妈妈的眼里发出冷酷的光。
可后来我们还是趁大人们不注意,在我家的林子里捉蜥蜴,抓无毒的蛇,爬树,扮牛仔和印利安人。我还借了我家的点22手枪给塞拉斯打火鸡。他和他母亲住在我家林子深处的小木屋里,我估计这是父亲安排的。
“我妈也不让我与你这个白人孩子玩。”塞拉斯有一天跟我说。
大人们真奇怪。我妈分明在每晚临睡前都为我祈祷:“主啊,请您发发慈悲,为我的拉里找一个特别的朋友,让他不再孤单。”她知道我因为生性木讷在学校不受欢迎,可我真有朋友时,她又反对。
我和塞拉斯的友谊偷偷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因为我要讨回我的点22,他不给,我们狠狠地打了一架而告终。
这不是最惨的,真正让我的人生陷入黑暗的,是后来我与辛迪的约会。
辛迪跟她妈妈和继父住在我家附近。我一直暗恋漂亮的她。一天,我路过她家时,她居然主动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周末要约我去汽车电影房看电影。我的心快跳出来,立刻答应。为了引起同学们的羡慕和注意,我还跟他们炫耀了此事。
周六晚上,我如约开车去接辛迪。路上,辛迪突然可怜巴巴地求我把车开去另一个地方,说她男朋友在等她。她说她怀了男友的孩子,要跟他商量对策,而她的继父一直想占她便宜,不许她交男朋友。
这事真滑稽。
“你老实得像个傻子,我继父对你没有防范,所以……”她哭着说。
我的心软了。按她的要求,送她到她与男朋友约会的小树林,然后独自去看电影,完了再转道过来接她回去。
然而,那晚我却没能接到她。她人间蒸发了。
大家都知道我当晚跟她有约会。我悲哀地成了众人眼里的“恐怖拉里”,被所有人唾弃。
塞拉斯的秘密
我最近老做噩梦,梦到拉里。一大早,法兰西来电话说,拉里已经恢复得不错,得抓紧时间审问他,早点把这几件案子了结。
我知道,大家都以为拉里是畏罪自杀。“莫顿的死,蒂娜的失踪,都与这个危险分子脱不了干系。”他们说他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枪,因为压力过大。
“我总觉得拉里没有杀人。我们不是没有证据吗,一切都是推理。”我提醒法兰西。
“总有办法让他承认。”法兰西显得胸有成竹。
这个我信。听说法兰西有让木桩开口说话的本事。
我很焦虑,那些尘封的往事在我的心里上蹿下跳,从十八岁开始,我压制了它们二十五年,眼看现在压制不住了。这么多年来,每次假期从牛津回来,我都借着拉里骂我黑鬼的名义刻意回避他,现在,我得面对。
前些天我去了拉里的家,在阁楼里翻到一些他小时候的照片,在那堆相片里,我惊奇地看到我的母亲抱着小拉里。
联想起我和母亲辗转的人生,以及和拉里一家的过往,我猛然醒悟。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我母亲以前是拉里家的女佣。男主人与女佣发生了某些故事,然后有了我……老天,拉里是我的白人兄弟!
从他家出来时,我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支吸剩的大麻烟和许多四轮车的轮印。拉里从不吸大麻,也没有四轮车。我决定沿着这些线索好好查查。
是的,我必须为我的兄弟做点什么。
下午我去了医院。法兰西和治安官正在审问拉里。
“说实话吧,拉里。不然你的悔恨和内疚不会消失。”法兰西说。
“当年,我只是送辛迪去约会,然后去接她,但没接到。就是这样。”
“这话你说了很多遍。”
“不是他干的。”我插嘴。
“32,出去。”法兰西瞪我一眼。
“辛迪失踪的那天,去见的人是我。我是她男朋友。”我吸了口气说。
他们都惊讶地望着我,特别是拉里。
“那天,拉里送辛迪来小树林,辛迪哭着要跟我私奔。我有很好的棒球前途,怎么可以放弃,所以我拒绝了她。她很生气,独自跑了。”
病房里静得只听到拉里身旁的体征监视器的声音。
“她怀孕了,你这样对她?”拉里叫。
“她没有,骗你帮她而已。”我低着头说,“让你背着沉重的黑锅坐了二十五年的心牢,我很抱歉。”
辛娜在失控跑回家时,或许被她继父发现,然后他杀了她。谁知道呢。总之,这些年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事是真的?”法兰西问。
“是,我以人格保证。”
“真够曲折的——”法兰西摸摸自己的胡子说,“32,回警局再跟我把这故事重头到尾说一遍。”
拉里的朋友
我没想到塞拉斯竟然是辛迪当年的男朋友。他当年就是为这事远离夏博镇,在牛津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的吧?懦夫!
我为之掏心掏肺的朋友就是这样对我的。我苦笑,眼泪流了出来,想到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华莱士。
是怎么认识华莱士的?我想想——好像是他自动找上门的。
那天我坐在家门口看书,一个瘦小的男人开着四轮车过来,向我推销电视接收器,后来我们聊了起来。
“我小时就认识你,大家都叫你恐怖拉里。但我很崇拜你,常偷偷去你家的小木屋玩。嘿,强奸并杀害一个女孩很过瘾吧?”华莱士喝着啤酒抽着大麻用神往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做过。”他的神色让我有点反感,但这家伙很善谈,我太寂寞了,需要有人跟我聊天。
华莱士后来常来我家做客,并送我一支旧的点22左轮手枪,还说要送我一条凶恶的看门狗。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他常当着我的面吸大麻,说一些关于绑架强奸的话题。
虽然他对我建议他在我的修车铺学点手艺这事嗤之以鼻,但我仍当他是朋友。“万能的主啊,请带给我一些生意,并帮助华莱士走上正途。”每晚入睡前,我都要为我俩做祷告,也不知主听到没有……
等等,我想起了一些事!那天朝我开枪的人的眼神和声音……还有,蒂娜失踪后的某天半夜,华莱士来找我,说他做了些事,但到底做了什么,他只顾着喝酒,也没明说。
嗯,或许,明天我得主动找法兰西聊聊。
第二天一整天,法兰西都没过来。我问在我病房外值班的警察,他说大家都在忙32的事。
“塞拉斯怎么了?”
“他去找一个叫华莱士的人,被他放狗咬伤了。很严重。”
我让他打开对讲机,我有话对法兰西说。
“开枪打伤我的人是华莱士,蒂娜也是他杀的。”
“你怎么知道?”
我说了我的怀疑。法兰西在那边匆匆地说,“谢谢你提供信息,我得挂了。”
我想不到塞拉斯会跟我住进同一个病房。
“拉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华莱士在被警察追击时开枪自杀了。莫顿也是他杀的。”塞拉斯一进来就兴奋地说。
我呆呆地听着,说不上是悲是喜。那些屈辱的过往在此时纷至沓来,堵在我逐渐康复的胸腔,让我的语言找不到出口。好吧,那就保持沉默。
但这个黑黑的家伙谈兴正浓,丝毫不在意他身上那些补丁似的伤口,他呲着亮白的牙说:“拉里,前些天我一直在帮你喂那些母鸡,它们下了许多蛋,我都替你收好了。还有,我的女朋友安吉把你家收拾得整洁而温馨,你出院回家就可以看到。”
我微笑着扭头看向窗外,如墨的星空广袤而深邃。阴霾都已过去,明天应该是个大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