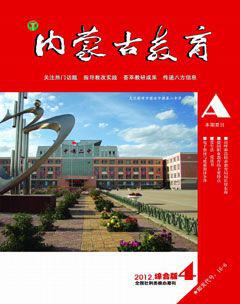古典的魅力
王丛
余秋雨《绑匪的纸条》中指出:“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因为简缩的文字“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所以,能写出简约的文字,一定是长期读古文,甚至能写文言文、旧体诗的人。
而这涉及到语文教育中的文、白之争——文言与白话的优劣之争。
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主要表现在教材上——是文言教材好,还是白话教材好?
教师、教材和学生是教育的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材是知识的载体,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教育就可以进行。作为知识的载体,教材决定了学生学习什么知识,甚至,决定学生做什么样的人。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教材的作用大矣哉。
语文教材又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单承载着知识,还承载着文化,承载着前人的思想情感;它不但以知识丰富人,还以文化熏陶人,以思想教育人,以情感感染人。但这些还并不是语文教材的本质作用,语文教材的本质作用是供学生借鉴模仿,是训练学生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的范本,使学生了解、掌握思想情感是怎样用语言表达的,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出来,相当于理科教材中的例题。
这样,语文教材的重要性就表现在——拿什么做课文让学生借鉴模仿,决定学生写什么文章。古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俗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芝麻出不来谷子”。要写出简缩的文字,即简约隽永的文章,就得让学生“长期读古文”甚至要“写旧体诗”,那么,语文教材就应该以文言文(含古典诗词,下同)为主。
我国古代教材都是文言文。
传统语文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为十五岁之前,约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亦即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目标是識字写字,输入信息,积累语汇,丰富思想。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蒙学读物及《四书》《五经》的正文。“大学”为十五岁之后,约等于现在的高中、大学阶段。这个阶段才略等于现在以学文章为主的语文教学,开始深入攻读典籍,要结合注疏继续学习《四书》《五经》,要读《左传》《国语》《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读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读《古文观止》之类的文选型教材以及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学生读书:“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引文依次出《论语》《幼学琼林》《易经》《尚书》)清代文人郭臣尧《村学》诗写私塾学生读书:“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千字文完翻《鉴略》(一种历史蒙学教材),百家姓毕理《神童》(《神童诗》)。就中有个超群者,一目三行读《大》《中》(《大学》《中庸》)。”这都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旧时蒙学教材的使用情况。
文言的教材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浓缩性。一是文字简约:“融四岁,能让梨”,六个字一个故事;“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八个字两个人物。二是篇幅简短:《三字经》一千一百四十五字,《千字文》顾名思义就是一千字,一本教材只相当于现在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论语》不足九千字,《孟子》不足一万五千字,一本书只相当于一篇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文言教材都便于诵读识记。
它有丰富性。因为信息高度浓缩,教材的内容就空前丰富。如《三字经》《千字文》都融汇了各方面知识,《幼学琼林》分门别类,更是相当于一部微型的百科全书。
文言教材就这样有效地利用了机械记忆力的黄金时期,集中地、密集地为儿童输入了大量信息,为以后的阅读写作乃至做人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它有人文性。《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涉及到人性的善恶,这是社会科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千字文》开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涉及到宇宙的产生,这是自然科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今古贤文》荟萃了大量为人处世的格言谚语,《四书》《五经》则更是封建社会中政治伦理思想道德的总纲。学生描红的字都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这样一些承载一定文化信息的字样。
它有典范性。不论是《四书》《五经》和《左传》《国语》,还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教材中所选诗文都是淘沙拣金遴选出来的千年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艺术的精华。
传统教育中儿童学习的教材,是现在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甚至是专家学者们学习研究的东西,这也使得文言教材大都具有背诵的价值。以这样的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内容,借鉴模仿的对象,发而为文,自然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就能具备简约的语言特点。
文言文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它不够通俗,理解运用都有一定难度,不易普及。
于是,到了晚清,人们把国家贫弱的账记到文言文的头上,以为是文言文屏蔽了民智所致。如陈子褒就认为,要改革就要“开民智,而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陈子褒教育遗议》)五四时期胡适则说:“文字的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人为最成功。”所以,主张弃文言而用白话,说文言是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明确提出“言文一致”的口号。
所谓“言文一致”,就是书面语言不再用文言,也用白话,以与口头语言一致。
如前所述,语文教材是学生模仿借鉴的对象,既然书面语言已改为与口语一致的白话了,教材当然也应该采用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先后发出训令通告,全国小学一至四年级国文教材改为语体文,“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1923年,中学语文教材开始语体文言混编,而以语体文为主,这与现在的语文教材已非常类似了。至此,文白之争以白话对文言的完胜而告终。
但上帝在给人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关上了另一扇门。人们在享受了白话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便利的同时,也痛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相对于文言教材的浓缩,白话教材是稀释的。白话教材没有集中、密集地输入信息的阶段,短暂的集中识字后就是文选型教材。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三字经》中是六个字,在白话的语文教材中就要稀释成几百字。浓度与味道是成正比的,浓度愈低,味道愈淡。当一种语言把承载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明确地表达出来后,这种语言本身就像嚼干的蔗渣,没有什么味道了。简约的特点既然丧失殆尽,隽永的效果也就荡然无存。
相对于文言教材的丰富,白话教材是贫乏的。课文变长了,课本变厚了,但信息的稀释却导致了信息量的减少,学生一学期一册书三四十篇课文,不过是三四十个信息而已。而课文变长又不利于学生的诵读记忆。
白话教材信息量太少,使得学生不能在机械记忆力的黄金时期摄入足够的信息。输入是输出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输入,何来输出?学生语文素质低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相对于文言教材人文性的厚重,白话教材的人文性是单薄的。课文往往过分迁就儿童的特点,太过直白。同是入学之初的识字写字,初期的白话教材是“大狗叫,小狗跳”;现在颇受热捧的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是“早上起来”、“上学去”,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现在的人教课标版是“口耳目”,而《三字经》却是“人之初,性本善”,这能够相提并论吗?
在典范性上,白话教材更无法与文言教材抗衡。白话之与文言,恰似暴发户之与世家。暴发户纵衣着光鲜,言谈总脱不了伧俗气;世家纵衣衫褴褛,举止总透着一份雍容与华贵。文言教材凝聚的是千年的精华,而现代的白话乳臭未干,且受先哲矫枉过正及欧化的影响而发育不良,用这样的白话作品作教材怎能具有典范性?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即使是他那些广为传颂的,被奉为经典的而收入教材的作品,如《荷塘月色》《背影》《绿》……在余光中看来,也“流于浅白、累赘”,遑论其他?语文教材中的不少篇章是编者自己编写的,像《开明国语课本》,就是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手书并配画,都是大家手笔,按说是很精良的,但我们举第十五课:“月亮出来了,天上也明亮,地上也明亮,像白天一样。”也是一首诗吧?但比之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恐怕也不能同等看待吧?
伍立杨在《文字灵幻》中说:“文字的灵幻和魔力绝大部分来自文言……白话文历史短,积累薄,浅水而能负大舟?未之闻也。”缺乏人文性、典范性的白話教材,自然也就缺少识记背诵的价值,不够借鉴模仿的资格。
可以说,语文教育质量不高,白话教材难辞其咎。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语文教材未能有效承载传统文化,不知不觉中,隔断了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古今变成了中外——文言变成了外语(今人对文言的熟悉程度与外语近似,甚至不如外语),古代文献变成了外国文献,今人要靠译文一鳞半爪地去隔靴搔痒。
范善祥在《教学国语的先决问题》中,历数了当时反对国语即白话进入教材的几种人,其中,保守派最有代表性。这派人“对于国语两字,绝端不赞同,以为国语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倘然国语教育普行于社会,那国文即无形消灭,势必亡国灭种而后已”。说国语毫无价值,国语教育会使国文消灭,亡国灭种,这当然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剔除过激的成分,我们发现,当时人们的担忧在今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至少,对大多数当代中国人而言,传统文化已形同陌路。
文言文在理解和运用上确有一定难度,但文言之难真的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吗?也不是。
就理解而言,张中行先生曾说:“我不同意学文言比学外语还难的说法,因为文言和现代语都是汉语,只是有祖孙的不同。祖和孙是两个人,但是有血缘关系,直截了当地说,是两种语的词汇语法系统有血肉联系。中语和外语就没有这种联系。以我的一点经验为证,我第一次读《聊斋志异》是在小学中年级,开卷第一篇《考城隍》,字我认识,意思我懂,因为这同‘考学生是一个类型。到高中阶段,已经学了三四年英文,碰到原本《双城记》,翻开试试,不成,这是因为两种语言没有血缘关系。还可以举个旁证,清朝有一位女作家,忘记名字了,据说是对着弹词听人唱识了字,然后广泛涉览,就通了。”
就运用而言,我国古代学生作文都是文言文。上个世纪20年代,白话进入教材,但学生写作文仍是文言白话并行。1925年出版的胡怀琛著的《作文研究》,第八章《文言与白话》就专门讲怎样处理文言与白话作文的关系。到上个世纪30年代,小学初中不再要求写文言文,但高中还要求写文言文,1936年修正颁行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第二条就是“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新中国成立后,文言作文才彻底废止了。
那么,学生的文言作文成绩如何呢?据《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介绍:“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也取得一定的实绩。学生写作的文章虽然还都是文言文,但有些还是言之有物,值得一读的。”
2011年3月3日出版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民国时期小学生的文言作文,共8篇,篇篇精彩,可为佐证。如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卢焯坡的《春郊游记》:“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今人评:“文字如此优雅,描写如此生动,对偶恰到好处。”
即使是小学生的日记,也都可圈可点,如下面这篇刘振芳的日记:“吾自校归,见一儿大哭不已,或曰:受数儿侮辱故也。余叹,中国犹此儿也,英法德美诸国犹彼数童也。虽然,儿童受侮,尚可申诉于己之父母,以责数儿之非。今中国受侮与英法诸国,将申诉于谁哉?无以,只有申诉于我少年。我少年安敢不勉。”(《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由小儿受侮类比联想到国家受侮联想到自身的责任,可谓小中见大,词意畅达,语气充沛,识见高远。日记如此,作文可想而知。
若文言文都能写得,写简约一点的白话文还不是如拾草芥?而且 “……学生要学写的是近代文言(也可以叫做普通文言或应用文言),不是古文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这与我们提倡的简约的文字已经十分接近。而由浅近的文言到简约的白话,似乎应该是写作在语言训练方面跋涉的旅程。胡怀琛在《作文研究》中说:“我的理想是要将文言渐渐地变为一种极浅近的文言,几乎和白话相似。一方面将白话提高(所谓提高就是省去冗繁之字,归于简便),使文言白话并为一物,那时候,文言白话的名词便可以取消了。”
而在语文教育的实践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白话教材的弊端,敢于逆历史潮流而上,弃白话而就文言,且结果并不像倡白话者所推论得那么坏。
陕西师大霍松林教授幼时,父亲送他上小学,走近学校时,听到学生读“大狗叫,小狗跳”,霍父大为反感:“童年记忆力强,应该读一些正经书,大好时光却教什么‘大狗叫,小狗跳,顶什么用?”(《教师报》1998年1月4日)于是不准儿子进小学,在家里亲自教他读书,这个书当然是文言教材,从《三》《百》《千》到《四书》《五经》了。我们不能说若霍松林读白话教材一定会失败,但霍先生既已成为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知名专家,就可以肯定他读文言教材是成功的。他行文并未刻意简约,但学养所在,偶一为之,也是随心所欲,若烹小鲜。如他论李商隐的无题诗,“或纯赋艳情,或兼寓人生感受,缠绵委婉,象征暗示,迷离惝怳,疑真疑梦,在我国诗史上首创朦胧诗范例。”
海外诗词研究名家叶嘉莹女士的父母,也认为童幼时记忆力好,应读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去小学读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故她幼时并未入小学,而是由家里聘家庭教师,教学语文、算术和习字,语文学的是《论语》以及吟咏背诵诗词,这使她在以后的为人治学中受益无穷。她能文言,工诗词,撰写诗学词学论著自然深得简约三昧,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如“其后苏辛二家出而词之意境一变,遂能以词之体式叙写志意,抒发襟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我的诗词道路》)倘她是读“大狗叫,小狗跳”成长的,就绝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慨叹: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话文课本取得了全胜,最终整个小学阶段,国语课本完全替代了国文课本,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总让人有些遗憾。(《文汇报》2011年3月3日)
这一声喟叹道出了古典的魅力所在:纵使失败也不失为英雄,百年之后依然让人临风怀想。
导致语文教育质量低下的原因不单是教材,还有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有什么问题呢?请看下一篇——《传统的挣扎——语文学科的教学方法应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