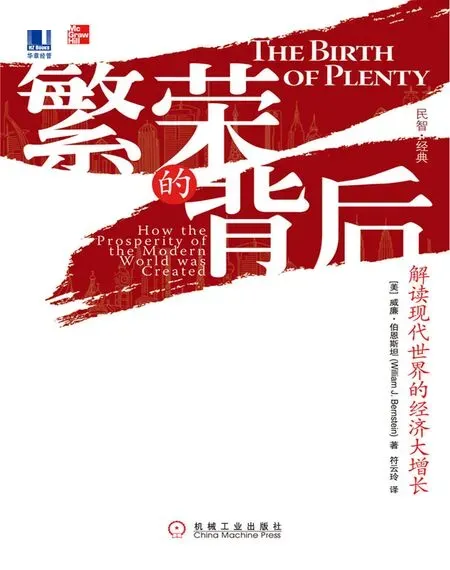“失业”的乡村教师
□本刊记者 张子琦
“失业”的乡村教师
□本刊记者 张子琦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很多农村学校一夕之间被闲置下来,曾经活跃在校园中的孩子们被并入“中心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调整中,作为学校的另一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教师们,他们的命运也随着学校的关闭而跌宕起伏。
“美好的”县城生活
王晓是吉林省梨树县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2001年,她所在的村小学校被列入撤点并校的行列。回想当年得到学校被撤并的消息时,王晓还是五年级的班主任。她说:“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学校说没就没了,难过是一定的,但我还有一个毕业班,能把那些孩子带到毕业是我最大的安慰。”
两年以后,48岁的王晓把这班孩子送上初中的同时,也接到了学校让她内退的通知。“服从组织安排”的王晓从此过上了“享清福”的生活。
根据政策规定,有编制的农村学校教师在学校被撤并后都会被安排到中心学校继续工作,在工资待遇方面也和中心学校的教师相同。在很多同乡的眼里,王晓成了“一朝飞上了高枝”的“城里人”。
提前退休的“城里人”王晓却觉得心里苦涩涩的,“我理解学校的决定,也知道有很多优秀的年轻教师能胜任教师这个岗位,可我是真的舍不得这三尺讲台。”
从“文化人”到“隐形人”
和很多教师相比,王晓无疑是幸运的,她还有机会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事实上,很多农村教师的业务水平与中心校的教师都存在一定差距,撤点并校之后,他们都离开了原本的教学岗位,或成为“校警”,或变成“校工”,或干脆成为中心校的“隐形人”,一年也不上一次班。
王翔就是这样的一位“隐形人”。2003年之前,王翔还是村里颇受尊敬的“文化人”,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王翔来记账,有时写春联也请他来代笔。
2003年,生源的急速减少让王翔所在的中学被并入了梨树县第二中学,曾经的“文化人”成了普通人。王翔不能适应“一切以升学为目标的应试教学模式”,他的“才华”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用他的话来说,“自己变成了没什么用处的人”,“领着工资却没有贡献”成了王翔的一块心病。
刚开始的几年,王翔还时不时到学校看看,监考、修桌椅、保卫处……可无论什么工作,王翔都觉的“差了那么点意思”,渐渐地也就不去了。如今的王翔在江苏张家港市和当医生的妻子在一家私立医院打工,过着“拿着两份工资的幸福生活”。
然而,对于这些 “外来教师”,梨树县中心小学陆海燕老师却颇有微词,“他们的工资水平和我们一样,可是大多数人却不具备合格的业务能力。我们的生源多了,他们却占着编制,年轻的优秀教师上不来,教学压力最后还是落到我们头上。”
被遗忘的“留守者”
李金原是梨树县喇嘛村人,在村小学做了7年的代课教师。“即使不能转成公办教师,在村里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李金原一直安安稳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和王翔一样,他也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还会拉手风琴,这样的人在村里都是有威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时说话比村长管用”。
撤校之前,李金原是“全才”,语文、音乐、体育……课排得满满的,有时还义务修理学校的桌椅板凳,用他妻子的话说是“恨不得睡在学校里”。然而,他的好日子从2001年学校被撤并的那一天结束了。“就像有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那时才明白‘编制’的重要性。”李金原说。
学校没了,学生也没了,老校长觉得有些愧对这个把青春都耗在学校的教书匠,便把学校的手风琴偷偷送给他留作纪念。
“有孩子的时候,手风琴飘出的是音乐;没孩子的时候,手风琴弹的就是噪音了。”丢了工作的李金原不想再种地,外出打工也无一技之长,人到中年,“依靠什么生活”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无所事事了一年之后,李金原发现自从村小消失之后,受影响的并不只是自己,孩子们到县城上学之后,连住宿都成了父母们的难题。
喇嘛村距县城至少需要40分钟的车程,中心校又没有宿舍,父母农闲时可以开着摩托车接送孩子,但农忙时节,对孩子的照管只能依靠寄宿来解决。
寄宿,有亲戚在县城的还好说,但是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仍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寄宿家庭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乡村教师因学校的撤并而前途未卜。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砦仫佬族乡大岩峒村教学点的师生们。
于是李金原倾尽家蓄在梨树县中心小学买了一栋80多平米的房子,开了一个寄宿班。“乡亲们都挺信任我的,最多的时候我这里住过13个孩子。”李金原说,“这样我既解决生计问题,也能为村民们做点事情。孩子们回来之后,我辅导他们功课,有时觉得又回到了从前教书的日子。”
“去年看到那么多地方发生校车事故,我心里特别难受。”李金原表示,并校后学生们去条件更好的县城读书是好事情,“但如果学生不需要奔波,让更多的优秀教师到农村去,不更是改变农村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