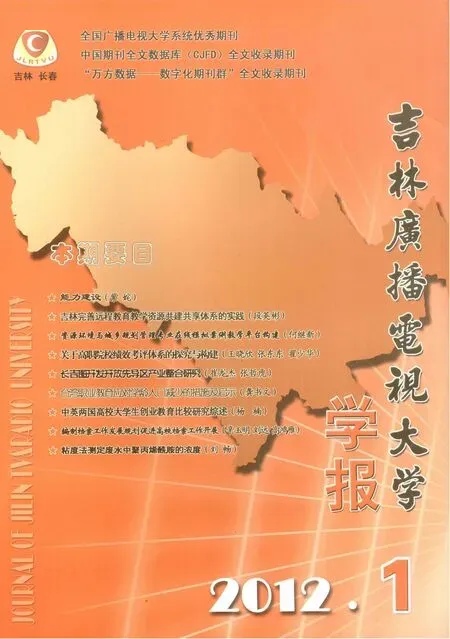逆境中的自我重生
——试析朱玛拜小说《童养媳》中的女性形象
高 莹 范学新
(伊犁师范学院,新疆伊宁 835000)
逆境中的自我重生
——试析朱玛拜小说《童养媳》中的女性形象
高 莹 范学新
(伊犁师范学院,新疆伊宁 835000)
女性的从属地位、话语权力、价值体现等等历来都是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哈萨克族代表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在他的小说《童养媳》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小媳妇在经历不幸命运的同时,依然可以用她的宽容和坚强来化解自身的不幸,从而寻求到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新生道路。
朱玛拜·比拉勒;命运;自我解脱;向心力
朱玛拜·比拉勒 (1941—),新疆额敏人,当代作家。1959年他就读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文化大革命”中辍学参加劳动。1987年至今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国家一级作家。其处女作小说《在黑暗中》发表于1956年。到目前为止,他已公开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深山新貌》 (1980)、《原野小鸟》(1992)、《东方美女》 (2003)、《理想青年》(2004);中篇小说集《岁月》、《父亲的业绩》、《山影朦胧》、《蓝雪》(汉文)以及报告文学集《前辈的眼睛》等。①与此同时,他作品中也描绘出了许多哈萨克妇女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说《童养媳》就是其中一篇。
一、在族规和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女性
张洁在她的小说《方舟》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的确,在男权的世界里,女人的权利很小甚至可以说没有,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朱丽亚·克里斯特瓦在《中国妇女》中所言:女人从男人的身体上分离出来,于是永远地挂念着男人,圣经式的女人是妻子、女儿、或者任何别的东西她很少有名字。她的功能就是确保生殖—人种的繁衍。②“神,总的说来,只对男人说话。没有说出的,是女人不应该知道的。”③可见,男人充当了上帝“发言人”,作为女人只有听从男人的安排才算是服从上帝。在《童养媳》中为我们讲述了在一场瘟疫之后,重病的父亲将自己唯一在这场瘟疫中活下来的十二岁的女儿交给自己朋友照顾,但为了女儿的将来,父亲将“童养媳”这个稳定的身份给予女儿作为了她日后最终的归属。父亲对自己的朋友说道:“我必须给她安排一个稳定的归宿,原谅我,你就拿她当你的童养媳吧。她将来长大成人,你们家就娶她。”④父亲的临终的话语致使小女孩失去了选择幸福的权利。然而,命运的不公让她成为童养媳后饱受来自于女主人的凌辱。在一次男主人和女主人争吵过后,女主人愤然的回到娘家,而男主人也则吵吵将童养媳嫁给他人,但是作为族规的代表比官大人则宣布了多少有些滑稽的判词:“男主人同时属于你们两个女人,但你们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共同拥有一个丈夫,理应有所区别。男主人上半身是神圣的,属于女主人;而他的下半身是污浊的和罪恶的,属于小妾。”⑤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身为童养媳的小妾在旧社会制度下是毫无话语的权利,甚至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她只能听从于“族规”或是听命于代表上帝的男人们安排。然而,在朱玛拜其他关于女性的作品中这种丧失话语权利的女性比比皆是。例如,在《符咒》中,一位年轻的寡妇,在为亡夫守灵一年后,按照族规是要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即使她的内心隐藏着怨恨,但是无能为力的她也只能听从族规的安排。再如,《夜半鸟鸣》中初春深夜的鸟鸣声唤醒了妇人对于自己初恋的记忆,但是家族的干预让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幸福,只有听从家族对于自己命运的安排。所以,无论处在何种文化下,女性曾经并且仍然受着女性处境的限制,她们只能服从于男性所建立的法律、风俗、上帝及其真理和男人的话语,她们的权利受到无情限制和剥夺,女性的定义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她们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所以,正如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所谓的“变成”,即“第二性”的命运不是先天而是后天的,是被社会造成的。这些身处“男性世界”下的女人,她们都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和期待,但是同男权社会制定的“族规”或是男性的话语相比,她们的这些所谓的向往和期待似乎变得渺小,她们力量是薄弱的,她们也无力改变整个家族,所以服从就是她们的唯一出路,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这种服从都是一种无形的压迫后的结果。
二、用内在的善良化解外在的不幸
我们不难看出在清规戒律下的哈萨克妇女们对于自己命运的无权掌握,就好比一只羔羊任人宰割,家族的力量、父母的命令远远胜于她们对于自己幸福的追求。那么面对如此困境的她们又该如何选择?瑞典女权理论家爱伦凯就提出母性之根的观点,她认为,母性之根在于利他主义,母性有这个根,才能消融人类所有的冲突,包括利己和利他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倘若母性得不到充分、健康的发展,那么,将是世界之患。⑥而所谓的“母性之根”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利他主义,通过利他人,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从内心得到自我的解脱并且这种“利他”是一种主动的而非被动。在《童养媳》中,男主人和女主人在争吵过后,依旧比谁都清醒的童养媳在这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官司期间为了能使男主人和女主人和好,她主动与家族里的大妈、嫂嫂们联络感情,并通过一位大婶传达出自己的心声“女主人是一家之主,所以她才会嫉妒我,痛恨我,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思。”“他们自己也知道,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亲手把我托付给了他们,让我作他的人,还为我们做了祷告。我不能违背父亲的心愿,否则就会触怒亡灵,得到报应。事实上,在我最悲惨的时候,是他们收留了我。所以,尽管他的年龄像我父亲一样,我还会把他看做我的丈夫的,我要嫁给男主人。”⑦即使在后来的宣判中,规定男主人的污浊下半身属于她的时候,善良的她还是依旧选择留下来,为男主人生儿育女,当她看到男主人和女主人对她生的孩子如此心爱的时候,她的心也达到了空前的平衡,即使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然而不幸的命运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折磨,土匪们夺去了她丈夫的性命,并且不允许任何人为他收尸。当所有族人都惧怕的时候,身为童养媳的她勇敢地站出来和土匪们进行对峙,要回了丈夫的尸首,维护了丈夫死后的尊严。然而,失去丈夫的她也开始了她整整五十年守寡生活,担负起了家庭所有的负担,即使后来在女主人死后,她也为这个曾经怠慢过她的女人操办了后事,宽恕了女主人曾经的行为,用善良举动赢得了族人们对她的依恋。
或许利他主义从表层来看确实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但是这样的牺牲的背后是内心得到的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安逸,是一种凤凰涅,浴火重生。“利他”不仅仅是对于他人有利,从更深层次讲是一种在无助之下的自我帮助,即不是他人之力的帮助,而是自我力量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童养媳是在用自己内心的善良改变着命运的安排,而她也像一只美丽的蝴蝶重新寻求着幸福的方向。
三、家庭和睦的内在向心力
在解放前,哈萨克族一直存在着所谓“安明格尔”的婚姻习俗,又叫转房婚姻制度或收继婚姻制度,即妇女死了丈夫之后,女方如果要求改嫁的话,一定要优先嫁给亡夫的亲兄弟或叔伯兄弟,甚至长辈或晚辈。只有在本家族无人娶时,才能嫁给本氏族的其他成员。因此哈萨克族有“失去丈夫也不离氏族”的俗语。⑧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习俗是有悖人道的,尤其是剥夺了哈萨克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但是,从积极方面而言,它又体现出了哈萨克民族的内在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哈萨克民族的团结与家庭的和睦。在《童养媳》中,作为小妾的童养媳是不可能选择脱离她本身的轨道,寻求一种新的出路。因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睦”这个概念占据了她整个内心世界,所以,家庭和睦的内在向心力也是她甘愿服从命运安排,即使后来丈夫被杀时也正直她人生最美好的季节,但是为了家庭和睦她选择了整整五十年守寡生活,像男人一样管理者丈夫生前留下不多的牲口,使它们发展壮大。所以,她的存在就是一股无形的凝聚力,是一个无言的召唤,是整个家庭和睦的内在向心力。
注 释:
①赵嘉麟.哈萨克文学简史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378.
②③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 [M].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0,11.
④⑤朱玛拜·比拉勒.蓝雪 [M].叶儿克西·胡尔曼别克,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35,43.
⑥盛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 [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67.
⑦朱玛拜·比拉勒.蓝雪 [M].叶儿克西·胡尔曼别克,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41.
⑧东黎.哈萨克当代文学中的妇女婚恋观 [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哈萨克文化研究版),2011:45.
I207.42
A
1008-7508(2012)01-0078-03
2011-11-02
高莹 (1987~),女,陕西西安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范学新 (1972~),女,新疆阿勒泰人,伊犁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民间歌谣看中国历史上的童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