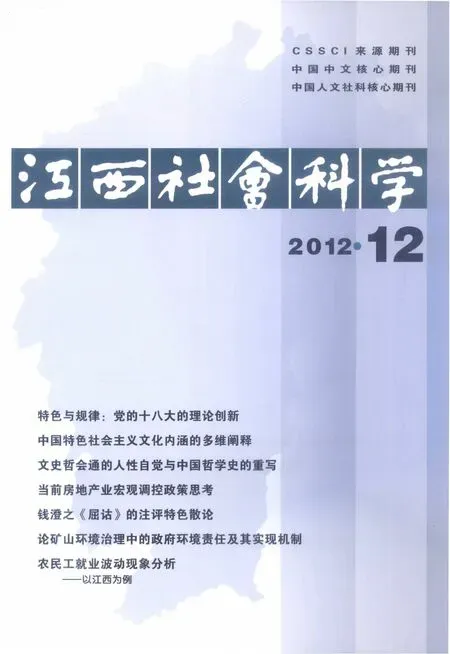海上钻井平台油污的法律适用范围与责任分析
■李天生
目前世界油气总产量的30%以上为通过钻井平台开发的海洋油气。油气新增产量的大部分来自海洋,我国在南海、东海、渤海等海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钻井平台开采作业。与此同时,海洋钻井平台污染事故也日益增多。如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爆炸造成溢油重大事故,2011年6月蓬莱19-3油田B、C钻井平台漏油事故,均造成了巨大的油污损害。而全世界对钻井平台油污问题的立法都不完善,特别是移动式钻井平台的油污责任,由于其介于航海和海洋工程之间的特殊性质,在我国当前的法律适用中令人颇为困惑。
一、中国法律框架下海洋油污责任的法律适用
(一)海洋油污责任的法律适用体系概述
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环境污染损害,特别是海洋油污的国内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中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主要是《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燃油公约》)。其他相关的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是《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防污条例》)以及2011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油污损害司法解释》)。
(二)持久性油类污染和燃油污染责任的法律适用
在中国,船舶油污损害的法律适用特别是相关国际公约如何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般而言,具有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事故应适用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即《油污公约》和《燃油公约》。前者主要规范船舶载运的持久性油类污染,而后者主要规范船舶燃油污染。2011年《船舶油污损害司法解释》第5条对持久性油类污染损害赔偿进行了统一,不再区分涉外和国内,一律适用《油污公约》。对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或者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的油污损害,规定适用《海商法》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同时适用《燃油公约》。
二、中国法律框架下移动式钻井平台的属性与法律适用
(一)船舶与海洋工程的不同法律适用
如果将移动式钻井平台属性认定为船舶,无论其所有人、经营人、作业方等相关主体是否为中国企业,其持久性油类污染责任应适用《油污公约》,燃油污染应适用《海商法》、《燃油公约》。
如果移动式钻井平台不属船舶,而是作为海洋工程所致的油污责任,和其他海洋油污责任一样,主要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污条例》等。
(二)《油污公约》、《燃油公约》的船舶定义与法律适用
《油污公约》对船舶的定义是:“‘船舶’系指为运输散装油类货物而建造或改建的任何类型的海船和海上航行器;但是,能够运输油类和其他货物的船舶,仅在其实际运输散装油类货物时,以及在此种运输之后的任何航行(已证明船上没有此种散装油类运输的残余物者除外)期间,才应视作船舶。”在这一定义下,移动式钻井平台是否属于船舶争议很大,希腊最高法院在the“Slops”[1]案中认为应该属于船舶,但是国际上观点很不一致,如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庭长T.A.Mensah法官[2]认为,依据《油污公约》,海上装置必须“实际运输”和“航行”才属于船舶。在中国,移动式钻井平台是否能被认定为《油污公约》下的船舶,进而是否可适用《油污公约》的问题,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尚不明确,且无指导性的案例。
相对而言,《燃油公约》中对船舶的定义很广,包括任何类型的海船和海上航行器。理论界和国际实践中,均将移动式钻井平台视为《燃油公约》下的船舶。因此,在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燃油污染的情况下,其责任应适用《燃油公约》的规定。
三、中国法律框架下移动式钻井平台三种油污的法律适用
(一)移动式钻井平台油污责任法律适用划分的原理
根据《油污公约》的相关内容,移动式钻井平台是否属于船舶存在争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正确认识移动式钻井的属性和作业特征。移动式钻井平台起源于船舶,与船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如可在海上航行且处于移动状态、部分具有自航能力且处在航行状态、处在被拖带状态等;但又与船舶有着重要的区别,如技术特征显著不同、不能完全自航、以就位开采而不是航行为目的等。事实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兼有航海和海洋工程的性质。对于移动式钻井平台的油污责任,应当依据其造成油污的环节、原因区别看待。凡造成油污的环节、原因属于航海性质的,就应当属于船舶,适用《油污公约》的规定;凡造成油污的环节、原因属于海洋工程性质的,就不应当属于船舶,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污条例》等法律法规。
按照上述原理和思路,结合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的特征,以及油污的类别,我们应将移动式钻井平台油污划分为三种情况,分别适用法律和认定责任归属。
(二)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时发生持久性油类污染的法律适用
移动式钻井平台在进行钻井作业时,处于就位状态,此时虽然不像固定式钻井平台那样永久性构架于海底,但也通过单点系泊或多点系泊等方式与海底稳定连接,这是移动式钻井平台进行海洋油气开采的需要。这种情况下,移动式钻井平台的属性完全与航海无关,属于海洋工程性质。其所致的持久性油类污染,主要是开采过程中发生的溢油污染,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钻井作业时发生持久性油类污染的赔偿责任来说,主要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由作业方承担责任。
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时易发生的主要是持久性油污,但如果发生非持久性油类污染,这将与其他海上油类及非油类海上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样,应适用《侵权责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三)移动式钻井平台海上移动时发生持久性油类污染的法律适用
移动式钻井平台在海上移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升式钻井平台的移动,这种平台不具备推进装置,在海上移动完全依靠拖带;另一种是半潜式钻井平台的移动,这种平台虽有一定的自航能力,但因其结构形成的巨大水流、空气阻力,也需要拖带才能在海上移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都不是独立航行,但属于拖带航行,其性质应该相当于拖航中的被拖船,即具有航海或运输的属性。实际上,若在海上移动时发生持久性油类污染,除燃油外,肯定就是其储存的持久性油类的漏油污染。这与被拖带的油轮的货油污染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此时的移动式钻井平台应被视为《油污公约》下的船舶,海上移动时发生的持久性油类污染应适用《油污公约》,相关责任主要由船东(移动式钻井平台所有人)承担。
同样,移动式钻井平台移动时如果发生非持久性油类污染,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并且,由于此时属于船舶造成污染损害,还应当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有观点认为,鉴于移动式钻井平台是否符合《油污公约》的船舶定义争议很大,所以凡是移动式钻井平台油污,均可以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般法。这种观点从实证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理论上过于简单化,并不可取。
(四)移动式钻井平台燃油污染的法律适用
在《燃油公约》下,移动式钻井平台属于该公约所适用的船舶。所以,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的燃油溢出或排放事故,应适用《燃油公约》的相关规定。《燃油公约》没有专门规定的责任限制和限制基金,而是规定适用《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或者该公约参加国的国内法。根据《船舶油污损害司法解释》规定,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或者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的油污损害,适用我国《海商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即相关责任主要由广义上的船舶所有人 (包括船东和光船承租人)承担。
此时,还需要将《燃油公约》中的移动式钻井平台是否属于油轮进行界定。因为如果属于油轮,则当移动式钻井平台储存、装载持久性燃油时,就应当适用《油污公约》而不是《燃油公约》。特别是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性质和风险与油轮颇为相近。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存在很大争议,澳、英、法等国和国际互保协会都提出各种复杂的探讨观点。本人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应不认定为油轮,因为按照2012年7月1日生效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油轮需要缴纳基金,这点目前显然难以适用于移动式钻井平台。
四、中国法律框架下移动式钻井平台油污的具体法律责任
(一)《海洋环境保护法》机制下的有关责任
根据上文分析,对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时发生的持久性油污和非持久性油污,应按移动式钻井平台的海洋工程属性,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污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法律是《海洋环境保护法》。2011年6月的渤海钻井平台漏油事故中,国家海洋局即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官方认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责任如下:
1.责任主体与免责理由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据此,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时发生的油污责任,赔偿主体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根据目前司法实践,责任者一般而言是作业方。因此,在移动式钻井平台光租业务中,平台所有人将平台光租给另一方,完全由另一方或其他方进行作业操作,若发生油污事故应由作业方承担责任,平台所有人一般不会承担责任。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具有以下免责理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损害的;战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灯塔或助航设备主管部门的疏忽或过失。
2.责任范围与责任限制
关于责任范围,《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非常笼统,即“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而2011年《船舶油污损害司法解释》中的损害赔偿范围比较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被用于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
《船舶油污损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范围包括:为防止或减轻损害采取预防措施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损害;油污造成该船舶之外的财产损害以及收入损失;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合理恢复环境费用。
此外,《海洋环境保护法》还规定了拥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国家海洋局曾草拟赔偿草案,其赔偿范围可能包括:清除污染和减轻损害等预防措施,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造成的次生污染或者损害;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修复受损海洋生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调查研究、制订修复技术方案等合理费用;重建替代有关生态功能的合理费用;监测、评估以及专业咨询、法律服务的合理费用;其他合理费用。
除民事责任外,责任方还可能会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因为,《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责任限制,移动式钻井平台作业时发生的油污不能适用限制赔偿责任。
(二)《油污公约》机制下的有关责任
如上所述,对移动式钻井平台在海上移动时发生持久性油类污染的情况,应按移动式钻井平台的航海属性,适用《油污公约》。如果发生非持久性油类污染,还应适用《侵权责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商法》等。
1.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
《油污公约》对发生油污的船舶船东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油污索赔只能针对注册船东或者系列污染事件中第一个污染船东,而不能针对第三方如光船承租人提起,除非第三方故意或明知污染损害实际发生而仍疏忽作为。另外,受害方也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索赔。
当发生涉及两艘或更多船舶事故并造成污染损害时,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应对所有无法合理区分的损害负连带责任。当然,船东向过错方追偿的权利不受影响。
2.赔偿范围、免责与抗辩事由
《油污公约》的赔偿范围包括:油类从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灭失或损害,但是,赔偿应限于已采取或将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预防措施的费用;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
该公约还规定了大量可以使船东免责的抗辩理由:战争、敌对行为、内战、暴动或特殊的、不可避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完全是因第三人的行为或疏忽、故意造成的损害;完全是由灯塔或助航设施维护部门的疏忽或错误行为;污染损害是受害人有意或疏忽造成的。
3.责任限制及责任限制的丧失
按《油污公约》2000年修正案的规定,对于不超过5000吨位的船舶,限额为4 510 000特别提款权;而对于超过5000吨位的船舶,除上述金额外,对每一额外吨位增加631特别提款权,但任何情况下总额不应超过89 770 000特别提款权。如经证明,污染损害是由船东故意造成或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致,则该船东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
(三)《燃油公约》机制下的有关责任
如上所述,由于《燃油公约》对适用船舶的定义非常宽泛,国际实践中普遍认为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燃油溢出或排放事故,应适用《燃油公约》的相关规定。
1.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
《燃油公约》对造成污染事故的船舶所有人也规定了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并要求造成事故的责任人对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该公约下的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光船承租人、管理人和经营人,故油污索赔可以针对事故发生时船舶的注册船东,也可以针对第三方如光船承租人提起,受害者还可直接向提供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提出索赔。当然,船舶所有人向过错方追偿的权利不受影响。
2.赔偿范围、免责与抗辩事由
造成事故的船舶所有人应对造成当事国的领土、专属经济区,或从其领海基线向外延伸200海里区域的污染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还应对任何防止或减少损害的预防措施,以及因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燃油公约》下船舶所有人的免责与抗辩事项与《油污公约》基本相同。
3.责任限制
《燃油公约》没有规定独立的责任限制制度和专属的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基金,在责任限制问题上规定适用《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或该公约参加国的国内法。我国不是该公约的参加国,根据国内相关主体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海商法》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燃油公约》下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按照“一次事故,一次限额”的原则,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请求与同一事故引起的其他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共同享有同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规定。
[1]Zuzanna Peplowska,What is a ship?The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the effect of the Greek Supreme Court judgment in the Slops case.Aegean Rev Law Sea(2010)1.
[2]T.A.Mensah.Can the SLOPS be considered as a ship for the purpose of the 1992 Civil Liability Convention and the 1992 Fund Convention?Aegean Review of the Law of Sea and Maritime Law(2010)l: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