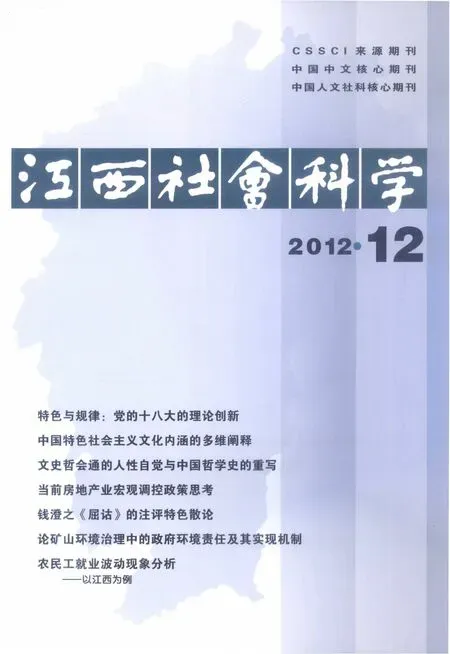从莫言热审视今日中国文化生态
■叶祝弟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内地本土作家。消息传来,一时间举国欢腾,群情激奋,大众、专家、官方、出版社、媒体所催生的莫言热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升腾、膨胀、弥漫。莫言获奖,无疑是21世纪中国文学界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最美的收获”。在这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人们奔走相告、不吝送上最美的祝福:莫言获奖,“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流水平”,“套在中国文学上符咒般的焦虑彻底放下了”,“中国文学第二春马上就要到来”,更有专家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为莫言获奖背书:“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甚至有人又高调重提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由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掀起的莫言热?这股莫言热到底是某些专家所谓的崛起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自发的反应?还是在媒体、官方、大众的借势炒作、推销、挪用、包装下,催生出的文化虚热?为了更好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选取莫言热中专家、媒体和公众对莫言形象的建构为观察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
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选择颁布给莫言,乃是因为莫言以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建构的“独一无二的小世界”中,所表现出的文学价值和世界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已经跻身当今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流作家行列。尽管如此,莫言的影响力也基本局限在由纯文学作家、出版社、小众化的文学消费市场和学院派批评家所构成的文学圈。人们关注莫言,聚焦的是莫言作品本身的价值,评论的是莫言孜孜不倦营构的主观感觉世界、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的暴风骤雨式的文学语言、天马行空式的文学想象和陌生化的文学经验。文学界对莫言获奖寄予厚望,也基本上是在肯定莫言作品“从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奋斗、苦难和悲欢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以奔放而独异的鲜明气韵,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境界”[1]的文学价值前提下所作出的判断。文学界对莫言作品给予批评,也主要是针对莫言作品本身存在的艺术问题而作出的评判。
但是随着莫言获奖,文学界内部的二重奏已经演变成公共领域多声部的大合唱,文学界和思想界组成的专家,读者和网民组成的公众,从中央宣传部门到地方政府所构成的官方,以及各色各样的纸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构成的媒介,共同谱写了这部世纪大合唱的旋律。在这样的一曲众声喧哗的大合唱中想要仔细辨别每一种声音的音质、精确测算每一种声音的分贝,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只能大致辨析以文学批评家为代表的学院批评家的声音,以历史、文化学者为代表的思想界的声音,以及以媒体和公众为主体的大众传媒的声音。
在莫言热的大合唱中,以文学批评家为代表的学院评论家的声音代表了一种相对专业、客观的理性立场。学院批评家的声音相对比较一致,基本是在文学的视野内对莫言获奖的赞誉,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是对莫言作为伟大作家的肯定。莫言所苦心营造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足以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相媲美。莫言上接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学传统,下接以马尔克斯、福克纳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它以其独具个人魅力的瑰丽而丰饶的无边想象、恣意狂洋而极具爆发力的语言、独创性的自由而超越的精神以及大气磅礴而纵横捭阖的文学气象,在文学、人性和艺术的维度上捍卫并“重申了文学的尊严”[2]。
第二,莫言获奖,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整体成绩的肯定。21世纪之初的第一个十年,无论是由丁东、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等思想界人士率先发难所主导的“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对“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3]的指责,还是由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引发的文学评论界内部关于“中国文学处于高峰还是低谷”的激烈争论,均指向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成绩的评判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无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贫乏、现实关怀缺失的批评还是对当代文学审美性、艺术性的肯定,均有一定的理据,但反对派的声音更加高亢一些,反对派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至今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没有得到世界性(实质是西方世界)的肯定。莫言的获奖无疑为迫切需要正名的当代文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就整个当代文学而言,莫言获奖既不会拔高也不会降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但是莫言的获奖,显然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扬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精神的肯定,也有利于刺激中国作家的创作热情,有利于提振中国文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觉,有利于我们客观、中立地评价当代文学。
第三,莫言获奖,是中国“日益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4],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深化认识文学与传统、本土的关系,也为深入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方面,莫言获奖是对文学性的尊重和对政治性的超越,它为人们重新思考百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为文学如何关照世界、立身于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路径。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并不总是那种以短兵相接的方式出现,文学同样可以借助自己独特的文学性、艺术性、想象力直抵人性的深处,发挥文学的“破坏性的超越力量”,承担对现实的批判和介入功能。当代文学应超越政治和社会的附庸,在本土文化语境中接通传统的文脉,在一个文学的自足性和艺术的自主性的文学空间建构中,学会在“在争议中加深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拓宽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加强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力”[4]。另一方面,莫言获奖为中国人重新处理自己与世界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莫言获奖,不仅缓解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而且让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更加正常和开放,“不要那么拧巴,既不要觉得说外国人说我们好,我们就好得不得了,也同样不要认为,外国人说我们是垃圾,我们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垃圾,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与世界文学的正常的对话的姿态、语态”[4],我们应超越过去那种文化自卑和自傲的两极心理,以平和的心态去认识诺贝尔文学奖,去处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关系。
学院批评家对莫言异口同声的赞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那些曾经对莫言作品颇有微词的批评家的声音。诺贝尔文学奖说到底只是一个奖项,其对文学的评判并不能代表历史的评判,也不能左右专业阅读者的口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家不可能取悦于所有人,也不会符合所有的具有苛刻眼光的批评家的口味。因此,在一个正常的文学批评生态下,伴随莫言热的理应既有对莫言作品赞扬,也应有对莫言作品的批评,不会因为莫言的获奖而为尊者讳,而应该形成新一轮的对话与交锋。事实上,在莫言获奖之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围绕着莫言作品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甚至不乏一些尖锐的声音。如被莫言封为“狗鱼批评家”的李建军对莫言《檀香刑》的批评《大象还是甲虫?》,对《蛙》的批评《〈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在一个文本细读的层面上对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其他如郜元宝、邵燕君、黄发有等批评家对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和思想缺失的批评,均有一定道理。莫言的作品固然有大家气象,但是他的作品中的那种泥沙俱下、毫无节制的叙事风格,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很遗憾,这样的“负面”声音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不仅鲜见媒体的报道,也鲜见网络媒体中。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声音真的因为莫言的获奖而消失了吗?如果存在,那么他们理应汇成这次大合唱的高潮部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么淹没在众声喧哗中,要么成为“失声者”。这大概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不过,以不在场的沉默方式表达一种在场,也是一种态度。
二
学院批评家对莫言的肯定,基本上立足于莫言文本本身,秉持的是一个非道德化、去政治化的立场,强调的是对小说家莫言及其作品和价值立场同情式的理解。这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道德的立场,在民间的、人性的视野下,关注莫言作品的审美独立性、艺术自足性。但是,学院批评家的发言,并不是空谷足音,他们更愿意放在一个中国经济、文化崛起的背景下谈论莫言,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超越了对莫言专业作家身份的认定,赋予其为中国文学取得世界性荣誉、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当然,任何对莫言符号化、标签化的理解都可能陷入过度阐释的危险境地,文学批评界的这种理解和认同,并没有获得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思想界人士的认可。2012年10月16日,学者许纪霖在其博客发文《我为什么批评莫言?》,对莫言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批评,认为莫言没有“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没有“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进而指责莫言缺乏信念,存在人格瑕疵。
客观地说,许纪霖的这些宏论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他的这些观点在“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以及文学界的回应中已经被预演过一次,在近年来人们对当代文坛大棒式的几次讨伐中,也曾作为批判武器被反对者们屡试不爽。但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狂欢声中,许纪霖的声音还是比较刺耳。学院批评家长篇累牍所做的文学性的肯定,在许纪霖那里以一句“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就打发了。许纪霖的发言,将莫言文学作品弃之一旁,却将矛头直指莫言的作家身份和人格品质。虽然许纪霖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激烈回应和辩护,也没有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肯定和回应 (许文在新浪博客发表并被置顶后,截止到2012年10月30日22点,共被阅读3084次,评论58条,从跟帖看,反对声和赞同声均有,但是绝大多数对许论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但是许纪霖的评论,却将人们的关注点从莫言的作品,转到人们对莫言作为作家、作协副主席、中共党员等多重身份的关注上来,借用周瓒在《当代文化英雄的出演与降落》中的观点,这实际上再次向人们提出对作家的精神人格结构、作家在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在当代文化、政治中的功能意义等问题的反思。[5](P104)它促使人们反思,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评判是否必然与这个作家的身份乃至人品联系在一起?
显然,相对于文学界的热烈肯定,思想界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无论是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还是耶利内克、帕慕克、赫塔·米勒,他们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除了缘于其作品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立场,更是缘于其对政府和现实持尖锐批判姿态与体制不合作的立场。思想界对莫言的苛求,也正反映了这种期待视野。但是,莫言所承继的中国文学精神,显然无法为思想界解释当下中国复杂的文化社会现实提供理论和精神的资源,更无法为思想界提供一个道德和政治的标杆,莫言本人也表示其无意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此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也正是要打破以往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无关政治身份、思想立场和道德境界,纯粹是对莫言文学成就的肯定。
在现实中做一个高调的反对者和批判者,在文学中表达自己鲜明的价值立场,对现实社会的丑和恶提出强烈的批判,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固然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尊重,但是对作家个人而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况且这种选择也并不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形象,中国人提倡的是士大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提倡的是温和的合作、隐忍精神。既不谄媚于权贵,也不横眉于体制,莫言在其作品中自觉选择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立场,远离知识分子立场,以一个更为高超的技巧张扬历史的正义和揭示人性普遍的困境。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力图在不同角色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抄写《讲话》,以及他在获奖之后的刻意或不刻意的低调、不停的致谢和感恩,正体现了中国儒家式的内隐精神,也体现了骨子里残存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他的这种姿态,既能得到官方、学界、媒体的认同,又能保持自己相对的人格独立,从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今天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对文化英雄的想象和认同。正如学者张旭东所说:“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形象……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写出最好的文学。”[6]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随后学界对陈寅恪、王国维、顾准等文化学者的重新书写和精神“招魂”,以及对王小波、海子等文学英雄的精神加冕,都暗示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恢复知识尊严、社会良知和人文精神的渴望。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学科的分野和思想的分化,特别是消费主义、专业主义、文化犬儒主义的流行,文学不仅与政治的关系渐行渐远,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联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而且作家也似乎失去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关注,几乎在许多重大的社会思潮和论争中,文学家的声音均处于失语的状态。这种强烈的反差,导致了思想界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也是导致学界对莫言评价的分歧所在。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应该回到它的本位,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文学性,而不是对现实的抨击和批判。祈望一个作家既是文学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太可能了。更何况在一个理性化、专业化的时代,文学经世经国的理想,已经让位于社会科学治国的现实。[7]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实面前,文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会像其他学科一样,直接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能够面对的只能是此在世界的人和人性问题。在一个犬牙交错、专业林立的文化现实面前,让文学承担政治的功能,显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专业作家,那么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文学写作者的莫言,其作品中表现出的艺术风格、叙事格局和文学品质,而作为一个文化英雄,我们可能关注得更多是作品以及作家本人表现出的思想品质、人文精神和独立人格。这大概也是今天的思想界人士和文学界人士对当代文学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的原因。评价结果的差异正是源于评价标准和出发点的差异。
三
对于莫言获奖意义的过度阐释或者无限拔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莫言的关注越来越远离莫言作品本身,罔顾现实,远兜近交,隔空放炮,显然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捧杀和棒杀均会遮蔽我们对今天的文化现实的正确认知。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无疑看中的是莫言作品中的巨大的文学价值,这理应是莫言热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兴奋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奖项,其相对完整、严谨而规范的评选方式,赋予了其很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正是这种权威性,激起人们对获奖作家作品的热读、评论乃至争鸣,但是很奇怪,在这股莫言热中,莫言作品本身的价值如何,虽被少数莫言研究专家所津津乐道,推崇之至,但是却鲜见普通民众和大众媒体的严肃、认真的讨论。这种舍本逐末式的莫言热,到底是实实在在的文学热,还是一场文化虚热?
笔者以为,大众对莫言的态度,真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文化状态和文化困境。与学界的分歧和纷争不同,大众显然并不关注如上略显沉重的话题,也不关注莫言的作品到底“写的什么,写得如何”。相对于文学界专家对莫言专业作家和文化英雄身份的关注,对大众而言,莫言更像是一位天外来客,是莫言获奖前登上博彩公司赔率榜的榜首以及获奖后大众媒体不遗余力地炒作让莫言在公众中“暴得大名”。相对于莫言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人们关注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带来的高额奖金可以折算成多少人民币,可以在北京内环买多大平方米的房子。而文化商人则关注的是莫言获奖的作品印数,关注的是如何吸引那些媚俗和媚雅的人们彻夜排队够买莫言的作品,背回家束之高阁。而更多的商人则窥见其中的商机,教材、服装、烧鸡这些看似不搭边的事物,也搭上顺风车,以莫言命名的“莫言醉”的注册商标就卖了1000万。围绕着莫言,不仅一个出版、发行、流通、消费一体的文学产业生产链正在形成,一个新时代的文化英雄和娱乐明星的形象也正在冉冉升起。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专家的颂扬和鼓噪、出版公司的宣传、产业化和时尚化的运作,一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标签化和偶像化。作家的偶像化是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要环节,[8]在媒体眼里,莫言不仅是新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党员、军人、农民、《红高粱》的编剧、富豪作家、奇人,这些色彩斑驳的象征符号共同构成了莫言新时代的文化英雄的身份标签。二是猎奇化和娱乐化。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莫言的家庭出身、生平逸事、兴趣爱好、求学生活、军旅生涯、巨额稿费和奖金、住房、一夜暴涨百万的手稿以及莫言作品中的情色描写、暴力场景、计划生育主题,均被媒体挪用过来反复渲染,大肆炒作,甚至他的小眼睛,发亮的额头,也被媒体涂上了更多文化和智慧的光芒。莫言在20多年前拍摄红高粱时与张艺谋、姜文等赤裸着上身的合影也被网友翻了出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三是时尚化和产业化。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经纪人精典博维一次性买断其版权,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延请发言人代为处理与媒体沟通事宜。精典博维的这种运作方式,完全遵循的是明星制造和时尚文学的生产方式。在媒体和出版方的狂轰滥炸下,“获奖作家本身的个人魅力、作品特质、人生的理解和艺术的表述均被奖金额度、照片、颁奖晚会、闪光灯、标题等等符号所覆盖,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的诺奖作家,一个被包装为新闻炒作焦点、出版界卖点和评论界热点的新闻人物。”[9]莫言热本身应具有的严肃意义和正典价值被以娱乐化、符号化的方式被置换、取消和消解了。
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如今视同娱乐明星般的趋之若鹜,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困境。人们对莫言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态度,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文学审美趣味,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人文精神萎靡现实的原因。文学应有其自主的位置和自足的空间,文学既不是启蒙救世的工具,也不是消闲娱乐的附庸,任何将莫言符号化、标签化、娱乐化、庸俗化的行为都是对莫言作品的亵渎,也是对文学精神的亵渎。我们对待莫言热最好的态度,不是捧杀和棒杀,而是回到文学本身,在对其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中分享和体悟莫言作品带给我们的沉静的力量。
[1]铁凝.祝贺莫言,祝福中国文学[N].文学报,2012-10-18.
[2]栾梅健.莫言获奖重申了文学的尊严[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07c220101c7q5.ht ml?tj=1.
[3]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J] .南都周刊,2006,(5).
[4]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N].文艺报,2012-11-24.
[5]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6]张旭东.莫言是通向当代中国文学的门户[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0-14.
[7]罗云峰.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迁——兼与陶东风教授商榷[J] .探索与争鸣,2011,(6).
[8]孟繁华,周荣.文化消费时代的新通俗文学——新世纪类型小说的叙事特征与消费逻辑[J].探索与争鸣,2011,(4).
[9]王晓路,等.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四人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