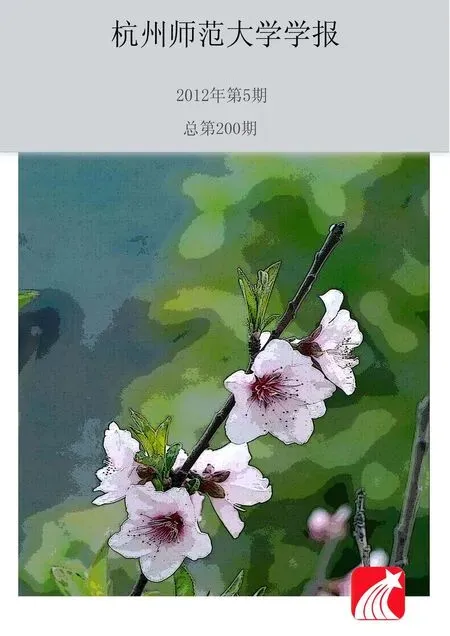汽车与城市:英国和西方汽车化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英]Simon Gunn著,丁雄飞译,张卫良校
(1.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英国莱斯特;2.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200241;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汽车与城市:英国和西方汽车化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英]Simon Gunn1著,丁雄飞2译,张卫良3校
(1.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英国莱斯特;2.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200241;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拥有汽车规模的扩大,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迎来了大众汽车化时代。许多历史学者开始反思这一现象,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全新研究路径:“汽车体制”的概念、大众汽车化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大众汽车所有权的政治,以及汽车对日常生活的深刻改造。
西方;现代史;大众汽车化;汽车体制;城市形态
1960年4月,在英国国会的一场关于道路交通的辩论中,工党议员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发表了一番演说,他的主题是“预想未来”。沃克说:
汽车是能够促进我们国家当下社会变革最有活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我们城市、道路和乡村的面貌……我认为拥有一辆汽车正开始取代拥有一所住房,这体现了人的独立感和自尊感。汽车已然日渐成为人的社会必需品,于是,我们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急剧增长。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精力,根据汽车这一维度来重新建构我们整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①Hansard,HC,vol 621,col 917(11 April 1960).
其他的一些专家并没有那么乐观,他们更担心的是大众汽车化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1961年,英国重要的交通规划师柯林·布坎南(Colin Buchanan)警告伦敦城市规划研究院:“作为机动车影响的一个结果,许多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现在,汽车“正威胁着城市地区的文明化运作”;根据布坎南的说法,汽车正在“产生让那些地方呈现出一派冷漠的面貌的恶劣影响”[1]。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所有评论家一致认为,随着大众拥有汽车时代的到来,这个国家的景观及其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在这方面,英国远不是独一无二的。遍及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些年里,社会学家们所谓的“汽车体制”的东西才嵌入进来。当然,就汽车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们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大众拥有汽车的规模扩展,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才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些年里,英国的汽车数量增长了五倍。[2]1958-1968年间,法国经历了一场消费革命,文化评论家视其重要性堪比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尽管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都是这场消费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就是像雪铁龙德尚(Citroen DS)这样的汽车。[3]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单单在1960-1970年间,日本的汽车和卡车数量就增长了16倍,从而在10年之内创造了一个大众汽车社会。即便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国家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了全国高速公路系统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②Susan Townsend,‘The“miracle”of car ownership in Japan's“Era of High Growth”1955-1973’,Business History,forthcoming 2012.[4]
在20世纪下半叶,汽车体制吞噬了西方社会。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可以阻挡这种趋势。但是,汽车大众化在不同国家产生了相当不同的影响——新建了道路系统,产生了物质方面的影响;政府获得了一个大众汽车社会,并给予回应,产生了政治方面的影响;汽车被作为消费者的驾驶人所专用,产生了文化方面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一部全球范围的关于汽车体制的历史。我们有的仅仅是一些零碎的关于汽车使用的编史。例如,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主要的撰稿者是一些企业史家和经济史家,因此,有一种著名的汽车制造和汽车企业史,例如像尼桑和福特这样的历史;但是,在北美之外关于汽车对城市形态或者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的历史研究却非常罕见。③可以参看大量的相关文献如Steve Tollida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1945-1995,2 vols.(Cheltenham,2001);Hugo Bonin et al.,Ford,1903-2003:the European History,2 vols.(Paris,2003).
尽管如此,由于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汽车对于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影响,也因为我们即将步入亚洲汽车革命这一新阶段,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思考1945年之后那几十年间发生的所谓大众汽车化的“第一次浪潮”。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抛弃那些相对浅显的思考方式,比如仅仅涉及汽车制造和汽车拥有规模的扩张。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就大众汽车化这一历史现象,查考一些更为重要的研究新路径。这些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汽车体制”的概念、大众汽车化对于城市形态的影响、大众汽车拥有权的政治学及其对于改变日常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
一 “汽车体制”
首先,最近有关汽车化的历史研究已经受到了社会学家们所谓“汽车体制”这一术语的影响。[5-6]这意味着,研究汽车化不能将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割裂开来,正是汽车化导致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出现。当大众汽车制造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腾飞的时候,一系列新的现象随之应运而生:各种新的道路系统以应对一个飞速机动化的社会;一个为汽车业供给燃料的石化工业,像壳牌和美孚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便是这一现象的缩影;汽车销售的经销商网络以及维修汽车的修理站;大量小型产业提供一切从汽车配件到道路标志的相关产品。其他的产业,比如广告业,开始大规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车品牌化和偶像化。这种全新工业上层建筑的增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汽车业在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是,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已经确立起来。不同形式的汽车运输业成为一个主要的就业雇主,汽车制造业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纺织、造船这样的传统工业走向衰弱的时期。各国政府设法通过调整消费者的借款利率来管控消费行为,因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是依靠贷款来购买汽车的。同时,汽车产业本身也开始将自身确立为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团体、公路货运公司、汽车销售商团体,等等——这个集团以“公路游说团”(‘road lobby’)著名。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公路游说团”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它们试图对从税费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务施加影响。[7]
因此,我们需要明白,汽车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商品,或者一种交通工具,毋宁说是一种体制——汽车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的集合。城市史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去理解,这种集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很多国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确立起来,但美国要更早一些,在20世纪的30-50年代之间就已经建立。只有意识到汽车深度嵌入社会这一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以下事实:汽车本身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政客们屡次试图限制汽车使用的努力,皆毫无效果;汽车有能力在油价连番上涨之后依然生存下来。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形态一样,如电力、自来水、计算机网络等,汽车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建筑形式、日常经济乃至现代都市社会的消费想象之中。[8]
二 汽车与城市形态
大众汽车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汽车对于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规划建设了各种道路系统,包括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这改变了道路所经之地的景观,也改变了沿途城镇的经济,就像19世纪铁路所发生的作用一样。[9]这些道路系统的作用在交通最集中的城镇和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私人汽车的普及加快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的进程,亦即人们搬离市中心的街区,迁往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社区。正如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Jackson)在《马唐草边疆:美国的郊区化》(Crabgrass Frontier)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虽然大众汽车化并没有产生美国郊区化的经典模式,因为后者出现于汽车拥有扩张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但是大众汽车化大幅度地促进了郊区化,于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就变成了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谓的“一个没有边界的城市”:洛杉矶以一个永远扩张的郊区网络为特征,这种网络互相联系的要点便是高速公路。[10-11]
然而,大众汽车化导致的不仅仅是低密度的郊区化,更是一次对城市的激进重组。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许多欧洲国家的城市规划师抓住时机,围绕着汽车优先原则重构城市。最突出的例子是联邦德国,在像科隆和汉堡这样曾遭受炸弹猛烈轰炸的城市,如今大量的市内高速公路便在其中穿行。[12]崭新的环城公路围绕着各大城市,从而限定了市中心的范围,市中心被改造为一个没有居民居住的空间,仅留给各种商店和办公楼——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商务区。在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在20世纪40-70年代期间,新建道路与清除贫民窟相吻合;在伯明翰,内环路的建造导致沿途大约3万座房屋被铲平。[13]毗邻新建道路的区域皆成了“衰退”(twilight)区,那里人口日益减少,有不能或是不愿搬离的老人和商店店主,过着岌岌可危的生活,这是高速公路将他们与城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的结果。[14]新的道路系统实际上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社会地理学,这往往是城市规划师所始料不及的方面。
第三,大众汽车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一种关于城市的新概念,亦即城市以汽车拥有者而非以行人、骑自行车人或有轨电车驾驶者为优先来组织。对此,芭芭拉·施穆基(Barbara Schmucki)更是得出以下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德的规划师将城市视为“交通机器”,而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便是为源源不断的汽车提高速度。[15]不过,城市规划本身也开始思考如何容纳汽车——英国规划师柯林·布坎南在其1963年著名的政府报告《城市交通》(Traffic in Towns)中使用了“交通建筑学”(traffic architecture)这样的说法。[16]英国的确是发展这种新的“交通建筑学”的先行者。尤为重要的是,道路安全运动的相关人士提出了以下观念:汽车交通应该与步行者严格分开。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与上述观念一起出现的还有:城市既要被纵向规划也要被横向规划,从而分区规划浮出水面。布坎南为伦敦的牛津街提出了一套分层式的设计方案,例如,汽车行驶在地面这一层,步行购物消费在上一层,而居民公寓在最高一层。这样的设计转而催生了所谓“超级建筑”(megastructure)的构想,即在这样的建筑内部会设计道路和车库,比如位于伯明翰的斗牛场购物中心(Bull Ring)。在一些新的城市,像苏格兰的坎伯诺尔德,把城市中心建成一个巨大的超级建筑,以供人们购物、工作和居住,而建筑本身由新型的道路系统相连接。[17]在这个意义上,汽车时代的到来促使规划师和政治家去想象新的组织城市结构的方式,从而能够回应新兴的汽车化社会的理念。
三 汽车的政治学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研究路径是,与汽车化相关的政治学和文化。我已经指出,随着汽车生产成为制造业经济的核心,社会开始日益依赖石化燃料,公路游说团也开始发挥能够感觉到的影响,于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汽车体制嵌入社会的时期,汽车体制开始重塑很多西方国家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一些晚近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汽车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在《司机共和国》(Republic of Drivers)一书中,戈登·塞勒(Cotton Seiler)认为,正是通过汽车化的各种实践和形象,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才理解自我与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美国所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塞勒认为,“在20世纪,开车行为本身就呈现了典型的‘美国人’形象”,“做一个美国人就等于要将汽车化视为自己的栖居之所和生活习惯”。[18]我并不想详细阐述塞勒讨论的细节部分,或者判断其观点的对错。这里的关键在于,他试图通过透视由技术所媒介的主体性来理解政治;汽车被视为一种媒介物,通过这个媒介,清晰地表达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嵌入到这种认同中的各种东西,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既有分属的不同公民群体。
在法国,20世纪60年代克里斯廷·罗斯(Kristin Ross)把汽车放在中心位置,对所谓的“日常生活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做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在同一时期,由于法国在海外的非殖民化和资本主义,法国政府便将注意力集中在60年代国内的消费革命,这场消费革命的缩影就是汽车——“20世纪一切现代化的核心交通工具”[3](P.19)。就文化表征而言,罗斯指出,汽车在各大报刊上无处不在;大众迷恋于像小说家阿尔贝·加缪这样的全国名人惨遭车祸死于非命的新闻;在一些电影里,也展现了人们对于汽车的迷恋,像让-吕克·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1965)和马塞尔·卡恩的《说谎者们》(1959)。对于批评家罗兰·巴特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话语中,只有食物是和汽车一样重要的。汽车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汽车有助于在法国的日常生活中嵌入一种新的消费文化,一种“极端的日常性”(sublime everydayness),与其他相对逊色但也是消费革命必要组成部分的东西共同发生作用,像吸尘器和洗衣机。[3](P.22)
在英国也是这样的状况,最近的一些写作已经指出,汽车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在英国很具特色的是,讨论汽车问题的框架是在有关阶级的争论之中的,特别关注所谓的“富裕工人”(affluent worker)——在类似汽车制造业这样行业中的高技能和高薪酬的男性工人,社会学家把他们视为正在发展一种私人化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这与工联主义、合作社运动和工党所体现的集体主义传统是背道而驰的。用政治术语来说,这些工人被认为正在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过程,这让他们远离社会主义和阶级意识,迈向一种被消费所驱动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像汽车和电视这样的物品将势不可挡地导致一套“中产阶级”的、保守的社会和政治态度。④20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都认为,资产阶级化事实上并没有在工人阶级家庭发生,虽然其他的社会变化,比如说“私有化”,的确发生了。John Goldthorpe et al.,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Cambridge,1968);Mike Savage,I-dent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the 1940s:the Politics of Method(London,2010);Mike Savage,‘Working-class identities in the 1960s:revisiting the Affluent Worker study’,Sociology,39:5(December 2005),pp.924-926;Dolly S.Wilson,‘A new look at the affluent worker:the good working mother in post-war Britain’,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17:2(2006),pp.206-229.不过,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众汽车拥有权的扩散开始以新的范式来编织生活。社会观察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和彼得维尔·莫特(Peter Wilmott)在1958年就发现了这点,通过考察伦敦周边新建房地产的布局以及家庭、工作地点、商店和亲戚家之间的距离,发现这些都是“驾驶汽车的距离:一辆汽车就像一部电话能够克服地理上的差距,从而将分散的生活组织成一个更易管理的整体”[19]。从我个人研究的早期证据来看,上述对生活的重组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于过去种种生活模式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用刚刚获得的汽车来维系与原先社区以及熟人的联系:开车回过去的酒吧(依然是“当地的”),找人一起踢足球,去拜访老邻居、老朋友和亲戚。起码就短期而言,“社区”(Community)适应着汽车,而非被汽车所瓦解。⑤Simon Gunn,‘The people and the car:automobility and the city in 1960s Britain’,2013年即出。
四 结论:20世纪西方的汽车化
这些大众汽车化研究的新路径是把汽车作为接近于城市现代性的中心来思考的,不论是否假借了伟大的高速公路规划师的做法,像纽约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抑或将汽车与大众神话式的自由相联系。正如这里指出的,汽车的意义部分地在于其象征性;比起其他任何商品,汽车更加能象征自由地行动、自由地走出去大干一场,而这是构成20世纪西方现代概念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过,正如我已经试图强调的,比这点意义更加深远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众汽车化导致了种种物质与政治的后果。我们看到城市转型的物质方面,城市根据汽车优先原则来重组或重建。有人或许会说,汽车化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城市规划的指导原则。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于汽车化政治学的研究,如“碳经济”的历史、石油政治学、在重新界定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个范畴时汽车所起的作用。⑥比如,参看Timothy Mitchell,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London,2011。我们只是刚刚开启对于这方面历史的书写;然而,即便我们开始做这些工作,我们也都意识到21世纪的汽车化历史将不仅仅由西方来书写。于是,将会有关于南半球和东半球的大众汽车化和特大型城市的历史,将会有关于墨西哥城、首尔和上海的历史。⑦这当然是像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这样的批评家在他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London,2006)一书中所持的观点。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历史将会呈现出什么面貌,也不知道是什么主题,像气候变化一样,也可能这样来书写。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这些新的汽车化历史在2015年或2050年被书写出来的时候,将非常不同于自由、消费主义和现代性的叙事,因为它伴随着整个20世纪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汽车时代的来临。
[1]Colin Buchanan.5th Rees Jeffrey's triennial lecture[M].London:Town Planning Institute,1961.
[2]British Road Federation.Basic Road Statistics[M].London,1971.
[3]Kristin Ross.Fast Cars,Clean Bodies:Decoloniza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M].Cambridge:Mass.,1996.
[4]Tom Lewis.Divided Highways:Building the Inter-State Highways,Transforming American Life[M].London:Penguin Books,1999.
[5]John Urry.Mobilitie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6]Dennis Kingsley,John Urry.After the Car[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9.
[7]William Plowden.The Motor Car and Politics,1896-1970[M].London:Bodley Head,1971.
[8]Steven Graham,Simon Marvin.Splintering Urbanism: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Technological Mobilitiesand the Urban Condition[M].London:Routledge,2001.
[9]Peter Merriman.Driving Spaces:A Cultural-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s M1 Motorway[M].Oxford:Wiley-Blackwell,2007.
[10]Kenneth Jackson.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1]Mike Davis.City of Quartz: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M].London:Verso Books,1990.12.
[12]J.M.Diefendorf.Artery:urban reconstruction and traffic planning in postwar Germany[J].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89,15(2):131-158.
[13]Anthony Sutcliffe,Roger Smith.Birmingham 1939-1970[M].Lond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4]Alison Ravetz.The Government of Space:town planning in modern society[M].London,Boston:Faber and Faber,1986.77-78.
[15]B.Schmucki.Der Traum vom Verkehrsfluss:Städtischen Verkehrsplanung seit 1945im deutsch-deutschenVergleich[M].Frankfurt u.a.:Campus Verlag,2001.
[16]Colin Buchanan.Traffic in Towns:A Study of the Long Term Problems of Traffic in Urban Areas[M].Harmondsworth:H.M.Stationery Off.,1964.
[17]John Gold.The Practice of Modernism:Modern Architects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1954-1972[M].London:Taylor&Francis,2007.146-164.
[18]Cotton Seiler.Republic of Drivers:A Cultural History of Automobility in Americ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9.
[19]Michael Young,Peter Wilmott.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M].London:Taylor&Francis,1958.158.
Abstract:In the 1950s and 1960s,with the expansion of mass car ownership,Britain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aw the advent of mass automobility.Historians are beginning to reflect on this phenomenon,and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new approaches to it,which can be summarised as the idea of the‘car system’,the impact of mass automobility on the shape of cities,and the politics of mass car ownership and how far it worked to transform everyday life.
Key words:the West;modern history;mass automobility;car system;urban form
(责任编辑:沈松华)
The Car and the City:New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Automobility in Britain and the West
Simon GUNN1,tr.DING Xiong-fei2,ZHANG Wei-liang3
(1.Centre for Urban History,University of Leicester,Leicester,UK;2.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3.School of Humanitie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K15
A
1674-2338(2012)05-0085-05
2012-04-22
Simon Gunn,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主任、教授,《城市史》杂志主编;丁雄飞(1990-),男,江西丰城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张卫良(1962-),男,浙江海宁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