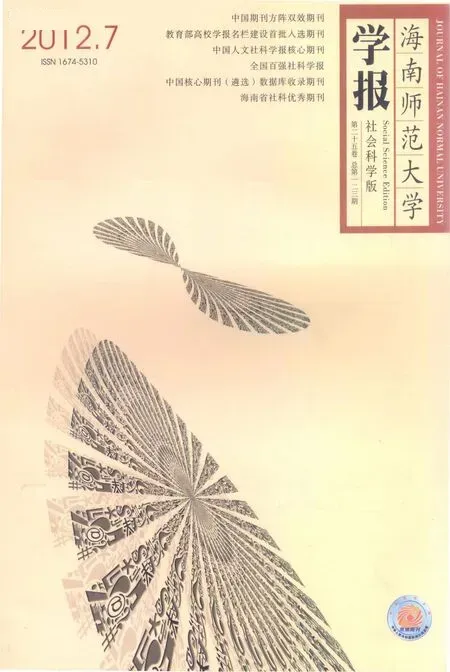论王阳明的知行观
刘华初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一 中国思想史上的知行观
在我国思想史上,“知”与“行”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语》和《左传》中。根据《国语·周语(上)》,邵公在谏厉王时有这样的一句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在《左传》里也有相似的文字记载,譬如“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此外还有论及先了解后行动的策略,即采取军事、政治方面的实际行动之前,对所涉及的事情现实状况与难易程度进行基本判断,据此而选择进攻或暂时退让的具体行动,所谓“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知”这个字进行文字考古,会发现其最初的含义是难以确定的,可是相反,在我国历史上对“智”字却是有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解释说明的,如《说文》中有“智,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的文字。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知”与“智”的字义变得逐渐相通了,都被赋予认识、知道与智慧的意义。据考证,“行”也是由其本义所指的道路四通八达,经过演变,最后变成了《说文》中所谓“行,人之步趋也”的意义。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大多都很关注与知行相关的问题,因为,在我国历史上,现实的社会问题总是主流思想家们首先要面对和思考的,要提供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而且他们——特别是儒家和接受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官员——总是倾向于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思想可以与政治统治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直接地解决现实问题,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总之,“知”、“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
关于儒家知行观,首先当论孔子的知行言论。他在《为政》中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众所周知,这是孔子在强调认知状况的重要性,对一件事情知道还是不知道这是最基本的,不能含糊其词。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就涉及到知与行关系问题了,只不过这里的“行”不是指具体的行动,也不是后来思想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实践,而是指主动的思考。换言之,有“习”参与的思考,归属于行,而不是归属于“知”的被动性的学。孔子又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积极敏捷,是基于知晓的言论不及行动的重要,表现出孔子积极行动的入世态度。而对于老子这位超脱现实主义的先哲来说,“知”与“行”二者显得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事情,所谓“圣人不行而知”(《道德经》),因为老子认为人的知识并不来源于外在的经验,而从根本上来源于与万有相对立的形而上之“道”,这表达了他以“道”为最高境界的哲学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基本思想,但是在知行关系上与孔子有所不同,用现代西方哲学话语来说,孟子是一个典型的先验唯理论者,因为他排斥感受经验、感性认识的本原地位,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高度强调“思”的重要性,他把尽心、知性、知天作为人们应该去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含有浓厚的理性色彩。他没有明确地提到“知行”关系,但是其“良知”、“良能”概念成为后来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主要理论源头。荀子在《儒效》里也明确地论及“知”与“行”,他把人的认知分成几个不同层次,但无论是来自书本和他人的间接知识,还是直接的感觉经验所得,抑或理性知识,都不如行动重要,对事物的“知”虽然指导着对事物采取具体的“行”,但现实的“行”却又具有高于“知”的方面。用现代话语来说,行动既是认识的来源,更是认识的目的,这表现出他与孟子先验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倾向。不过,荀况所说的“行”的范围还是局限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原则和各种礼仪规范的道德行为。在荀子之后,韩非提出“参验”,以“行”验“知”的思想,认为“参验”是检验言辞是非的可靠方法,所谓“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拭臣》)。而且与孟子等人侧重于道德层面上的“行”不同,韩非所讲的“行”已经包括农耕备战、富国安邦之类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了。
到宋明理学阶段,以程颢、程颐与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念。他们认为“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对事物有了认知也就能够采取行动了。可见在程子看来,知是行的条件,行是知的后续和结果。概括起来说,二程在知行关系上的论述包含有三个方面:知本行次、知先行后、知难行也难。知与行不可分割,对事物知道得越深入,行动就越到位。如果说有所谓知之而不能行者,那其实是因为知道得不够;对于应该做的事情人会自然而然地去做的,不会刻意地去做就能够实现。对于知行关系方面的问题,二程似乎更侧重于认识论的角度,而较少言及具体实践中的困难,也未联系到后来朱熹的伦理道德。
不过,朱熹的知行观与二程相比是有所不同的,主要表现在,朱熹涉及到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他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九)。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在时间性的先后次序上知为先,而论它们的重要性,则行动更加重要。在朱熹那里,“知”既指知识,又指求知;“行”不是泛指一切行为,而是指对既有知识的实行,其涵义稍狭窄。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但就其讨论的特定问题而言,朱熹强调的是道德中致知与力行的相互关系,因为他要把知行观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所谓“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就是说,无论是读书还是对世界上事物的探究,最终还是要把握住深层次的道德观念;但在伦理实践上朱熹重视“行”,同时也主张知与行的融合和互动,虽然知先行后,但并非一定要达到“知至”才去力行,在实际行动中,知与行要齐头并进,如此才能相互助长和激发。在此基础上,朱熹弟子陈淳进而提出“知行并做”的思想,认为知行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相似,朱熹的早期思想接近陆九渊,认为心的主观能动性有积极一面,但后期放弃了中和旧说而发展出心、性、情三分的观念,他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心的把握、对心的对治。钱穆先生曾经说朱学就是心学(广义的意义上),即如何在涵养和治心方面开辟出一条有效的功夫之路。朱子晚年的功夫是艰苦的功夫,他不再对人心持确定的乐观态度,他认识到人心容易受到恶的势力的影响,心的漂泊不定需要功夫来把持,所以他更追求持敬。这很类似于康德所提出的敬重的道德情感,因为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
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在我国思想史上,程朱以降有关知行关系的观念,构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也是他创建自己的知行观的理论出发点。正如杜维明所说,不理解朱熹的知行思想,就不能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真实内涵。[1]王阳明并不明显地反对朱熹的知行观,他甚至在朱陆之间持某种“中立态度”,他的许多问题与哲学意识都从朱熹而来,譬如“格物”之说。朱王学说各有差异侧重,朱学重在经世致用,重于事情的外在性,在王阳明看来好像沾染了一些感性的成分,从而暴露出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恶的那一方面。而王学则侧重于个人的身心性命,他张扬心善而少谈经世,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说法,是因为不满于当时流行的知行不一的社会风气。他认为,经世致用的外化结果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人们内心的善已经丧失了,内心的道德准则被重物质性的、重现实利益的外在行为所吞噬。王阳明不是一个如佛教徒那样把修身养性纯粹指向内心世界的遁世主义者,恰恰相反,在现实世界里,他的丰功伟绩毫不逊色于许多将相君王,而且其面向现实的大局观也很强。他还以身作则,在广西田州军机繁忙之时仍然和弟子们讲学不断,并且在每一次采取军事行动前,他都要“扪心自问是否会有愧”,以做到行动与其思想理论的统一,不愧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伟大实践者。
王阳明的基本哲学命题是“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他是在龙场“格物致知”而大悟的次年开启“知行合一”论题的。他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首先,“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紫阳书院集序》),简要说来,“心即理”是就本体而言,“心外无学”是就功夫而言,故而“致良知”乃是“求理于吾心”,“行”是发之于内的功夫,我们“不必向外求索”什么道理,故有“知行合一”之旨。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详细解释了他为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第九章)。与佛学的内心指向不同,王阳明的“心”是面向现实社会的。他提出“知行合一”主张的社会原因,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道德危机。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现当下我国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细化解读。①例如,陈来认为,所谓一念发动有不善即是行,从“知是行之始”方面来看,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既然意念、动机被看作整个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意念之动机即是行,……然而,如果这个“一念发动”不是恶念,而是善念,能否说“一念发动是善,即是行善”了呢?如果人只停留在意念的善,而并不付诸社会行为,这不正是阳明所要批判的“知而不行”吗?可见,一念发动即是行,这个说法只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一个方面,它只适用于“去恶”,并不适用于“为善”,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显然是不能归结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参见: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而张世英则有不同的见解:王阳明专从道德意义上讲知行,几乎不讲认识论意义的知行,所以在他那里,知与行相合一的程度达到了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最高峰。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更明显地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行……此“一念”既是道德意义之“念”,则念善便是道德,念恶便是不道德,故一念之初便已是行。王阳明从道德意义上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把道德意义的知行作为知行合一说的“立言宗旨”,正是抓住了以往儒家一贯偏重道德意义的知行问题的探讨和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思想的核心,可算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理论的一个总结和发展。(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如果考察王阳明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明代中期整个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道德危机,社会信任下降,出现了普遍的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社会现象。对于王阳明来说,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文人的责任重大,而要扭转颓废的社会局势,必须倡导“知行合一”的主张,来医治“文盛实衰”、知行脱节、只知不行的时代弊病。[2]以今天的历史意识反思来看,其实王阳明更应把问题之源归于皇权对儒学士人的排斥,而非仅仅士大夫阶层;这犹如崇祯死前怨恨士大夫误国,而缺乏对高度集中的皇权本身的反省。事实上,我们还是能够在王阳明的遗言中多多少少看到这种忧国忧民而无奈的叹语。
从中国哲学史上来看,知行问题主要是指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要知道,王阳明的“知”即是“良知”,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孟子有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良知良能是指一种先天的道德观念、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而非后天经验。在先验道德观,先天良知说上,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提出“心之本体”说,所谓“心之本体”即指良知,良知就是人心的本体,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作为社会之中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与能力;他又把良知看成即是天理,也即道。在王阳明的知行观中,“知”不仅对应着“心”,它还指向行动,因为“行”是心理上的意念活动,通过心又指回到“知”,即“良知”的所谓“发用流行”,或者“笃行”,因而有“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宗旨,就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良知”克服欲望,重新回复到“良知”之本体,并让本体自我显明。既然有“一”这个要回复的本体的存在,而且它也是知与行的依归,那么知、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体之外的“用”。如此一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知和行是一体之两面,知本身就蕴含着返回本体的行动,而行动也已经蕴含了认识到最终归于本体的“知”的存在。二者本来都是由“心”所生发,是“心”的外发,所谓“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先后之分。就“外化说”而言,王阳明的学说比黑格尔的精神外化为自然之说早了三个世纪。在王阳明看来,“知”乃是发自于内心世界,即那个本体的“一”,它指向本心良知而非外在之物;“行”就是要回复到那知之本体的行为。如此说来,“知”与“行”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逻辑环节,实际上是一回事,知是行的主意,而另一方面行是知的功夫。其次,从发生过程来看,二者同根同源,同时存在,难分先后,所以是合一的,知是行动之始,而行动则是知之成,相伴始终,难以区分开来。
与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不同,王阳明认为知与行不分先后,社会道德危机的发生正是因为知与行的次序之分的结果,因为先知后行很容易成为只说不做的借口,所谓“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正是由于普遍流行的这种观念导致了明朝中后期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行动上的矮子。面对现实中的社会道德危机,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之药。相反,朱熹的“知先行后”主张偏重于静观性的认识机理,而不是面向现实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性机制。王阳明有着更加紧迫的现实感,虽然理论上基于内心世界,但实际上是想恢复圣人之学,用理想型的道德律令于心,并直接实现其外化的社会效果,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当然,在内心与外在社会行为的表现上不存在差异性,也不存在任何实现过程。知与行都是内心的属性,是零距离、零时间相随的。他在《传习录》上举好好色、恶恶臭之例来说明知与行的时间性先后关系,认为人们看到好色与产生美感,既是知,也是行;它们归根结底说来其实是一回事。在“知行合一”进人道德范畴时,王阳明提出了他的立言宗旨,他说发动处的善与恶即伴随着对善恶意念的张扬或克服,前者是知,后者则是行动了。王阳明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让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在认识到道德危机的同时自我行动起来,践行已经认知到的道德准则。
简而言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有如下几个特点: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属于一个功夫,知行本体同一,知行合一并进,行而后有真知。内心意向的道德需要通过实践,才能变为现实的社会道德,唯此合一,人们才能实现现实社会的道德转变,解决社会道德的危机。对于面向现实的关怀,回应时代的挑战而言,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是殊途同归,“知行合一”与“格物穷理”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格物”由于是“求之于吾心”,实质内容是“去人欲”,“穷理”则是“存天理”。“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都是为解决当下道德危机而使用的不同形式的命题和范畴。
三 余论
“知行合一”与“心即理”、“致良知”构成了王阳明思想体系的概念基石,也是其从“知行合一”到“存天理去人欲”,再到“致良知”、“事上磨练”以及“四句教”这条实践伦理思想脉络的基础。为了根除明代中期社会上流行的言行不一的弊端,王阳明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进行了改造,主张“知行合一”,突出“事上磨练”,把认知落实到实践行动中去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基于社会现实,改造理论的一个创举。虽然在唯物唯心二元划分标准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属于唯心主义,但它包含了许多有现代价值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的思想成分,通过“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他实现了在伦理学实践与认识论的统一,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在这个统一性之下,知与行的一致性,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就很容易得到揭示。王阳明认为,只要人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在行动中实现儒家学者所主张的道德观念,就能够回到那个完善的本体,社会也会回归到理想的状态中。这种“知行合一”观揭示了能动性实践的实质,是中国哲学上完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统一的一次尝试。另外,从审美的视角来看,以“行”的功夫为主、内外合一的道德学说颇富东方文化和生命哲学之韵味。这在资本泛滥与技术主导人生的当下时代,不失为一种有效遏制内心空虚化的古老思想资源。
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倾向于自我内心修养的心学虽然在王阳明那里蕰含着儒家“内圣外王”和“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的结合,但是,常常由于对良知道德理性的价值的过分强调,最终会导致知识理性的客观性及其合理性的淡化乃至丧失,就更谈不上“经世致用”的发挥了,王阳明后学的发展历史性地验证了这一点。王阳明用“心”取代朱熹的“理”,把它置于最高本体,而将“理”归属于心体,这很容易导致常人的自我膨胀,从而脱离外在社会与世界,在知与行的天平上,人心逐渐倾向于自我之心了。毕竟人心内在之“善”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的“善”外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内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绝不是说到就做到了,行动及其效果还有待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经验上的具体实践。对内在心性之“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前提条件,但是,只有将它变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生活经验,才能最终实现善的真理认知与实存行动的统一,才能达到那个“本心”。
王阳明似乎从未想到要对行动的强调,更不要说将行动作为合一的本体,“知”似乎总是在前面,行动总是在后面,本体的归依渐渐地落脚到“知”、到心了,更糟糕的是,每个个体的人心相互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外在的行动及其所构建起来的世界,而不存在一个先天的人类共同之心,这才是王阳明所没有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关键之处。从“格物”转到“内心”,就必然切断了人心相互交往的通道,从而缺失对每个人所谓“知行合一”的检验标准,因为一个现实的、客观的、易于掌握的标准通常是外在化的器物,而不是各自内心的某种神秘的尺度。以内心抵制外在之物容易导致各说各话,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表现为独断专制,如明朝强烈的皇权集中和对士大夫阶层的排斥,王权拥有者会进一步张扬内心、排斥外理,失去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济世救民的胸襟。功夫内化失去了外在标准和传承方法,必然会步禅学之后尘,而禅学的发展后果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经验认知。西方哲学的理性发展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点,没有外化的客观性,内在的观念将失去准绳与意义,也不会结出现实的社会之果。
[1]张宏生.让儒学走向世界——杜维明教授的学术研究及其精神世界[J].中国文化,2001(1):351-360.
[2]任凤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J].前沿,2004(7):185-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