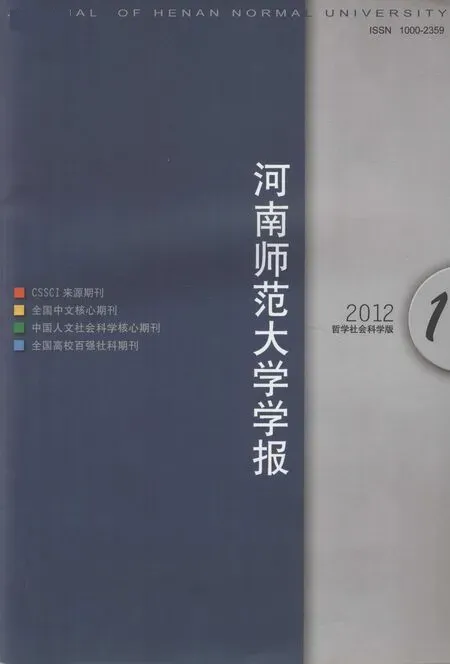论《铁皮鼓》的叙事伦理
周红红,徐 瑾
(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论《铁皮鼓》的叙事伦理
周红红,徐 瑾
(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因其多重主题与多重叙事略策当之无愧地进入到世界经典文学之列,其叙事伦理在其中起着潜在的然而是重要的作用。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是多维互动关系,作为人物的奥斯卡与作为叙述人的奥斯卡,第一人称叙述者与第三人称叙事者、叙述者的叙事声音与社会声音有重合也有分裂、有一致也有对立,从而显示出复杂的叙事伦理。
格拉斯;《铁皮鼓》;叙事伦理;叙事人称;叙事声音;社会声音
君特·格拉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但泽,二战时期被德国当局征召入伍,后因受伤成为美军俘虏,获释后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当过农业工人、钾盐矿矿工、石匠学徒工,学过雕塑与版画,其间还当过艺术学院画室模特的德国作家,于1959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铁皮鼓》,就是这一小说使战后德国文学又一次走向世界前列,随着1980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引起轰动,《铁皮鼓》当之无愧地成为最负盛名的世界经典名著之一。
一、《铁皮鼓》与叙事学: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是一个名叫奥斯卡·马策拉特的侏儒,警方怀疑他卷入一场杀人案中而被强行送进护理和疗养院(精神病院的委婉称呼),于是在白漆栏杆病床上侏儒奥斯卡在“清白”的纸上写下自己的供认状,并不断追忆自己的过去。关于《铁皮鼓》,人们可以用诸如现实主义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荒诞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历史反思小说、现代流浪汉小说、(反)教育小说、童话小说、戏仿小说、互文小说等各种名称称呼它,但几乎所有对《铁皮鼓》的评论中都强调了小说独特的叙事创新,强调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它不同于一般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是第一、第三人称混合的叙述方式,强调小说独特的叙事视角——怪诞反常规的另类视角,强调它的多种叙事手段。李万钧甚至把《铁皮鼓》提高到“20世纪小说叙事学”的高度,认为它最少有九种叙事手段:历史叙事,第一人称叙事,重复叙事,民间传说叙事,童话叙事,戏剧体叙事,荒诞叙事,反讽叙事,穿插独立的短篇故事[1]。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象征隐喻叙事、原型意象叙事等多种,但最为重要的作为各种叙事手段之统摄的无疑是第一人称叙事。马爱华认为《铁皮鼓》有一种狂欢化精神,而狂欢精神的首要特征和重要表现就是它的“奇异视角和意识复调”[2]。华少广羊也认为“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那种冷漠超然、荒诞滑稽的叙述风格,与小说的叙事角度有密切联系”[3]。
然而问题是,第一人称叙述在20世纪小说中几乎成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叙述手段,另类视角在小说叙事中也并非没有先例,早在欧洲古罗马小说和中世纪小说中就不乏愚人故事和愚人叙事,美国作家福克纳更是在《喧哗与骚动》中以多人称叙事——包括傻子叙事——开创了现代小说叙事手段的革命,为什么单单是《铁皮鼓》的叙事人称与叙事视角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事实上,单纯的叙事人称与叙事视角并不能解释这一问题,小说的信息交流决不是“现实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现实中的读者”[4]的单向度交流,在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读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维互动关系,即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其中可能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铁皮鼓》的叙事者与人物之间存在分裂,叙述人也不是单一的叙述人,叙事视角也具有隐蔽性,叙事声音也是多重的,从叙述人、叙事视角及叙述声音的角度讨论可以使我们将《铁皮鼓》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奥斯卡:人物视角、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
《铁皮鼓》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性丑陋、长像奇特的怪人,是一个身高只有九十四公分的侏儒,即使后来他决定长高了,也只有一百二十一公分。护理院的布鲁诺这样描写他的病人奥斯卡,“两肩之间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5]370-371。鸡胸驼背的奥斯卡生活艰辛,内心孤独,缺乏亲情,没有友情,得不到爱情,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个被社会抛弃几乎自杀的局外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他的奋斗史是令人心酸的自我奋斗史,他的一生是流浪的一生,因为是长不大(高)的侏儒,在常人眼里他永远是个无知的心智不建全的孩子、愚人和傻子,于是小孩子逼他喝下混有痰、尿液和青蛙的砖头汤,妈妈每周带着他去和表兄幽会,可能的父亲——表舅扬·布朗斯基——当着自己的面把手伸进妈妈的内衣里,打牌时把脚从桌子下面伸进妈妈的两腿间,大人们偷情时肆无忌惮地发出咂嘴声和吮吸声。孤独的奥斯卡只能依靠不断地敲击铁皮鼓远离污浊,忘记现在,追忆过去,寻找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慰藉。奥斯卡对成人世界的观察视角是“自下向上”[5]302和由内向外的视角,由下向上的视角是不同于常人的侏儒视角,由内向外的视角是不同于成人的孩子视角,这种视角展示的是一个撕开一切假面具的庸俗、无聊的成人世界,一个“靠拢人体下身的生活,靠拢肚子和生殖器官的生活,因而,也就是靠拢诸如交媾、受胎、怀孕、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6]。这是肉体的狂欢节,这是欧洲中世纪狂欢文化的世俗化、肉体化和庸俗化。
但是,《铁皮鼓》的观察视角(人物视角)和叙述视角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有重复的部分——他们都是侏儒奥斯卡,他们也有分裂的部分——叙述者奥斯卡是二十八岁的被关在疗养和护理院的杀人嫌疑犯奥斯卡,他的听力异乎寻常的强,还在母体时就能听到母亲与假想父亲的对话,就因成人世界的无聊而想回到母体,他有超过常人三倍的智力,有唱碎玻璃的神奇的能力,于是借着唱碎玻璃保护自己,借着鼓声追忆过去。于是,奥斯卡可以穿越时空叙述自己没有出生之前甚至母亲出生之前的外祖母“肥大的裙子”,可以多次反复追忆自己的流浪经历,追忆母亲的死、可能的和假想的父亲的死、朋友特鲁钦斯基的死、情人罗丝维塔的死、犹太商人马库拉的死,在追忆中人们感受到人性的真与善、世界的美与丑,感受到奥斯卡的爱与恨、情与仇、追求与失望、理智与疯狂,奥斯卡还以全知者的口吻叙说尼俄柏的传说、但泽的历史,模仿童话写下“有信有望有爱”一章,造成音乐中的赋格曲风格,以幻想式叙述把自己描写成耶稣童子,把一个鸡胸驼背的裸体侏儒坐在一个一米七八的裸体女模特腿上叙说成圣母与圣子,奥斯卡还多次写出歌德式的“日神”状态和拉斯普庭式的“酒神”状态,写下自己身上弗洛伊德式的“第三根鼓棒”。
这一切都只能是回顾性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专利”。“第一人称叙述成功地造成了四个结构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1)被叙述的事件本身;(2)叙述者幼年体验事件的眼光;(3)叙述者追忆往事时较为成熟的眼光;(4)叙述者未意识但读者在阅读时却领会到了的更深一层次的意义。这四个层次的四重奏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特有的‘专利’”[7]。事实上,第一、二个层次并不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专利,而是与第一人称情境叙述或曰人物叙述共有,第三个层次才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专利,《铁皮鼓》的叙述者的叙述是小说人物奥斯卡二十八岁时在精神病院的回忆,当然属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他不但能追述自己三十年(从精神病院无罪释放时已是两年以后了)的经历,还能在重复叙述中进行自我质疑和自我观照,戏仿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语言风格,奥斯卡的口吻是笑谑的、反讽的、怪诞的、诙谐的和喜剧化的,他把沉重的话题轻松化,历史的话题游戏化,崇高的话题戏谑化,悲剧性的人物喜剧化。因为“奥斯卡则是一个小小的半神……优于自古以来的全神们”[5]287。他不但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还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他不但是事件的亲历者,还是生活的旁观者,这“不关痛痒的生活参与者,为永远是生活窥查者和反映者,找到了一种生存形式,也找到了反映这一生活,将它公之于众的特殊形式”[8]。他在身体上低于常人与成人,他在智力上远远高于常人与成人,如果说奥斯卡观察的视角是由下向上和由内向外的仰视角,那么他叙述的视角就是由上向下和由外向内的俯视角,这是一种超然的具有自我优越感视角,这一叙事策略和叙事手段让作为叙述者的奥斯卡与作为人物的奥斯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从叙事伦理上看,申丹所说的四重奏的第四重并不能算作第一人称视角专利,而是由叙述人与读者所共有,这里实际上关涉到一个叙事话语与(叙述)声音关系问题。自从巴赫金在研究小说话语的多声部时使用了声音这一概念以来,声音已经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涵义,兰瑟认为声音既可指“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化”[9]4的“叙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9]3。也可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9]4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费伦也从叙事修辞的角度认为叙述人、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与声音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有时叙述人的叙事话语与叙事声音是一致的,有时是分裂的和暗含性的,因为声音“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10]19,“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10]20,“声音包含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相同的文体、语气可以展示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由不同的文体语气暗示出来”[11]。叙述人奥斯卡的话语是笑谑的、反讽的、怪诞的、诙谐的和喜剧化的,他的声音是超然的和冷漠的,他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他从不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情绪变化,也不发表自己的对社会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外祖母的‘四条裙子’象征着女性和母性,象征着生命、爱、温暖、和平、安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所在,也是现代人类希望、光明、互爱、安全的保证”[1]。奥斯卡一次次回忆外祖母,回忆自己如何钻到外祖母的裙子下,但只是以一种平静的语调叙说,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孩子们逼他喝下砖头粉汤,他也没有丝毫的愤怒之情。母亲阿格内斯可能是世上唯一真正爱着他的人,但母亲死了,他只是作为一个鼓手,叮叮当当地敲着铁皮鼓把母亲送走,还一直对那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记忆犹新。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死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送葬,没有生命逝去的悲哀,甚至当他间接地害死了可能的父亲扬·布朗斯基和名义上和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时,他也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愧疚之心。在这里,我们看到奥斯卡的叙述声音与社会声音也存在距离,在奥斯卡冷漠的叙述中我们分明感到他的心灵世界的冷漠,他没有爱憎感也没有是非感,他不进行情感评价也不进行道德评价,奥斯卡的冷漠是他的侏儒身份造成的吗?是他的流浪经历造成的吗?是庸俗无聊的德国小市民习气造成的吗?是战争的冷酷与血腥造成的吗?或许兼而有之?奥斯卡没有明说,格拉斯把对奥斯卡的评说与对奥斯卡声音的“细听”留置给了读者。
三、两个面具:双重叙事背后的双重声音及其重合
《铁皮鼓》并不是单一的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手法,奥斯卡以我的口吻叙述时格拉斯还不时地插入另一个叙事者,我们先看下面一段话: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5]179
在这段话中,开始是“我”——作为主体的奥斯卡——在叙述,突然隐含作者把我降到作为客体奥斯卡的地位,说“奥斯卡苦修苦行”,“逐日消瘦”,随后又没有任何过渡与征兆地转为“我”的叙述,但是读者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阅读障碍,像这样的叙述人的转换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这个第三人称叙述者是谁呢?或许是作者,或许是隐含作者,或许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自我指称,这实际上是叙述者的两个面具,这样,单一叙述者裂变成两个叙述者的双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往往以“叙而不议、超然冷漠的语调来回忆往事”[2],第二叙述声音如影随形地跟着奥斯卡,或者就站在“我”的背后,他的叙事同样是冷漠的,但在这叙述声音之中我们不断地感受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作者的具有显明意识形态倾向的声音——存在着,这是一种反思历史与民族、反思战争与苦难的声音。
《铁皮鼓》的故事时间上起1899年,终于1954年,重点是1939—1946年,二战是故事的主要背景,像个人经历叙述一样,奥斯卡以同样的冷漠述说着历史,述说着战争,对奥斯卡来说,战争以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犹太人的会堂被烧毁了,马策拉特拉着奥斯卡来看热闹,还“借着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5]171。一边是战火纷飞的波兰保卫战,一边是奥斯卡和扬·布朗斯基玩斯卡特纸牌。奥斯卡不断听收音机里的战事报道,但那些报道只是他学习地理知识的途径。奥斯卡的师傅贝布拉率领由侏儒们组成的“前线剧团”到防御工事访问,他们眼睁睁看着纳粹上士用机枪射杀附近的修女而无动于衷。“那种荒诞的情节和无动于衷的语式,使读者分明感到,对死亡恐怖的描写,更多的是一种玩赏,一种戏谑,犹如观看一部喜剧”[3]。奥斯卡参与战争并不反思战争,置身历史但不把事件历史化,奥斯卡早已用他的鼓把战争敲碎,用奇特的声音把历史唱破,在奥斯卡那里,历史成了零乱的符号化的碎片,历史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奥斯卡(人们)不需要对历史评头品足。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相互缠绕、难以区分,人们很容易把两者所暗含的意识形态观念模糊、混淆甚至等同起来。但是“作者声音的存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而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以传达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观或判断上的差异”[10]21。格拉斯是一位有道义感责任感的作家,他出生于但泽这个现在归属波兰但历史上多次易主的苦难城市,他的父亲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亲身参与了纳粹战争还成了美军俘虏,他身上流着两个民族的血液,他同情波兰人也反思纳粹德国给世界造成的灾难。二战期间希特勒为了实现纳粹统治目的,用强制和蛊惑的手段把普通市民组织起来,每周日党卫军、青年团员、妇女队员和普通市民涌向五月草场听纳粹在台上演讲,奥斯卡却在台下敲起他的铁皮鼓,使众人跟着他的节奏跳起浪漫的华尔兹,这是具有强烈反讽效果的叙述。奥斯卡的师傅贝布拉一方面宣称“内心流放”,另一面又组织“前线剧团”到纳粹战场的前线进行慰问表演,让人联想到战时德国一些知识分子的行为。小说不时地对纳粹语言进行戏仿,如“有的想在创造历史时亲临现场”。“泥泞时期到来时”“奥斯卡也开始在泥泞地里使劲挖掘。”在这里,叙述者的叙说保持了一贯的冷漠与戏谑,但在滑稽可笑的场面描写和戏仿反讽的语言中我们感到另一种对战争的态度,对纳粹行动的嘲讽,对历史的反思,这是隐藏在叙述者语言下的另一种话语,这是作为个体声音的叙述声音背后的另一种“社会声音”,显示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观或判断上的亦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毫无疑问,说不尽的主题与说不尽的艺术独创性已让《铁皮鼓》当之无愧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之列,而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对《铁皮鼓》艺术手法与主题的每一侧面的深化与展示都是起着潜在的然而是重要的影响。作为对《铁皮鼓》叙事伦理的最后补充,读者也许会发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奥斯卡与作者的声音在分裂之后有渐趋重合的征兆,艺术学院里的学生“在每一个画架上,(让)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拆社会”[5]402。洋葱地窖里,奥斯卡让人们在被称作无泪的世纪里“体面的哭泣,无碍的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5]456。奥斯卡的声音终于与作者的声音合一了。
《铁皮鼓》的叙事伦理,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李万钧.格拉斯的《铁皮鼓》与20世纪小说叙事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2).
[2]马爱华.论《铁皮鼓》的狂欢诗化精神[J].当代外国文学,2002(3).
[3]华少广羊.试论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荒诞与真实[J],外国文学研究,2000(3).
[4]Chatman Seymour.Story and Discourse[M].Ithaca:Cor-nell UP,1978:151.
[5]君特·格拉斯.铁皮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格拉斯.拒绝经典[J].世界文学,2000(2).
[7]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3.
[8]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7.
[9]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王振军.论意识形态叙事的谱系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2).
I106.4
A
1000-2359(2012)01-0212-04
周红红(1966—),女,浙江诸暨人,语言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和词典学研究。
201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