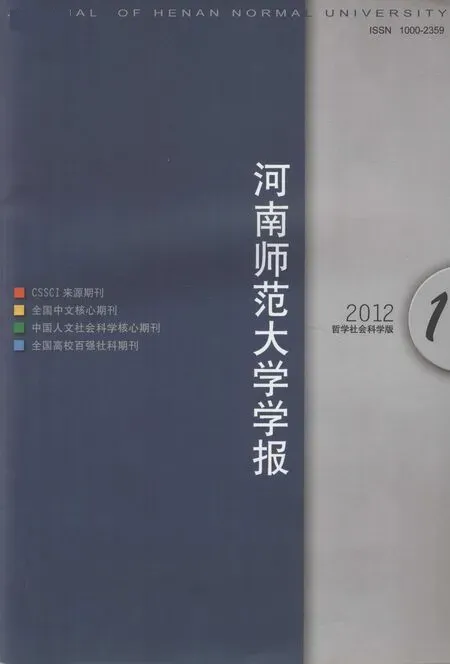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到废弃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认识轨迹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到废弃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认识轨迹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人民自治理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以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内容的新政治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维埃制度的三个重要理论支柱。戈尔巴乔夫最初把加强苏维埃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自治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与泛化的新思维理念在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戈尔巴乔夫的苏维埃制度改革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最高苏维埃体制转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引进总统制,再转而实行总统内阁制的复杂嬗变。在这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从改革苏维埃制度走上了废弃苏维埃制度的不归路。
戈尔巴乔夫;苏维埃制度;人民自治;新政治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一、人民自治理论的延续与结构改造思想的萌生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劳动人民的自治设想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一项切实可行的民主原则。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过人民自治的思想。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前辈们的概念和内容,强调“在为了提高苏维埃的作用与威信,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所有方式方法而进行大量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发展的理论问题”[1]10。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指出,要发展人民自治制度,就要在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民主原则,自治原则不是在“国家制度之外,而是在其中发展的”[1]330,人民自治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苏共“二十七大”的党纲把党、苏维埃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分别看成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体系,其中“党是推动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保障”,它本身又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而苏维埃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及其在实现人民的充分权力、团结和动员群众方面的巨大可能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完善政治体制,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就是开展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1]330-332,22。此后,“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人民自治”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号而被一再提及。
苏维埃是人民自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加强人民自治,必然要涉及苏维埃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了苏维埃这个“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称其为“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创造活动的成果”,并说,如果没有苏维埃,就不可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团结起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新经济政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苏维埃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维护者,它的最大特点便是自己做出决定和自己执行决定,“这是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2]135。但是,由于行政命令式管理体制的实行,苏维埃的威信降低了,苏维埃被排挤了,许多问题是在没有苏维埃参与的情况下解决的。党代替了苏维埃,执行机关凌驾于苏维埃之上,苏维埃不被尊重,不被理睬,功能得不到发挥,在国家生活中沦落到了二等甚至三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承认,这种状况曾引起注意和不安,也做出过决定和法令,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苏维埃的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改善[3]。于是,戈尔巴乔夫面临着或者说再次重复了与其前任几乎相同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治权力机关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体现者的作用”[2]137,即“苏维埃应该完全起到自己全权决策机关的作用”[4],也就是“要使各级苏维埃真正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运作中的发挥首创精神的全权的中心”。为此就要求扩大苏维埃的权限,厘清苏维埃与党和执行机关的关系,真正做到将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交由苏维埃去研究解决,而不再发生各级党委干涉苏维埃的内部事务、执行机关凌驾于代表大会机关之上或不受其约束的现象。要使苏维埃真正行使自己的全权,还需要改革苏维埃代表选举制度,使选举名副其实;同时,还要提高苏维埃自身的工作质量,把苏维埃会议从“隆重的会议”变成对具体事务的讨论,不是以举行会议的次数,而是以实际的效果来评判苏维埃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看法,固然有若干新的见解、新的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大多仍不过是其前任们一再重复的旧章。更重要的是,单单几次讲话、几个决议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它们能够落于实处,类似的措施已不止一次地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了。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恢复苏维埃的革命和民主本质的最初步骤”[2]138,而问题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防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扩大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5]38,40。要保证改革不再停滞不前,不使重复性的决议和措施再循环下去,就必须使苏维埃本身的地位和工作“实现创新性的变革”[2]134-135。实践已经证明,恢复人民代表苏维埃充分权力的任务用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根本解决,也就是要对人民代表苏维埃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造,以建立起能保障政治体制及时自我更新的有效机制,“这种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中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自治原则”[5]4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戈尔巴乔夫的目光开始游离苏维埃本身,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借鉴,以修补其人民自治理论,扩充苏维埃的内涵。而这时,另外两种观念即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与泛化的新思维理念已在他的思想中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两种因素的渗入和交互作用使得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二、社会主义人道化与对苏维埃体制的否定
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已把“人、人的利益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人的生命、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是最大价值”“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等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认为这是苏共实践活动的目标。新党纲因而被认为具有了“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1]292,372。这反映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但在此前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与僵化,民主化的目的是加深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而不是对既存政治制度的某种破坏。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长篇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70年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思考,这一总结与思考几乎涉及了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所有时期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他肯定十月革命所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认为向列宁的思想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他肯定斯大林及其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批评了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他赞扬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及其后的变革是“开始试图摧毁30~40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但也“犯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停滞现象则歪曲和损害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破坏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公正性的信心。评价这70年历史的目的在于肯定“成就是巨大的和无可争辩的”[2]45,46,但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本身已在孕育一场否定传统的激烈变革。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到了首位。戈尔巴乔夫认为,现行政治体制没有克服人与政权的异化,它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与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概括了它的基本特征,而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恰恰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有严重变形的社会主义”的。他表示:“我们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清除了以前各个时期的积垢和曲解,然而却继承了产生于我们学说奠基人的创造思想、靠人民的劳动和努力而实现、反映人民的希望和宿愿的一切优秀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吸取世界发展的全部先进经验,充分依靠人类进步成就的社会主义。”[5]96随着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理念的人道化、伦理化色彩越来越浓,他对苏联历史的批判与指责也越来越严厉,斯大林的理论被冠以“斯大林主义”而予以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被称为“专横的官僚主义体制”而遭到彻底批判;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异化的社会主义”而予以公然唾弃。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被替换,导致了群众对它的理解的歪曲,导致抛弃了马克思和列宁社会主义设想中的最主要之点,即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6]11。因此,对这种制度不应采取“修补”“完善”,而必须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彻底摧毁”“炸毁”。既然改革的重点已转向政治领域,这种“炸毁”“摧毁”也就必然首先指向政治体制,苏维埃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了。
戈尔巴乔夫为了批判斯大林而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和列宁,并把马克思和列宁全面彻底人道化。这种以传统反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斯大林体制。但问题在于,苏联的整个体制是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则是斯大林的直接延续,而斯大林与列宁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所以尽管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力图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恢复全部真相”,“十月革命既不是错误也不是偶然事件”[6]10,“我们仍然要忠于1917年10月的选择,忠于社会主义思想”[7],但逐渐地,他自己也无力阻止自己呼唤出来的魔力而只能随波逐流了。这是必然的。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切实实的人道主义”。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斯大林以来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那里全是大规模的镇压、清洗、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变形等而没有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公开性”暴露出来的是斯大林的“暴行”“暴君”形象和历史的灰暗阴冷,而不再有人民的领袖和历史的辉煌;甚至列宁时期也充满着暴力、革命与流血,显然也与“人道”的原则相悖了。这种对历史的过分道德化、伦理化的图解显然已远远越出了历史主义的范畴,而过分沉溺于历史问题及过多地否定历史的结果是使人们丧失信心、激烈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践踏一切、打碎一切。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却不能给人民的权利以保障,作为人民自治机关却不能阻止政权的“异化”现象,甚至成了“专横的官僚体制”的附属物,它之被唾弃也是必然的。这样便不难理解,戈尔巴乔夫的人道化理念每进一步,他对历史的否定便加深一层,他对苏维埃的信心便失去一分。当他的政治理念从历史主义蜕变成纯粹的道德主义时,他也从完善苏维埃经由苏维埃与议会制度的结合走到了完全接受议会民主制。苏维埃变成了议会制度的一个部门,苏维埃体制被最终抛弃了,议会制代替了苏维埃,而戈尔巴乔夫对议会制的认同则是通过他的新思维实现的。
三、从借鉴到嫁接:新政治思维与苏维埃改制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对外政策相联系的,但它后来逐渐演化成了苏联改革中的一种“普遍哲学”[6]17,它包括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其核心则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2]184。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维护文明负有责任”,而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对阵的喧嚣声中,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属于这些文明成就的不仅有简单的道德和正义标准,而且还有形式上的权利原则。社会主义应该是一般民主与全人类理想和价值观的继承者、体现者和捍卫者。“社会主义革新的许多进程,从实质上讲,就是以某种形式在另一种社会土壤上发生的已普遍文明化的进程”[8]。新思维奉“全人类价值”为圭臬,它为戈尔巴乔夫引进西方政治准则改造苏维埃开启了闸门。随着他的“全人类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日益靠拢,吸收与借鉴也日渐变成了嫁接和抄袭。而当这个“全人类价值”与西方的价值准则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时,“引进”便是全盘的照搬和取代了。戈尔巴乔夫一系列政治观念的变化过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起初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制的反应还是比较审慎的。对于苏联国内的民主化改革,他主要是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从列宁的苏维埃民主理论那里寻找根据的,认为民主化对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损害,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苏维埃这种民主形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2]135。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被排挤掉了的苏维埃的全权。
1988年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进程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戈尔巴乔夫观念转变中的一个关键点。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用“借鉴论”与“结合论”为指导大幅度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制,试图实现苏维埃民主与议会民主的结合。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开始明确地把“全人类价值观”“全人类利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奉为国内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并置于突出的位置。“借鉴”从一开始便带有大面积嫁接的痕迹。它为戈尔巴乔夫政治观念的进一步倾斜埋下了伏线。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以发挥苏维埃的作用和功能为出发点,在民主的操作性、程序性方面引进了诸如权力的分工与制衡、差额选举、代表竞选、任期制、延长最高苏维埃会期等重要原则和规范,改最高苏维埃体制为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宣布党政分开,党只实行政治领导,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苏维埃民主制度,发掘其潜在的优势,并试图实现两种民主制度即苏维埃制与议会制的结合。上述种种,显然是“借鉴论”与“结合论”的延伸与具体化。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随着新思维强调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随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化、完善化,虽然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了让苏维埃变成真正权力机关的目标,但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走上了实质上完全相反的方向。根据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西方民主观实际上等同于全人类价值观,既然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那么由此便不难推导出西方民主观高于一切的结论来。多党制、三权分立、总统制等具体制度被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超时空的性质而直接突兀地搬运过来,而苏维埃则被一步步地挤出了政治舞台。
随着新思维与否定传统趋向的合流,戈尔巴乔夫最终完成了认同议会民主制和否定苏维埃体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突出地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的矛盾。作为一个苏联人、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不愿意承担否定历史的责任。他主张深入研究列宁、重新认识列宁,主张回到列宁去;他认为他领导下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革新而不是拒绝和抛弃列宁、布尔什维克和苏联人民在1917年10月所作出的选择[9]296;他意识到对全体苏联人来说,“社会主义的选择、苏维埃政权,这不是普通的词句,而是我们的基本价值、我们的方向”[9]310;“重要的是不要丧失方向,依然忠于社会主义前景,沿着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和建立正常的社会条件的道路前进,哪怕是困难重重和犯了错误也不退缩”[10]。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不满于苏联历史与他的日益浓厚的人道主义理念相距越来越远和冲突越来越强烈的事实。他要批判乃至毁灭这段与自己原则不相容、不可调和的历史。对于苏维埃也是一样。他不愿意丢掉它并赋予它极高的荣誉价值,认为这是俄国人民、苏联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最好的机关,但他又痛苦地发现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苏维埃却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目标;他接受了先辈们对议会民主制度的批判性分析,但他又在情感上认同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而且承认和赞赏议会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政治操作领域的巨大效力。这种深藏于情感深处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搅扰着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的改革。他希望苏维埃更有效力,试图把议会制度与苏维埃制度结合起来,吸收两者的优长,最后干脆企图把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等他认为卓然有效的一系列制度直接嫁接到苏维埃的躯体上,但在内心深处又割舍不下对苏维埃的依恋,于是便希望在名称上保留苏维埃的若干形式,在运作上保留苏维埃的若干原则。结果,苏维埃在改革中没能达到最优组合,而是成了实质上的牺牲品。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造最高苏维埃体制,他宣称其目的是为了激活苏维埃,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未见功效的情况下,又引进总统制,旋又改行总统内阁制。与设计者所宣称的目标完全相反,改制的结果,不但苏维埃被吞没了,而且政权崩溃了,国家也瓦解了。
[1]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3]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9.
[4]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N].真理报,1987-11-03.
[5]尧凌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8,40.
[6]米·谢·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7]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2月5日-7日)文件选编[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6.
[8]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N].真理报,1989-11-26.
[9]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10]米·谢·戈尔巴乔夫.八月政变(原因与后果)[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93.
[责任编辑 孙景峰]
D1
A
1000-2359(2012)01-0018-04
蒲国良(1966-),男,河南柘城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10019)
201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