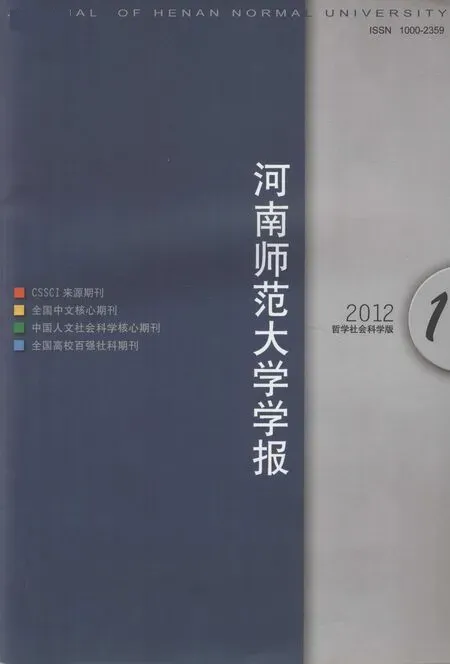从庙产风波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僧伽保护庙产的举措
单 侠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从庙产风波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僧伽保护庙产的举措
单 侠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庙产既遇到了外界强有力的冲击又遭到其自身肆无忌惮的挥霍。内外夹击的庙产风波加重了僧伽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从治标(强调庙产为佛教界所公有和积极呼吁政府切实保护)和治本(统制庙产、将庙产积极用于建设各项佛教事业及提高僧伽整体素质)两个层面来理清长期以来庙产的混乱局面。其标本兼治的举措既可保证庙产的合理利用,又可为佛教的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是解决庙产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以后庙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僧伽;庙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危机四伏的中国,无力以大量的财产投资办学和其他社会革新事业,而寺院甚多且寺院经济雄厚,如江南一些大寺拥有成百上千亩的地产,却多为少数无知僧徒所把持,以致不能用之于佛教正当事业的建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快业已开展的现代化改革的进程,加大了对庙产征用的力度,使庙产问题日益尖锐化。在外界的强力刺激下,僧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和佛教的存续,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条件和办法,竭尽全力去维护自身的利益。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风波
庙产指寺庙的一切财产,具体包括寺田、寺屋及其附属的法物等。民国以降,各地征用庙产现象更为普遍,其征用力度也远远超过了晚清,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庙产受到了比清末新政时更为严重的冲击。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风波更使庙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数以万计的庙产被强征或提取甚至挥霍,佛教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向社会各阶层推行启蒙运动,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公布法令,禁止人民以卜筮、占星等迷信活动为职业,宗教活动也被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为彻底贯彻中央政府这一破除迷信的政策,南京特别市长刘纪文首敕令社会局调查全市庙宇,下令如有完美精致之雕刻品、佛像则另造房屋以资保存,其余一概拆毁[1]。于是,各省相继发生捣毁神像的事件,起初仅以一般神庙为对象,后来蔓延及佛像。除了直接捣毁佛像外,政府当局还在破除迷信的旗号下大张旗鼓地实行打击佛教的政策,如北京设立了破除迷信会诉请政府勒令所有僧尼还俗改业,并严禁僧道于葬仪时诵经,致使“北平市之庙宇颓废残败,或改建工厂或租予小贩,结果使之七零八落,古迹日渐淹没”[2];浙江省政府民政厅为侵占庙产则通令全省各县禁止未成年人出家,并勒令二十岁以下已经出家者还俗,甚至通令各县党部解散僧道团体。此外,政府还积极提倡用庙产兴办公益慈善事业。1931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各寺庙应依其财产之多寡,兴办初等教育、图书馆、救济院(孤儿院、养老院、保育所)、贫民工厂、合作社等。次年,内政部指出,除古代寺庙有保存的必要外,“其余悉应移办公益慈善事业,由各地方组织委员会办理”[3]。在政府的倡导纵容下,地方团体、劣绅等纷纷染指庙产,以致庙产风波愈演愈烈:湖南、贵州等省的寺庙纷纷被地方提取以办理公益,甚至有些地方劣绅打着办公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占庙产,如四川有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修马路的名义把庙产差不多囊括殆尽[4]。
其次,教育界的侵占与掠夺使庙产的处境雪上加霜。由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补助与教育界的期望相去甚远,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使教育界人士及有关部门期望借庙产之力来普及教育。在此情况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吁请设立庙产兴学运动促进会,并得到了各省教育界中坚人物的积极响应,他们推行义务小学教育,借寺庙做校址,并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为学校的提议。鄂、浙、豫、皖等七省教育厅还联名呈请中央教育部,要求切实保障庙产兴学,厉行《监督寺庙条例》,将庙产悉数用作改办短期小学或其他地方教育事业[5]。受此影响,全国到处都闻有毁寺逐僧和占夺庙产的声浪:江苏镇江提倡义务小学百处(实际五十处)校址都设在寺庙里,所有寺庙不论首堂、二堂,都一律作为校址[6];大醒以切身经历、调查说:“在我的家乡那一县城,约有学校二十所,只有一所有建造的校舍,其余都是占用的寺庙房屋。”[7]即使远离江浙一带的山西铜梁县教育界也召开教育行政会议,议决将庙产全数提作教育经费,并设庙产清理处以彻底推行庙产兴学。直到40年代,因创办新式教育而发生的提占庙产事件,可以说遍布全国。
佛教界内部肆无忌惮地挥霍使庙产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1931年2月4日,上海《威音》佛刊社海珊法师在致大醒的信中指出:现在这班当住持的对于庙产不是管理而是实在的享受、百般的依赖,不但不作任何慈善事业而且佛教教育也一筹莫展,他们只知买洋房、住高楼、着锦服、贪美味。河南的长老方丈们穿的都是绸缎衣服,“他们小袖长衫,炫目光彩之色,皮鞋、洋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8],以致有冯玉祥驱逐僧尼,掠夺寺产的事发生;云南长老方丈们的工作就是吃、喝、嫖、赌,“吃完饭向大烟床上一倒,小和尚替他烧烟、倒茶,脾气来了,拿小和尚做个出气桶”[9]。这些住持大和尚除了肆无忌惮地挥霍及为自己谋相当的利益外,对整个佛教没有顾及,为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加大对庙产的征用和侵占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产风波既包含外界强有力的冲击,也有其自身腐败因素的积累。内外夹击的庙产风波加重了佛教界的危机意识,使他们加大了反抗的力度,反抗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或被动地去寻求各种保护,并向政府呐喊、吁请;或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进而大声疾呼庙产改革和各项佛教事业建设。
二、僧伽保护庙产的治标之举
针对庙产被严重征用或侵占的事实,佛教界最直接的反应是保护庙产并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强调庙产为佛教界所公有,外界不应也无权觊觎。佛教庙产性质向未确定:或被视为地方和国家公有,地方与中央可任意侵凌毁改;或被视为僧众内某个人、某一系、某一宗派所私有以致互相争讼,累年不能解决,庙产的这种不确定性给佛教带来了无限的困扰。因此,早在1912年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就明确指出,“各寺庵财产无论十方捐助或自行手置均为佛教公产”[10],并就此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佛教会有监督佛教公团一切财产上处分之权,任何人不得以地方团体或原捐主子孙之名义操纵或管理寺庙[11]。但这种正当要求在当时直接遭到了内务部的反对,认为不应一概而论应具体根据寺庙的产权确定其管理权的归属问题。毫无疑问,民国初年对庙产的这种认识是整个民国时期庙产风波一直不休的重要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庙产风波愈演愈烈,为彻底摆脱庙产任人摆布的命运,佛教界再一次严正声明:庙产具有宗教集团的性质,依照法律,其管理权和收益权理应属于僧伽全体,地方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越俎代庖占据寺宇、提取寺租、处分寺产、管理寺田,非法侵害或掠夺庙产的团体或个人应送交司法机关审查,而非仅凭行政命令处理。
其次,呼吁政府对庙产实质性的保护。其原因有三:其一,僧伽亦是国民一分子,他们尽到了与世俗人同等的纳税、办学捐助等义务,自然应与普通人一样享受安居乐业的权利,政府有保护庙产不受侵犯的义务。其二,占夺庙产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相背离,与国家法律、党纲也相抵触:1931年的国民会议再一次肯定了民国初年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如果僧伽连自己的庙产都无法自由支配,不但庙产被破坏、佛教遭到无情的摧残,而且信教自由也无从谈起,“宗教将失其根据地,尚何有信仰自由之可言?”[12]再三,依照国际惯例,世界各国宗教财产皆由宗教团体自行保管,我国也不应例外。鉴于僧伽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其第17章第261条云,对于坛庙、寺观及其他礼拜所,公然侮辱者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13],并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
从表面上看,僧伽的积极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国民政府对庙产的保护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其实质是要佛教自生自灭。政府对佛教既不管理又不监督,尽管也制定了一些法案,但都属空言而成为政府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对佛教这种令文上的保护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在割据的局面下,即使南京城内都不能奉行国民政府的命令:行政院曾通令各省市,无论任何机关和人民团体不得占用寺庙,可是紧靠在国民政府府墙外的毗卢寺就不曾有一天不驻兵[14]。因此,尽管佛教界一再强调庙产为全体僧伽所公有,并积极寻求政府的各种保护,但一直到40年代,提充庙产的事件几乎遍布全国,这种情形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佛教势力,并引起了佛教界有识之士对庙产归宿和佛教自身发展的积极反思。
三、僧伽保护庙产的治本之措
佛教界的治标之举虽然在当时在改善寺僧的社会形象和提高寺僧适应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终因其局限于保护庙产的直接目的而实际收效甚微。同时,庙产风波使越来越多的佛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决定佛教盛衰的关键不是庙产的有无,而是如何对待庙产。于是,在外在的“生存”压力和内在的革新除弊的需求下,佛教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谋求自身的发展。
统制庙产。庙产的存在不但使一部分僧众好逸恶劳、不学无术,而且也从客观上阻碍了青年僧众的好学上进,庙产养成了僧伽的惰性,以致整个佛教界混乱不堪。这种状况使佛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扭转佛教界破败零落的局面,必须统制庙产,而其基础就是公开寺产及常年开支。寺产及其常年收支不公开是僧伽内部百弊丛生的根源:较大的丛林有职事——监院、副寺等象征性的监视使住持无法明目张胆地侵占,而相当一部分虽有寺田十百千顷的丛林住持却不受任何约束,以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既不开堂参禅习教又不接众挂单,所有寺产均被住持一人挥霍享受。为从根本上杜绝此种局面,巨赞指出,应将大小寺院产业公开支配,将各种僧学教育费、僧众生活费、寺院管理费、社会慈善费等种种用途的费用由各省、县佛教会另派专人管理,每年将寺产收入集结各省、县佛教会再由佛会分配各处,既可图前途之发展又可免外界之觊觎[15]。此外,组建强有力的佛教组织切实管理庙产。为彻底打破寺产私有和宗派集成的传统,真正使庙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就必须实行集产制度,“凡佛教范围内之财产、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统一机关之佛教总会公有而保护之,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除佛教统一机关之外,无论何项机关,或团体、或私人,均不能侵占而干涉之”[16]。此“佛教统一机关”必须能“通盘合作”,使全国佛教寺院皆成一系统的组织,使全国佛教徒众皆成一整个的团体[17]。总之,只有群策群力的佛教组织来管理庙产,才能使庙产不受外界的觊觎,真正为佛教的发展保驾护航,实现佛教的自我管理。
将庙产积极用于建设各项佛教事业。首先,丰富的庙产不但成为僧伽内部倾轧的因素,而且还由于忽视文化事业、福利事业等佛教各项事业的建设,而成为社会觊觎的目标。太虚大师常说,中国佛教的庙产活像一块臭肉,徒引来蝇蚁恶狗,大抵在愚僧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勾结中消耗净尽;中国佛教过去病在脂肪过剩不肯运动臃肿不灵,等到体力衰退,又积食不消,这才从外强中干演变到奄奄一息[18]。有庙产而不积极兴办各项佛教事业是庙产被侵占、佛教日益衰微的根本原因,“佛法因产而亡,僧伽因产而堕落,产为法累,产为僧害”[19]。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将庙产用于供养十方僧众“办道、宏法、利他、度生”[20]。其次,在全面的国民经济政策建设之下,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也同样是刻不容缓的。因此要合理处置庙产,一方面全面利用资源如利用寺庙附近的山、地开辟农、林场,组织僧尼开展生产劳动实现自养;另一方面开办佛教实业,寺庙的收入除了维持僧尼生活外还完全有能力举办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和佛教事业,如佛教工厂、佛教医院、佛教教养院、佛教大学等。由此,全国的僧尼才有机会成为生产者或学者,才能利益佛教、服务社会。太虚甚至还根据全国寺院的类型,分别提出了开发寺院经济的办法:山乡寺僧应就原有的山场田地,在县区联合为林场、农场或农林场;城市寺僧可就寺地所宜,集办罐头笋菜及僧衣鞋帽,或图书馆、印刷等工厂、商店;应民众需求而服务的经忏应由佛教会订立法规,整理运用,以增经济收入,同时改善风俗[21]。毫无疑问,以上措施都有利于僧伽形象的改善、佛教的发扬和庙产的保护。
提高僧伽整体素质以更好地管理庙产。统制庙产和将庙产积极用于建设各项佛教事业是解决庙产问题的重要措施,而提高僧伽整体素质则是关键。现实让佛教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庙产风波的最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僧伽本身素质的提升,即“对外对内务宜兼顾,对外是标,对内乃本”[22]。提高僧伽素质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养成高尚的僧格,端正僧伽对庙产的态度。只有养成高尚的僧格才能使僧伽认为佛教的命运与自身言行休戚相关,从而唤起其维护佛教整体利益的自觉。但事实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僧伽没有养成高尚的僧格,直接导致了僧团的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甚至违法乱纪,庙产也跟着遭殃。为改变此种局面,养成高尚的僧格和对庙产的正确态度是极其重要的,端良的人品、纯正的信仰、坚固的道心是其根本和核心。具体来说,就是要僧伽少欲知足而不过分贪求,能安贫乐道,坚守清苦淡泊的原有的佛教生活。僧伽尤其是修学的学僧不但不应以奢华的生活为美,而且更要清苦淡薄,勤苦劳动,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总之,僧伽应该打破一切奢华、虚荣名闻利养之观念,剔除种种不良之习惯,不正之嗜好,不慕荣华,不图适意,养成布衣茅舍、青菜豆腐、粗糠、粗米的简单朴素之生活[23]。
其次,养成“群”的合作精神以建立高效的组织,佛教才能真正发扬光大,庙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野客指出,正是长期以来只注重佛学、国文以及其他各种科学的灌输而忽视合作的思想和方法,致使僧伽教育所造就的知识分子,散居各地,一无联络,且互相蔑视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教授们在学僧求学时代,只晓得一意的授给佛学,国文以及其他的各种科学而忽视了灌输复兴佛教途上最关紧要的共力合作的思想与方法,因此一出校门就各谋各的前程去了”[24]。大醒说,如果学僧有合作的精神、密切的组织,佛教的状况会有很大改观,“如果有密切的组织,竖的方面不一定要有系统,而横的方面若能有一个连锁,情况也许要好的多”[25]。可见,僧伽除学习佛学和社会常识及技能外,养成“群”的合作精神对保护庙产也是极其必要的。
总而言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庙产风波的愈演愈烈,僧伽端正了对庙产的态度,认识到只有合理处置庙产才能真正使佛教发扬光大,不再局限于“保产护僧”,而是从历史大势出发,着眼于振兴佛教的根本大计。其对庙产的整理理清了长期以来的庙产混乱局面,保证了其合理的利用,为佛教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符合时代需求的,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M].台北:东初出版社,1974:142.
[2]为保存古迹而保存庙宇[J].正觉杂志,1931(7).
[3]新闻.移用全国庙产之新计划[J].威音,1932(51).
[4]新闻.内江的电灯[J].佛化旬刊,1928(108).
[5]雪烦.外侮频临与僧伽教育[J].海潮音,1936(1).
[6]法舫.实行庙产兴学[J].海潮音,1935(9).
[7]大醒.十五年来教难之回顾[J].海潮音,1935(1).
[8]含虚.谈河南僧伽生活[J].现代僧伽,1929—1930.
[9]性空.云南僧伽生活的怪现象[J].现代僧伽,1929—1930.
[10]中华佛教总会章程[J].佛学丛报,1912(1).
[11]佛教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条件[J].佛学丛报,1912(2).
[12]杭州民众上中委会电一[J].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8(19).
[13]政府护教法律之施行[J].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1(28).
[14]大醒.十五年来教难之回顾[J].海潮音,1935(1).
[15]钱诚善.佛教学务方案建议[M]//海潮音文库:第一编.北京:线装书局,2005:163
[16]太虚.上参众两院意见书[M]//太虚大师全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659.
[17]大醒.中国佛教会进行之计划[J].中国佛教会公报,1929(2).
[18]印顺.泛论中国佛教制度[M]//妙云集下编之八.台北:正闻出版社,1981:12.
[19]雷音.中佛会无理取闹[J].海潮音,1936(8).
[20]警迷严化顽.读中佛会为修改会章事致各理监事一函后之不平鸣[J].海潮音,1936(8).
[21]太虚.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A].太虚大师全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189.
[22]记者.庙产兴学停顿后之问题[J].现代僧伽,1933(1).
[23]智藏.献给全国青年学僧[J].海潮音,1935(5).
[24]野客.佛教复兴与救济学僧[J].海潮音,1937(8).
[25]大醒.我的感想——复法舫法师的一封信[J].海潮音,1938(1).
K258
A
1000-2359(2012)01-0148-04
单侠(1978—),女,山东单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2011-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