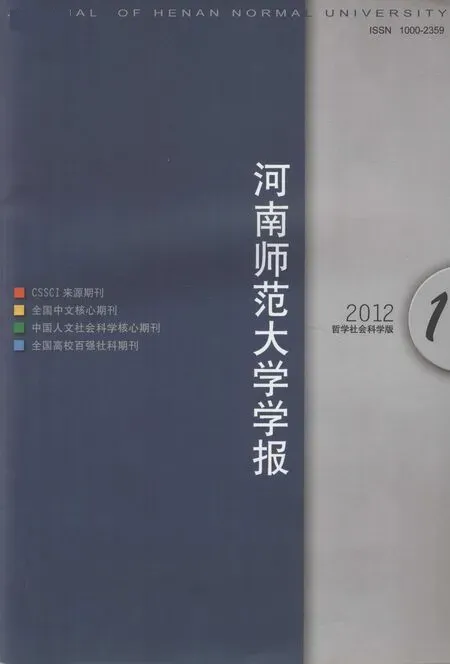法治:从形式主义到现实主义
——重读戴西的法治理论
于庆生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法治:从形式主义到现实主义
——重读戴西的法治理论
于庆生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1885年,英国法学家戴西在他出版的《宪法研究导论》中,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法治”的含义,强调法治为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和司法救济,以及人人平等守法,并主张贬抑日益扩张的行政权。权利来自司法救济,宪法不过是这种保护之“堡垒”的观念,是戴西法治概念的核心。通过研读戴西,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法治”之法律现实主义的概念,它有可能克服迄今作为这一概念之特征的形式主义困境和关于其有效性的疑虑。
戴西;法治思想;议会主权;法治国
17世纪末,在光荣革命获得胜利之后,英国人普遍相信,“法治”已然确立,个人自由因此得到了保障。正如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所言,“法律是一个人可能获得的最可靠的庇护所,是保护最弱者的坚不可摧的堡垒”[1]。然而反常的是,在19世纪末以前,并没有法学家曾试图给“法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没有人追问过“法治”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没有人探讨过英国的“法治(rule of law)”与欧陆“法治国(Rechtsstaat)”及其他类似概念之间的区别。戴西(Albert Venn Dicey)在他第一次出版于1885年的《宪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一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在这本著作中,他描述了英国宪法制度的运作过程,并将法治确定为它的主要核心。戴西的著作因其思路清晰而闻名,它是第一次以严格的法律方法来研究英国公法,而直到那时,该领域一直是以历史研究为主导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英国宪法研究的奠基之作,“人们还普遍将法治与戴西对法治的阐释当做一回事”[2]。
一、戴西论法治的内涵
戴西将法治或者法律的至上性作为英国宪法制度的一项主要特征,他认为,法治包含三个明显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主旨。
第一,法治意味着严格合法性的至高无上,政府作出的侵犯个人领域或私人财产的行为必须得到法律的规制。详言之,普通法律的绝对权威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反对专断权力的影响并且摒除专制、特权甚至政府方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除非明显违反了普通法律的明文规定,并经由普通法院通过合法程序裁判,任何人都不受惩处,其身体或财产不受非法损害。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的阐释。
第二,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平等隶属于同一司法体系。正如戴西所言,“当我们将‘法治’作为我国的一个特征谈论时,我们的意思……不仅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是指(这是个不同的问题)在这里,不论其地位与身份,每个人都受到王国普通法律的约束,都要服从普通 法院的司法”[3]114。法治原则不仅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求每个人都服从由同样的法院施行的同样的法律。在此,戴西将法律地位平等性的自由主义学说划分成了两项原则:他既坚持法律具有普遍性的传统观点,又补充说,司法也应该如此。第二项原则使得英国的宪法制度与欧洲大陆的宪法制度背道而驰,而后者通常只承认法官的权限是由法律所确立的。戴西对司法平等性的强调是他的法治概念的核心,也是他抨击行政法的工具。他指出,如果司法平等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相结合的话,官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不适当运用肯定是要被排除的。单单合法性原则并不足以保证普通法律的绝对至上性,或者排除专断权力、特权的行使。唯一的保障是由所有阶层平等地服从于由普通法院施行的国家普通法律提供的。司法平等性原则既不豁免公职人员受特别法调整的行为,也不排除特别法庭因这些特殊规定的违反,而审理那些官员。
第三,法治意味着宪法并不是个人权利的渊源,而是由法院规定与执行个人权利后产生的效果。戴西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原则,而是一项历史事实,它表现为英国普通法传统的一项具体成果,并因此成为与欧陆宪法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宪法”的特征之一。他声称,英国宪法“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法治传播开来的,即宪法一般原则(例如人身自由权,或者公开集会权)的成立缘起于司法判决结果确定了私人的权利,特别是在诉至法院的案件中;而在许多外国宪法中,赋予个人权利的保护(至少表面上)是,或者似乎是源自宪法的一般原则的”[3]115。通过强调英国宪法是普通法律的运行结果,戴西的目的是要表明,英国宪法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与欧陆的一样有效;这些权利起源上的差异只是形式上的,而与保障是否有效无关;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英国成文宪法的缺位导致了维护个人权利的困难,而是那些同样的权利受到了成文宪法不适当的保护。在戴西看来,欧洲大陆国家的宪法都专门对个人权利进行了规定,却很少注意到为那些权利提供保护的需要,以至于很多时候宪法权利不过成了完全空洞的宣言,而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并不宣告任何的原则,或者界定任何的权利,而是“为了实践的目的,用成百个宪法条文来保障个人的自由”,这突出体现了ubi jus ibi remedium(有权利便有救济)这一拉丁法谚的实践妥帖性。
从上述三层含义来看,戴西强调的法治,在形式上不外乎是: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和司法救济,以及人人平等守法。他的法治,是针对政治权力而言的,彰显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而贬抑了日益扩张的行政权。他的政治法律哲学理念,基本上是洛克式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以一个19世纪力主自由放任或个人主义原则的辉格党人的姿态重述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其研究的知识进路仍旧是自启蒙时期起为法学研究奠定基础的、源于古希腊的知识论思想传统。其研究的方法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特别是奥斯丁的分析法学[4]。
二、戴西论法治与议会主权
在戴西的宪法理论中,与法治原则相并置的是议会主权原则。戴西强调,议会主权是英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并且这是从法律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5]。对于现代法学理论而言,这两项原则之间是否兼容是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例如,沃克(Geoffrey De Q.Walker)在提到“戴西的议会主权这个含糊的教条”时,指责《宪法研究导论》“就像巨大而又丑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念碑,它耸立于法律与宪政的景观当中,并对法律认知发挥着催眠的作用”[6]。
但在戴西看来,法治和议会主权是推动英国宪法发展的两项原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抵牾,相反,法治不仅是与议会主权完全兼容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律的至上性与议会的主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强化,共同体现着英国宪法提供给个人权利的安全保障。他指出,相对于任何其他主权权力的形式,议会主权有利于法律的至上性,而严格合法性的统治地位要求运用并因而增强了议会主权的权威性。
戴西的论证来自奥斯丁的一项理论预设,即根据定义,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主权机关:那是一个其权力是初始的,而不是从任何规范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不受任何预先定义限制的机关。这一观点认为,法治仅仅是一项合法性的原则:只有一般的行政和管理机关遵守法律,它们的行为才是合法的。不过,戴西声言,代表着英国宪政基本特征的议会主权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虽然在英国已经发展起来的议会主权确实促进了法治的至上性,但是,这在所有有着议会政体的国家中却不见得是事实。在此,戴西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法治概念的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导向。英国的议会、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冲突中获得了发展,法院与议会联合起来对抗君权。这一冲突在17世纪达到了顶峰,并以议会与法院联盟的胜利而告终,自18世纪以降,一只“自由的手”便在拟定着宪政的秩序。戴西强调,这些事件表明,议会已经显现出保护司法独立性的倾向,而君主制则努力保护政府官员对其权力的行使。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议会是主权者,但它必须在行使其主权时与其盟友——法院——相一致。由这种特殊关系及其历史根源所产生的司法实践,为《宪法研究导论》中提出的法治概念增添了可信性。
为了理解戴西的推理,退回去重新审视他在法治与合法性原则之间作出的比较是有所助益的:这肯定是戴西理论中最含糊不清和富有争议的部分。戴西似乎认为,法治并不能保障任何的基本权利,它仅限于使个人免受政府强权的侵害。通过对比17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他承认,许多外国政府也并不是特别暴虐的,虽然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完全免于强权的侵害。也就是说,戴西承认,英国的独特情况并非来自其固有的美德,而是来自其政府体制的合法性[3]111。因此,法治并不直接确定可归属于公民的权利,而是局限于保证国家当局行为的可预测性,即法律的确定性。法治所保障的自由似乎是一种剩余的自由,即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事的自由。在一个权利宣言缺位,仅仅依赖法治的制度中,是不可能存在法律必须尊重的核心性基本权利的。因此,法治并不涉及一个基本的和受保护的权利的清单,而是被与纯粹的合法性原则视为一体。显然,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可能被议会大笔一挥便予以废除,而仅仅作为合法性原则的法治虽然可以保护公民对抗任意的行政行为,但不能对他们的自由提供完全的保障,因为议会保留着通过极端限制性的法律的权力,只要它愿意。事实上,这一原则只意味着,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干涉,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
应予强调的是,在戴西阐述的法治原则中,立法者消失,只剩下立法文本的观念,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它是使得法院能够施行其自主规范活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它创立了一个框架,其中,司法活动并不遵循立法者的成果,而有其独立的追求。法院不应该执行立法者的意志,而是必须将其与包含在普通法中的宪法传统融合在一起。在防止法官将法律视为立法者意志的解释规则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理解,即解释法律的法官不仅受到法院独特情感的影响,而且受到普通法精神的激励。正是法院的这种受到它们对法律文本之忠诚保护的双重态度,表现出了戴西的法治概念的长处。同样的态度中和了内在于议会主权原则中的唯意志论,并巩固了对于权利与自由的保护。法官应当按照“普通法的规范和精神”解释法律的理论,可以追溯到马修·黑尔爵士(Sir Mathew Hale):议会拥有宪法权力批准一项全新的、通常不被普通法所承认的法令,但是,批准本身并不等于它被认可为“法律”;只有当法院将它纳入到普通法,取代了原有的规则时,它才变成了“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议会主权并不意味着“制定”(produce)法律,毋宁说是“提出”(propose)法律,这些提议可能会立即产生法律效力,但此效力或许是短暂的。因此,议会虽然行使立法主权,但法官仍然是法律的主人,他们是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确立规则。
在阐释他的法治理论时,戴西回溯到了黑尔那里;但是,在确定被黑尔视为英国法之基石的普通法的原则、标准和价值时,他却诉诸自由主义的哲学。因而,戴西改变了普通法合法化的基础。普通法已经被承认为一种背景,其中,新法的成立不只是因为它表现为国法,而且还因为它保障了被自由主义传统视为基石的权利;此外,它优于任何其他的法律安排。这是隐含的框架,潜藏在戴西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自由宪政之间的比较背后。通过表明权利通常被规定在为普通法所承认的宪法当中,通过坚持它所提供的保护的优势地位,戴西将若干世纪以来英国的法律传统归结为自由主义的传统。普通法法学家虽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主义法律大厦。《宪法研究导论》在英国宪法领域的成功,以及其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便源自这一将普通法和自由主义传统相融合的努力。这一运作在19世纪末导致了普通法神话的复兴,并且不论从法律实证主义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都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戴西的法治概念与欧洲大陆的法治国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戴西的法治概念,尝试在其与欧洲大陆的法治国理论之间进行比较性评价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法治国理论的基本要素是对存在于国家主权、根本法与自由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确信,是作为获得了其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而传播的信念。这种良性循环以某些理论为核心:洛克的通过法律加之于个人自由之上的限制是自由受到限制的主体之理性自我所追求的限制的观念,或者卢梭的公意观念——根据这种观念,集体当然绝不会追求限制其任何成员的自由。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孟德斯鸠的法官是“法律之喉舌”、司法权力“价值无涉”的贵族化观念相结合。矛盾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获得了其有效性,并为一种宪政组织的理想类型注入了活力,而这种理想类型可以被界定为卢梭与孟德斯鸠观念的结合。这种模式以议会的作用为核心,并将作为立法机关的意志(因而最终是人民的意志)之忠实执行者来适用法律的角色分配给了法官。司法权基本上是一种确保议会意志得以实现的工具而已。
卢梭-孟德斯鸠模式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效力,它于19世纪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并维持其支配力长达200多年。尽管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但社会契约理论的逐步破灭导致了关于这一宪政理论之基础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自18世纪末以来,立法机关天生地保障个人自由的观念便不断受到质疑。这一认识越来越清楚,即最能保障自由的秩序恰恰依赖于也最能否弃它的主权权力。
19世纪中叶,伴随着劳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与奥托·贝尔(Otto Bähr)对国家利维坦化的努力控制,德国的法律理论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转化成了国家不同职能(行政、司法与立法)的具体规定。结果,行政国家受到了立法国家和作为法官的国家判决的控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法治国开始成为这样一种国家,即合法性原则不仅在18世纪启蒙运动所坚持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 poena sine lege)中得到了承认,而且在行政事务中也得到了承认。然而,即使是德国的法学流派也质疑了国家作为立法者的作用,即为了其统治,它只有依赖法律外的因素,如公众舆论、公民意识和国家历史来控制。即使是最精致的法治国家理论也不得不求助于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国家自我限制的理论,或者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所提出的主观公权的理论。
在20世纪初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之前,立法权力与法律之间的棘手关系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个奥地利法学家一方面确定了国家的法律秩序,消除了其任何的唯意志论色彩。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法律秩序的层级理论,并通过将宪法和法规之间的关系与任何两项不同法规的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将前者化约为需要从法律角度进行评价的一种规范。在这一框架中,议会已不再是一个主权机关,而是成了一个根据明确的宪法规范——它界定了议会需要遵守的权限和程序——活动的机关。对这些规则的严格遵守,使得法律的形式与实质正确性便能够受到法院的控制。通过在宪法与法律之间建立这种层级关系,凯尔森的层级理论(Stufenbautheorie)废除了19世纪的议会主权教条,并通过使其服从于法律限制,将立法权力置于司法控制之下。这为欧洲公法与北美宪法传统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铺平了道路。
戴西用其法治理论想要解决的难题,与长期困扰欧洲理论家的并无不同,这个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公民自由之保护与国家,特别是立法机关的主权之间的关系。戴西和大陆法学家都试图聚合起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占据了过去四个多世纪法律理论争辩的舞台:一方面是唯意志论,其最高表现是现代国家的绝对概念;另一方面是普遍的、形式的、理性主义的法律概念,亦即自由的个人权利。
戴西的解决方案与欧洲大陆的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的法治理念来自普通法的法律传统。他的解决方案削弱了欧洲大陆人认为对法治至关重要的观念。由于追随奥斯丁,戴西拒绝了英国宪法是建立在孟德斯鸠所坚持的分权原则之上,以及议会受到宪法支配的理念。戴西认为,法治是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的,因此,与德国法治国理念类似,它主要是为了限制行政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他还指出,作为一项合法性原则,法治保障了英国人的基本权利。矛盾的是,他提出,对于这些权利的保障是议会主权的必然结论。
通过戴西赋予司法权的不同职能,这一矛盾获得了解决。正是这一因素将戴西的理论与大陆的那些理论区分了开来:他断然拒绝了卢梭-孟德斯鸠模式。孟德斯鸠司法权独立的概念与戴西假定为起点的普通法传统是大为不同的。卢梭-孟德斯鸠范式赋予了法院——仅仅是有机的,虽然被认为对立法者意志之中立适用是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但是,戴西却赋予它们一种独立的规定性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正如戴西在其《十九世纪英国法律和舆论的关系》一书中所言:“一项规则的解释——尤其是在规则被作为先例来遵守的场合——很容易逐渐变成规则的延伸或制定,或者影响到规则的延伸或制定,或者影响到立法,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往往是不能明确划定的”[7]。
卢梭-孟德斯鸠模式削弱了普通法法院所发挥的维护个人权利的传统作用,它将法院的作用视为对政治权力的僭越,因为个人权利被界定为对于多数人权力的限制,被界定为对于将其(可能是专横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统治者的限制。戴西的法治概念明确反对“留声机式的”司法权力观念,明确反对法官只是重复着立法者意志的观念。他不仅赋予法院一种形式上独立的权力,而且赋予法院一种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规范性的独立权力。戴西的法治因此成为了一种“法官造法”的原则。议会立法被看做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有赖于对某些基本权利,即历史上“英国人的权利”的尊重;法官尊重通过法律表达出来的民意,因为他的“规范性意识形态”(normative ideology)体现了民主的价值(或者更简单地说,议会主权的原则)。但是,法令的合法性仅仅是表面的合法性:议会的民主性质不应当自动地说服法官去适用经它认可的法律,而不问其内容如何。法治要求,侵害了重要公民权利的形式上有效的法律,应该由法院按照自由和独立的价值来解释,按照戴西的观点,这些价值是受到普通法保障的传统价值。
可以说,传统的英国宪法产生了一种与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宪法不同的模式,而后者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基础的,即宪法认可分权,并且通过分权来保障基本权利。而权利来自司法保护(即戴西反复强调的“无救济即无权利,提供救济便是赋予权利”),宪法不过是这种保护之“堡垒”的观念,是戴西法治概念的核心。这个“堡垒”至少在原则上独立于权力分立(即使在历史上已经实现了法院的独立性),它是建立在使得法律几乎免于立法唯意志论之滥用的深厚法律传统的基础上的。
一旦被置于普通法传统当中,戴西的法治理论便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场域;今天,在这个场域中,很有可能对法治这个极为一般性的概念进行重新评价。大陆的法治国经验似乎是一次让权力受法律控制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凯尔森无疑代表了这一过程的顶峰,因为他为将立法权力置于司法控制之下的宪政工程开辟了道路。通过将重点放在实质的而不是形式的方面,法治国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将主权权力的领域与消解这种权力的个人自由的法律领域调合在一起的尝试。在19世纪,这一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凯尔森的理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形式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消除了立法机关主权的教条。在他之后,许多战后的宪法已经致力于不仅保障自由权利,而且保障社会权利。凯尔森的形式主义很快变成了一种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解决方案。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家干预的不断扩张已经使个人自由重新面临着“利维坦”的威胁。根据启蒙运动的传统,凯尔森将司法审查视为控制国家权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更确切地说,他将司法机关看做是最适合完成这一任务者,因为它是一种——用孟德斯鸠的话说——“价值无涉的权力”。司法机关仅仅是“宪法的喉舌”。戴西迫使我们从根本上质疑了这种法官作用的概念,并将重点放在与法律适用、解释技术、法律训练和文化有关的问题上。以戴西的理论为起点,我们很可能获得一个“法治”之法律现实主义的概念,它有可能克服迄今作为这一概念之特征的形式主义困境和关于其有效性的疑虑。
[1]E.Coke.TheSecondPartoftheInstitutesofEnglandContainingtheExpositionofManyAncientandOtherStatutes,3rd edn.,London:Crooke:56.
[2][英]艾沃·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侯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7.
[3]A.V.Dicey.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1915],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2.
[4]张彩凤.现代英国法治理论的经典表述——戴雪的法治观及现代批判[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2(1):70-77.
[5]邹利琴.无涉道德的宪法——重读戴西的宪法理论[J].当代法学,2005,19(3):20-26.
[6]G.De Q.Walker.Dicey’sDubiousDogmaofParliamentarySovereignty:ARecentFraywithFreedomofReligion,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1985,59:283-284.
[7]A.V.Dicey.LecturesontheRelationsbetweenLawandPublicOpinioninEnglandduringtheNineteenthCentury,London:Macmillan,1914:491.
[责任编辑 张家鹿]
DF091
A
1000-2359(2011)01-0081-05
201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