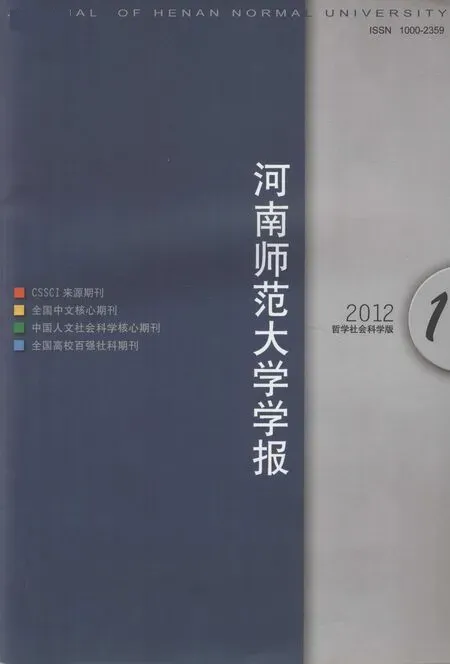恐惧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张玉龙,陈晓阳
(1.山东大学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012;2.滨州医学院,山东 烟台264003)
恐惧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张玉龙1,2,陈晓阳2
(1.山东大学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012;2.滨州医学院,山东 烟台264003)
恐惧在现代生命科技的强势和暴力环境中,可以促进理性认知的形成,从伦理上化解技术和生命的尖锐矛盾。恐惧导致对技术与道德的冲突产生焦虑,形成对工具理性和人性的反思,推动对生命伦理重大命题的解读。以恐惧为基点,可以明确生命伦理体系的新颖方法、核心规范、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
恐惧;伦理;价值
现代生命科技已经嵌入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给人类带来福祉、展现希望曙光的同时,也使得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陷入高风险的漩涡,使传统伦理受到严峻挑战。生命伦理学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审思技术,探索为人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提供持久的道德力量,其理论和实践研究空间的构建也正在进行之中。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1]由害怕、恐惧开始,伦理学这颗参天巨木,繁盛出生命伦理之花。
一、恐惧在现代科技环境中的新价值
恐惧作为一种只有人类及生物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状态,是由于周围不可预料不可确定的因素而导致的无所适从的心理或生理的强烈反应,是只有人与生物才有的一种特有情绪,是生存的本能表现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有机体企图摆脱、逃避某种情景而又无能为力的情绪体验。拉斯·史文德森认为:“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情绪就是恐惧。”[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认为恐惧作为现身情态就是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克尔凯郭尔《恐惧的概念》则认为恐惧是“单独个体”最基本的存在状态。
作为一种只有主体才能体验到的感觉,恐惧往往具有描述性而非分析性,对其精确定义比较困难。与恐惧相关的词语,如忧虑、担心、焦虑、害怕、恐慌、畏惧等可以辅助完成对恐惧的说明,大致勾勒出恐惧的构成和内容。一般来说,恐惧的产生源于主体被迫置身于无法安然地相信世界、时刻面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严峻的生存境遇中,往往与死亡、无知相伴。伊壁鸠鲁认为恐惧的两大根源是宗教与怕死;康德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感到畏惧,战战兢兢;在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说中有“毁灭和终结是人类恐惧产生的源泉”;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的恐惧,其一是对于头脑中假想出的,或根据公开传说构想出来的对于不可见的力量的恐惧,这是宗教的来源,其二则是一种由于对原因或者状况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恐惧,这被称为恐慌(Panique Terror),他并指出最初的恐惧来源于对于原因和状态的未知;克尔凯郭尔说,“虚无具有什么作用?它激起了恐惧”;海德格尔认为“畏与怕有着亲缘关系,这两者现象多半是不分的,是怕的东西被标示为畏,而有畏的性质的东西被称为怕[3];按照英国神学家詹姆斯·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德国的斯宾格勒在《悲剧主义》中说,人对他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最感到恐惧,分为时间恐惧、空间恐惧。可以认为,所有类型的恐惧都往往由处于危险或面临着危险的感觉而来,人们对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险丧失了控制力,既不能对危险事物作出有效的预见,也对行将到来的危险失去抵御能力,无力摆脱危险的局面。总之,在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却无法控制时,恐惧才具有存在的基础。
恐惧是人类在大自然中饱经困苦和不幸的最初反应,并贯穿于探索自然和生命奥秘的人类文明始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中,对于恐惧、敬畏都有着深入的论述。古希腊意识中的天命作用和古代人面临天命所体验到的恐惧,被历代哲人所关注。有研究表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会把恐惧某种东西的信息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4]。近现代以来,当神学桎梏被打破,对地狱的恐惧感消失,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却发现没有了上帝的世界充满了不安、忧虑和恐惧,为此,保罗·纽曼无不沮丧地说:“尽管旧的神灵抗衡罪恶的宇宙存在问题,但是生活在一个无神灵的宇宙却让人胆怯。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炼狱、没有监狱、没有永恒的生命,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使得罗切斯特大人血管冰凉、让克尔凯郭尔感到战栗、使让·保罗·萨特感到恶心。”[5]凡·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理论体系表达了人类是如何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经受了战争、种族灭绝、极权统治、核爆炸等重大社会事件,被视为恐怖的时代”[6]。在后现代的境遇中,人的不安全感是多重面向的,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焦虑、恐惧、孤独、寂寞、失落、悲伤等等[7]。比如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关系不仅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也使得陌生人社会充满了更多敌意。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熟人社会的领域不断缩小,被称为陌生人社会的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社会中生活并相互交往,恐惧和不安便愈加严重。
在上述宏观背景中,现代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发动机,对整个人类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现代技术已不仅仅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对于社会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权力存在”[8]67。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减轻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程度,却也同时形成了新的恐惧来源。人类自身对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价值或效应不能完全科学地预测。技术在暴力性窥探自然、对物质内部直至生命存在最隐秘部分进行特定意向性改变的同时,也按其自身逻辑对抗着人性、人权、人伦关系,从根本上冲击隐藏在既有交往关系及其秩序中的伦理关系、伦理秩序与伦理观念。有人从技术心理反应角度分析这种恐惧,提出了技术恐惧(technophobia)概念,即对技术对于社会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与之相关联,对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安全感的普遍缺乏,也开辟了从风险视角透视当代社会的新视域[9]。
在从伦理上解读技术和生命的尖锐矛盾方面,恐惧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德国技术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深刻地指出:“过去,恐惧在情感中威望不高,它是胆怯者的一个缺点,现在它必须受到尊敬,对它的崇拜简直就成了伦理的义务。”[10]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恐惧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是伴随认知活动而产生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是人类实践理性的特殊存在样式。人存恐惧,可以促进理性认知的形成,面对某种重大变迁,就不会贸然行事,就可以确立对神圣事物或力量的信仰与敬畏,以警示、约束人类的言行。孟德斯鸠说,“怕”的结局是“静”,基于对未来的恐惧,人类就会变得不再卤莽,而是小心谨慎地行事,肩负人的世间责任。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具有传递性,因而具有公共性或者普遍性,这样的普遍存在的恐惧之心,赋予人类以善良的品格、美好的德性,使人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而是在恐惧的警示静思中建造并维护自身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恐惧,成为生命伦理大厦的基点。
二、恐惧:生命伦理体系确立的基础
随着1953年DNA结构的发现,分子生物学成为生命科学的带头学科,20世纪70-80年代基因工程开始转化为生产力,1990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进入21世纪,蛋白组学、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等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进入生命科学世纪。生命科技在促进社会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引发出一系列复杂且相互关联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难题,诸如生命科技创造有害物种,生物芯片技术、纳米传感侵犯个人隐私,人工辅助生殖打乱传统人伦关系,胚胎研究引发人权争论,器官移植和克隆导致人的价值和尊严重估,等等。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古老的伦理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承担起价值批判、造福人类、引领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并获得新生。霍布斯在《恐惧的概念》中说:“身体的恐惧是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恰当起点。”从恐惧开始,可以梳理出生命伦理学内在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若干层面,从而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各种价值判断的冲突,以此确立理论基础。
(一)恐惧导致人类对技术与道德之冲突产生焦虑
恐惧情绪具有适应、组织和信号等功能,面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塑造的恐惧世界,我们感受到的强烈信号和最大困扰首先是对技术终极目的的困惑和迷茫:技术的发展目的、服务对象、对人类的利害关系等都不断引起巨大争议,技术能否在终极意义上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仍旧得不到准确的答案。其次就是对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的质疑:无论是道德的价值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的探讨,还是道德本身是否需要变革论证,都成为恐惧背景中的讨论焦点。最后就是对技术和道德双边关系的不解: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技术与道德何以相互依赖和谐共处又何以彼此独立各具合理性,这些广泛而深刻的焦虑,是我们接近科学生命伦理体系大门的开始。
(二)恐惧形成对工具理性和人性的反思
焦虑和恐惧,不断澄清人类禁忌和警示的界限,促进人类自省,将生命神圣再次提到了绝对的高度,于是“敬畏伦理”开始发挥作用。“敬畏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对自身终有一死之命运的反思,亦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焦虑的一种文化方式,更是人类面对各种困境而产生的生存智慧”[11]。对生命的敬畏,引发了对人类现实和终极命运的双重关怀。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历史形态的)技术规定了人性、人的本质的基本内容”[8]63,生命受时空的限制具有很强的尺度性,其质量高低受限于工具理性与人性的关系,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存在关系的调和程度。因此,只有明确现代生命技术中人权的边界,解决诸如克隆是否侵犯人权、基因增强是否合乎人道等问题,才能为解决新技术时代的焦虑提供线索。在终极意义上,人类在通过现代技术获得空前自由能力的同时,又高度依赖于技术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原有的自由,甚至还有可能失去尊严,这是人的存在悖论。人类不能预测和减少技术的负面价值,不能控制世界,将对自身的终极关怀寄托在自由、理性、科技等价值和理想之上,无异于南辕北辙。承认和理性对待这一悖论,将使生命伦理的认知进入一个深刻的层次,将为其理论构建指明方向。
(三)恐惧推动对生命伦理重大命题的解读
恐惧是一种不幸的状态,在恐惧中面对生命更容易激起对“善”和“幸福”的追求,克服功利主义和后果主义的不利论调。在恐惧中体味生命自身的力量,激发对生命的神圣拷问,有理由成为创构生命伦理体系的坚实起点,为人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提供一种持久不衰的道德力量。
在恐惧中,我们自然就会认同人类存在着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就会尊重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主体并存的现实,也必然会思索生命本身,特别是与生命创造、完整和健康相关的重大命题。关于生命创造,在恐惧和敬畏态度下,人们将会深思熟虑,反复论证,明确生与死的权力,解决好克隆人、安乐死、堕胎和用人的胚胎的争议,回答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研究人究竟是否具备创造人类生命自身以及为人的生命进程立法的权利与能力。关于生命完整,在对技术的恐惧中,人们将尽力解决涉及基因、生物芯片技术纳米传感侵犯个人隐私问题,维护人的尊严、平等与自主自决权。关于生命健康,在恐惧和敬畏中,人类将寻求改变和改善人类自身质量的规律,更新生命、疾病、健康观念,从而对医学或生物医学技术与疾病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和回答。
三、以恐惧为基点的生命伦理展开路径初探
在恐惧中,我们焦虑技术与道德的冲突,反思工具理性和人性,解读生命伦理重大命题,以此开始研讨和构建生命伦理体系,而首要的就是方法问题。关于方法,约纳斯提出了“恐惧的启迪术”(Heuristik der Furcht):面对现代科技能力可能招致的人类的彻底毁灭产生一种恐惧感,将驱使我们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尽可能避免风险。“恐惧的启迪术”的实质就是帮助人们在技术时代里去测度技术的力量及其威胁,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体地位和意义。这种方法指导下的生命伦理体系,在时刻警觉技术文明本身危险的同时,主动思考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承担对自然和未来的责任和义务。
以恐惧为基点,生命伦理构建的核心指向就是规范“能做”与“应做”。对于“能做”与“应做”,康德有过终极性追问,在现代技术的恐惧中,必须体味这个终极性问题的刺激性与震撼力。一方面,以恐惧为警示和启迪,要明确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在其现实性上具有有限性。人类往往自以为是为自身造福,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必须对自身的自信持有某种警惕,并对现代技术本身存有某种警觉,为“能做”划界。另一方面,以恐惧为警示和启迪,要重新审视道德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人具有自由意志特质,且这种自由意志必定要通过行动、做,超越其纯粹抽象主观性而成为现实存在。技术是人的自由意志超越纯粹主观性而成为现实客观存在的方式。美德不仅不拒斥手段、技术,甚至还内在地要求有恰当的手段与技术。伦理学理论应当充分关注实践智慧、实践理性,为“应做”立范。
以恐惧为基点,我们可以确定生命伦理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共生共存、公众参与、程序(规则)正义。所谓共生共存,就是在恐惧中由关心自己的生存发展到关心他人的生存发展,由关心人类的生存发展到关心万物的存废,在处理生命伦理难题的过程中,共生共存具有普遍价值,具有神圣性,是第一位的原则。所谓公众参与,就是说,恐惧带来对生命高科技的理性,在尚不明确实施新技术对生命及人类未来的利弊影响之前,除了伦理审查、纯粹技术领域关于技术本身成熟性与局限性的专业讨论外,还应当通过广泛公共讨论、公共对话的方式形成某种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某些规范性调节,使技术有规范地发展与应用。所谓程序(规则)正义,就是在公共参与、多元对话、伦理审查中都需要有规则,有规则的权威以及对规则的尊重。
以恐惧为基点,构建和实施生命伦理,最简单地说,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人类自身伦理的建设。要培育生命技术过程中的人道、博爱、责任精神,使现代技术人文化,培养和提高生命技术发明家、使用者(如公众等)和观察者(如技术评估和评论家等)的伦理素质。二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理性精神的建设。要对公众开展生命技术伦理教育,制定技术发明及其应用规范和准则,建立由公众参与的技术评估或评价机制。
[1]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M].公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7.
[2]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M].范晶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64-165.
[4]佘继祥.恐惧的发生及理解与心理治疗[J].临床身心疾病杂志,2008(6):545-546.
[5]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M].赵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8.
[6]贺海仁.免于恐惧的权利:不幸的哲学及其他[J].清华法学,2009(4):40.
[7]林丽珊.后现代社会的“不安全感”析论[J].警学丛刊,2007(7):87.
[8]高兆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伦理问题[C]//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9]何小勇.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科技理性批判[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1):10.
[10]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4.
[11]郭淑新.敬畏伦理初探[J].哲学动态,2007(9):22-23.
[责任编辑 张家鹿]
Study on Ethical Value of Fear in Modern Life Technology
ZHANG Yu-long,et al
(Medical Ethics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China)
In powerful and violent environ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fear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ational cognition,resolve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ife from the ethical.Fear leads to anxiety about technical and moral conflict,forms the reflec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human nature and promo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jor propositions on the bioethics.With fear as the starting point,it can define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bioethical system,the core specification,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means of realization.
fear;ethical;value
B82-058
A
1000-2359(2012)01-0061-04
张玉龙(1976-),男,山东沾化人,滨州医学院讲师,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文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陈晓阳(1955-),男,博士,滨州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研究项目(09YJAZH050)
201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