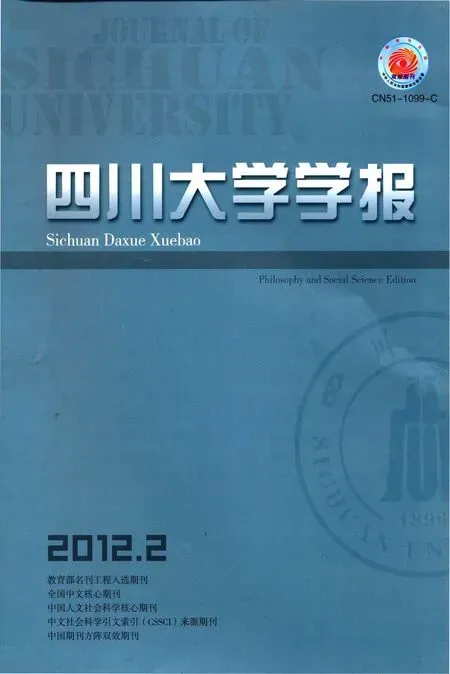“元语言”观念考察及其对文艺阐释活动的价值
伏飞雄
(宜宾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在当代学术界,“元语言”观念已在很多学科得到应用。然而,人们对其所作的理解却不太一致。那么,“元语言”观念都有哪些基本的信条?人们对其作“泛化”理解与应用的观念基础或渊源是什么,是否有其合理性?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文艺阐释活动到底借用了什么样的“元语言”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例证的方式,强调了“元语言”观念在文艺阐释活动中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追问的价值。
一、哲学“元语言”观念
现代“元语言”观念早于“元语言”概念出现。L.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18年定稿)中明确地表达了类似观念:“任何命题都不能言说自身,因为表达命题的符号不能包含在这些符号自身之中 (这就是整个‘模型论’)。”(3.332)为什么“表达命题的符号不能包含在这些符号自身之中”?我们可以从他对“符号的定义”、“符号的定义与命题的关系”的理解中看出来:“任何一个特定的符号都意味着:它的定义都要借助其他符号才能完成,而定义则显示出定义由出的方式。两个符号,一个属于初始符号,另一个则是通过初始符号定义的符号,它们不能以相同的方式标记。不能用定义的方式对名称进行拆分。任何符号都不能单独具有意义。”(3.261)“初始符号的意义通过解释得到说明。解释就是包含着初始符号的命题。因此,只有当这些初始符号的意义已经得到理解时,这些命题才能得到理解”。(3.263)①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by C.K.Ogden,New York:Barnes&Noble Publishing Inc.,2003,pp.33,27.这种观念在罗素1920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做了更为明白的表述:“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每种语言都有着自己的结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在自身范围内对自己的这种结构进行言说。但是,可以有另一种语言来处理第一种语言的结构,这另一种语言自身又具有一种新的结构。语言的这种层级体系 (hierarchy)可以无限推衍。”②B.Russell,“Introduction,”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pp.xxxiii-xxxiv.应该说,维特根斯坦这种从“符号系统的原则” (罗素语)讨论“命题”的方式,对20世纪西方分析哲学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讨论命题陈述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所蕴含的“元语言”观念,成为后来相关讨论的基础。
明确提出“元语言”概念的,是20世纪波兰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A·塔尔斯基。在其先后发表的《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 (1933年,其主要思想1929年业已完成)、①Alfred Tarski,“The concept of the formalized languages,”in 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Indian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3.本文参考了张祥龙与陈嘉映两位先生的论述。张祥龙:《塔斯基对于“真理”的定义及其意义》,2009年11月1日,http://www.scuphilosophy.org;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5-278页。《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 (1944年)②A·塔尔斯基:《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见A·P·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两文中,塔尔斯基从解决“说谎者悖论”入手,以形式语义学的方式讨论了真理的定义问题。在他看来,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使用“语义上封闭的语言”表达命题:这种语言在自身内部断定自己语句的真值。为此,他建议在讨论真理的定义或任何语义学问题时禁用这类语言,而代之以他区分出的、居于不同语言层次、具有不同功能的两种语言:“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对象语言”是被提及的、作为讨论对象的语言,“元语言”则属于讨论第一种语言即“对象语言”的语言——它既包含了对象语言之表达式的名称,又具有对象语言所没有的语义学的词项 (实为更高逻辑类型的变项),因而“本质上更丰富”。这样,“对象语言”所构造的语句的真假,就可以从语义角度用“元语言”来进行定义。在此基础上,塔尔斯基还对“元语言”做了进一步区分,即“句法元语言”和“语义元语言”,前者只谈及“对象语言”的语言表达式——涉及原始符号、形成规则、变形规则等,后者既涉及对象语言的语言表达式,而且谈及这些表达式所涉及的对象,比如语义中的真假、普遍有效性等。正是由于以具体例子作论证,塔尔斯基的“元语言”观念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元语言”观念就不显那么抽象与令人玄惑。这种例证使他首次明确提出的“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以及运用此区分从形式 (逻辑)语义学立场研究现代数理逻辑中的“意义理论”的方式,奠基性地影响了20世纪逻辑学界、语言哲学界、语言学界。
在“元语言”观念的演变发展中,美国现代语言哲学家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把塔尔斯基逻辑论的真理语义论提升至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理论;③陈嘉映:《语言哲学》,第275页。第二,他一改弗雷格 (F.L.G.Frege)、塔尔斯基等现代数理逻辑学家拒斥“自然语言”(“日常语言”,具有意义、文法特性,结构繁杂、不规则与用法含混)、仅仅处理和企图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形式化的逻辑语言)的传统,而致力于建构一个适合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理论,“一种意义理论 (从我所理解的那种稍稍不同于惯常理解的意义上),是一种经验理论,它的抱负是对自然语言的运作方式做出解释”。④Donald Davidson,The essential Davids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p.161.另请参阅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对戴维森“意义理论”所做的发展。这无疑使他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论析了“元语言”观念。从为自然语言提供意义理论的目的出发,他对塔尔斯基的“T约定”作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对象语言之语句的意义,是由元语言中的语句给出的,后者就像一本释义语言手册。更重要的在于,在为意义理论寻求“一套方法”的过程中,他在很多文章中已经把对语句意义成真 (实际上也就是对陈述语句的意义的解释)的论据基础的论证,推进到言语行为的层面:言语交流的语境——包括其中的非语言行为,言语交流中陈述者的意向、信念,解释者的知识、能力等方面。这就是他提出的“原始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观念,它涉及到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的话语的解释”,它不仅发生在同种语言之间,也出现于不同语言之间(类似翻译)。
另外,我们还可以提到歌德尔 (Kurt Godel)1930年代提出的“不完备性定理”:“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相容的形式系统中,存在着不可判定命题,即命题本身和它的否定在该系统中都不可证”(第一定理);“一个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在该系统内是不可证明的”(推论)。①朱水林编:《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页。有学者对此做了更为通俗的表述:“如果一个描述系统是自洽的,那它就是不完备的;如果它是完备的,则是不自洽的。”②《和谐关系哲学丛书·总序》,2008年11月21日,http://blog.sina.com.cn。正是由于它对现代形式逻辑之形式科学化理想的致命颠覆,使它成为现代“元语言”观念最为充分的表达。
显而易见,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对“元语言”观念的发现,内在于西方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逻辑,对其所做的论证,自然也内在于自身学科的新旧传统。简言之,他们基本是从形式或逻辑语义学角度进行论证的,主要服务于命题语义逻辑结构的分析、语句语义真值条件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颇具认识论、本体论意义的论证使得“元语言”观念完全确立了起来。
二、符号学“元语言”观念
西方现代符号学对“元语言”观念的论说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与言说方式。尽管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思想中所蕴含的“元语言”观念,绝对早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思考,我们还是愿意把他放在这部分来说。因为,尽管皮尔斯的基本思想已经得到哲学界的广泛承认,并把他视为西方现代逻辑重要先驱之一,但他的主要影响,还是在符号学界。或者说,学术界热衷讨论的,主要还是他的符号学思想 (相对狭义上的,在他那里,逻辑学也是符号学的分支)。他无可置疑地被看成西方现代符号学两大奠基人之一。与作为语言学家的索绪尔基本研究“语言符号”不同,作为哲学家的他,完全是从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研究所有的符号现象,从而建立了全面、基础意义上的符号学体系。相关于本文论题,是他的“符号过程”三分法所蕴含的“元语言”观念。确切地说,是其中的“解释项”部分。③参考卢德平:《皮尔士符号学说再评价》,2010年3月1日,http://www.semiotics.net.cn;赵毅衡、傅其林、张怡主编:《现代西方批评理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在皮尔斯看来,再现体、对象 (object)、解释项,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意指过程”。为不囿于人世纷繁万千的“对象客体”(具物理属性的存在体或纯观念性的存在体)——不为其所缠所累,在人类为提升自身所建构的具深层认知机制的认知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抽象替代(代表、表现、提喻)功能的符号,即用符号替代“对象体”;但符号的“意义”不等于“对象体”,它是“符号所引发的思想”。④参考卢德平:《皮尔士符号学说再评价》;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而这种“思想”,必须通过解释才能完成—— “解释项”由此而设立。换言之,必须要有一个“解释项”来完成符号意义的解释。相对于某一具体符号这个“常量”而言,解释项则是一个“变量”。这里的“变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人们在听到或见到某一符号比如“狗”(皮尔斯的例子)这个符号时,虽然能凭借自己的知识意会到这个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并对这种对象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能确定知道这个符号(词)究竟指哪条狗、哪种狗等等。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和知识结构,同一个人因不同的语境,都可能对这个符号有不同的反应与认知。简言之,人们对一个符号的“意义”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因知识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 (这当然更说明符号意义需要解释)。第二层意思是说,解释项对符号的解释是一个开放过程:一个解释项开始了对符号的解释过程,另一个解释项又继续解释前一个解释项,依此不断推演下去。从而,符号不断被“衍义”。
我们之所以说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包括他对这个概念的反复解释)蕴含着“元语言”观念 (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如此展开自己的论述),仅仅是因为:既然一个解释项需要一个新的解释项对其做进一步的解释,就说明这个新的解释项的出现有着必要性,其在解释原始符号的效力上优于前一个解释项——也就优于前一个解释项对某符号的解释;既然展开一个新的解释项,就展开了一个新的符号过程,那么,这个新的符号过程所内含的语法规则、释义规则等就更基本于、或者至少包含了前一个解释项的语法规则、释义规则等等。符号本身不能自我解释其意义,一个解释项本身也不能自我解释,无论是哲学的逻辑语义学论证,还是符号学对符号意指过程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解释项所内含的符号解释的“无限衍义”,还不仅仅是指符号意义解释的历史变迁与累积。另外,解释项不断推衍的观念也可看出“元语言”概念的相对性。
雅克布森是符号学发展史上较早明确提到“元语言”观念的符号学家。从对他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元语言”(meta-lingual)概念的。他首先认为, “元语言并非只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才能使用的一种必要的科学工具,它在日常语言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Style and Language,New York:Willy,1960,p.356.该文1958年曾作为一次语言学会议的总结性演讲首次出现。由此,他完全从日常语言符号传达与接受的角度,来讨论“元语言”观念。在他所提出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图式中, “元语言”就是“谈论语言本身”(speak of language)的语言。浅显地说,就是在言谈中,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符号 (code,又译“信码”)本身。他举例提到了电话问答中说话人对符号通道是否畅通的关注,以及人类 (尤小孩)学习语言时事实上的“元语言操作”。在他看来,人们在这样的语言操作中,包含着元语言特征。另外,他还认为, “元语言”就是对语言本身作“注解”(glossing)。而符号的这种“元语言”特性和功能与其“诗性”特征及其功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运用组合建立一种对等关系”,后者“则是运用对等关系达到某种组合”。②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Style and Language,p.358.
综合雅柯布森并不系统的说明,我们可以对其“元语言”观念作这样的概述:第一,“元语言”观念主要指语言本身的编码规则——他举了喜剧作家莫里哀笔下人物约尔旦用“散文”说话却不知道在用“散文”的例子 (文类体裁表明了某种类型的语言编码规则);第二,元语言解释对象语言—— “这个sophomore落榜了”,就是对“落榜”、“sophomore”及这个句子本身的意义的一步步解释。后面的句子解释前面的句子。这一点倒暗合皮尔斯对“解释项”的理解。
总结以上两人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他们是从人类符号意指过程这个基础层面来建构他们的符号学体系的 (尤其是皮尔斯),并道出了所有符号意义解释的基本特性,而不是仅仅要用“元语言”去定义真理,或检验命题的真值,因此,无论是雅柯布森对“元语言”观念之直接简单的论述,还是皮尔斯的“解释项”所内蕴的“元语言”观念,都更具基础性,因而更具普适性。
中国当代符号学学者赵毅衡在融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符号学诸家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元语言”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对“符码”的认识中发掘出“元语言”现象。“符码”涉及到符号单位及其编码规则,于是也就涉及到“作为解释规则的形成方式,即元语言问题”。当然,“元语言”不等于符码,它是符码的集合。因为,符码是个别的,它必须成套出现或形成体系才能起到解释符号文本的作用。反过来说,任何符号文本意义的解释都离不开元语言。第二,在人类文化活动的符号特点与元语言的关系中探索“元语言”在解释符号文本意义时的具体情况。同一个人、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符号文本,使用的元语言都不固定。尤其是,人们在每次解释符号文本时,可以调动不同的元语言,从而组成一个“元语言集合”。这个概念远比符号学界通常所说的“联合解码”贴切明白。第三,在深入认识元语言之间的关系中,首次提出了 (分布性的)同层次元语言(“元语言集合”)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可能构成的冲突,即“解释旋涡”。③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27、228、236-237页。应当说,这种认识完全打破了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西方符号学只谈“异层次”元语言“层控”关系的解释框架。此外,他还深入讨论了元语言的构成,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解释者能力元语言”及“文本自携元语言”的概念,并对元语言的标记、元语言在解释文化艺术符号活动中的一些可能情形做了颇具洞察力的分析。相比于上文两位久富世界声名的符号学家的相关论述,赵毅衡从人类整体文化进行思考的进路,更具系统性、全面性、普适性,对种种文化现象也更具解释力。
三、对“元语言”观念的泛化理解与运用
实在说来,现代语言学、教育学、翻译与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或领域基本只是在“泛化”理解的基础上借用“元语言”观念,进而从自身学科层面上展开具体的实践操作。撇开人们对“翻译”的宽泛理解不说,翻译领域所借用的“元语言”观念比较直接单纯,即直接借用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二项式,有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味——翻译领域元语言现象突出,它往往成为西方现代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例证或阐发其“元语言”观念的基本领地。从具体操作来看,主要是分析异质 (异种)语言符号书写的文化文本之间的翻译问题。因为这种翻译自然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元语言构成方式及解释规则的转换 (这种转换带来了意义解释的变化),涉及到元语言标记的保留对于对象语言文本意义的有效阐释。①封宗信:《文学翻译中的元语言问题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其他学科所借用的“元语言”观念,基本呈“合取”状态,即“元语言”观念与“元意识”的“合取”。②中国学术界一般使用的是“元思想”这一术语,我们则主要把它看成一种思想进路或观念取向,故使用“元意识”这一概念。
说到“元意识”,不少学者都会提到德国现代著名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1920年代所创立的“元数学” (metamathematics)。的确,自从他开创“元数学”以来,不少传统学科都受到启发,纷纷在自己学科名称前加上“meta-”这个前缀而成为“元哲学”、“元物理学”、 “元心理学”等“现代学科”。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元意识”完全是从希尔伯特开始的。的确,希尔伯特在学科定位层面的“元意识”对后学之直接、显性的启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的“纲要”在1930年代就遭到了歌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的致命颠覆。但是,起作用的还有隐性的“元意识”。
在我们看来,以塔尔斯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所讨论的“元语言”观念本身,就内含“元意识”。这完全可以从它与希尔伯特的“元数学”在问题意识上的相通之处看出来:都在追问基础理论论证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所谓“元数学”,就是把数学理论本身作为数学研究的对象——旨在“绝对证明古典数论、解析学及集论 (适当地公理化后)的无矛盾性”,即主要证明理论中命题、定理的无矛盾性。③S·C·克林:《元数学导论》,莫绍揆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8页。也许, “元语言”观念所内含的“元意识”被“掩映”于对“元语言”观念本身的讨论之中。但从整个西方现代 (数理)逻辑的思想进路来看,其“元意识”取向并非绝对亚于“元数学”。毕竟,20世纪前后的西方学术,都有着共同的“追问理论前提、基础本身”的学术语境:一直潜存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之“基元”追问的“元意识”,复活、纵横于“解构”与“建构”之间。在中国,不少学者也自然而然地把“meta-”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元”与“初始”观念结合起来。用“元~”来翻译,就绝妙道出“道”之精义。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明白以现代语言学为代表的一些现代学科“合取”或者说混用“元语言”观念与“元意识”的思想渊源。之所以说是“大致明白”,还因为这些现代学科还借用了“元数学”与“元语言”观念研究共同使用的具有“元意识”的操作方法。他们都企图用有限的技术化的形式符号,也就是“元符号”,去建立公理。克林就这样说到“元数学”形式符号的特性:“在结构上,形式符号表与通常语言的字母表相似。”④S·C·克林:《元数学导论》,第70页。的确,从经验上说,人类已发现了在人类语言或符号系统中,自有一些符号一直以来起着“元语言”的作用。从观念上说,它已为莱布尼茨的“人类思维字母表”及洪堡所强调的词汇与语法中“总是存在着所有语言围之旋转的中心”等所开启。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学科首先借用的,还是“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这个最基本的二项式,并把这个二项式的相对性,或者说“元语言”这个概念的相对性作了极大的发挥。西方语言学界值得一提的是安娜·韦日比茨卡(A.Wierzbicka)。①张喆、赵国栋:《韦日比茨卡和她的元语言思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她把建立普遍语义元语言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一方面,她努力探求语义初始单元,以数量有限的基础词语的简单语义要素去描写意义;另一方面,她试图用普遍意义子集去描写自然语言词汇和语法。后来她的研究工作还发展到为不同语言之语义结构差异寻求“文化原型”。受西方语言学界相关研究工作的影响,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在“元语言”研究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有益探索,比如苏新春、李葆嘉、安华林等人。他们多把“元语言”理解为一种语言中最基础的语言,相当于“根语言”。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写“元语言词典”方面,希望建立能定义其他自然语言的基础词汇。计算机领域,也基本是从“根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并建构“元语言”的。教育学领域的“元语言”研究,则主要探索人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元语言现象。因为,人们 (尤其是小孩)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元语言规则内化的过程。
四、“元语言”观念与文艺阐释活动
与其他学科一样,中国文艺学也是在对“元语言”观念、“元意识”作泛化理解的基础上“合取”借用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文艺文本意义所作的“文学人类学”的解释方面。“空”、“道”、“性”、“昆仑”、“气”、“葫芦”、“生—死—生”等,都成为他们所讨论的“元语言”观念或元意识的对象。②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萧兵:《张艺谋电影与人类文化元语言》,《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承继上文的相关考察,我们认为,他们的论述是值得肯定的。人类发展至今,也确实塑造与积淀了一些基本的“文化元语言”——也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原始文化意象”或“文化原型”。它们渗透到包括文艺在内的所有文化符号体系中,对它们意义编码与解码起着基础的、甚至意义阐释的定向与“归源”作用。我们的问题是,混合了“元意识”的“元语言”观念,对于文艺阐释活动来说,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只例证性地给以说明,以求抛砖引玉。
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文艺属于一个异常特殊的领域。文艺符号的弱编码方式,导致其符号意义解释的极端复杂性。但其意义并非可以随意解释。尽管“元语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并非相对得没有边界。元语言集合中种种元语言与某对象语言之间的关系远近,倒是检验元语言解释对象语言效力的方式。
“文化转向”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热闹的话题。我们到底该在什么层次上来理解文艺研究中的这种转向呢?我们以为,如果把整个文艺活动(所有的文艺符号文本)看成对象语言,那么它最直接的元语言就应该是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因为,文艺符号系统自有一套在“成规”中(相对区别于其他文化符号系统的“成规”)形成的意义生成机制,即编码与解码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文学元语言本身,即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③值得一提的是郑一舟的《试论作为一种元语言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一文 (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作者以结构主义诗学为例,探讨了文学批评、作品、诗学三者之间“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关系的转换,这种转换带来了它们的不断自审与重写。那么,文化研究在文艺阐释活动中到底居于什么层次呢?正如赵毅衡所指出的,“无限衍义的最后就是‘整体语意场’,即文化”。④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08页。这个“最后”一词倒也贴切地指出了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中的位置。当然,这并非是说,文艺是一个绝对独立、封闭、自在自为的领地,“文化”仅仅只属于解释它的最后的元语言。文化转向出现本身,文艺史上所谓纯而又纯的文艺研究走向死胡同的先例,都说明“文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伴随文本”,在文艺符号系统的建构中,处处有着它的身影。但是,无论如何,文艺元语言自身的建构规则、解释规则,它的元语言标记,都要求我们努力探索文艺阐释活动自身。同时,在我们看来,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文学性”的追问、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文本结构的探讨等,还是形式论一项未竟的事业。
再来看看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中国现代美学。它把美分成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领域,即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本来,美与丑相对。同时,美又与真、善相区别。但是,从事实上说,善的元语言,即“道德元语言”,成了“社会美”立论的基础——即“定义”它的最基础、最直接的元语言。人是伦理的动物:伦理是人性之基础,也是其终极目标。然而,对于与善相区分的“美”这个范畴来说,善、或者说“道德元语言”只是其最终的解释元语言,也就是说要归化到它。换言之,“道德元语言”首先是用来解释善的。那么,社会美的元语言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当然是“美”元语言?那么,“美”元语言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人们对“自然美”的解释。人们多认为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也没有说不通。但是,这是直接在用哲学人类学元语言来解释它。其实,在我们看来,解释它们的最直接的元语言,应该是艺术。比如说社会美,它主要是社会日常产品设计体现了艺术风格——产品制造者的艺术追求,社会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生活之艺术品格的追求;自然美,主要是它被纳入到广义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契合了人类对艺术的规定与追求。在这里,艺术与社会现实生活相对,各自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自有一套元语言解释系统。所谓社会中的美,自然的美,与艺术中的美具有同质的意义,即人们不同程度超越“社会实用”、“世俗物质享受”等之心理或精神追求。①这里的“不同程度”,取“审美三境”之说:“悦目悦耳”、“悦心悦情”、“悦志悦神”。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65-177页。这也就是它们共同的“美元语言”,即“艺术元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是艺术中的范畴 (正如“丑”是艺术中的范畴一样)。简言之,所有美的形态,都在艺术的营构之中。
最后,我们想特别提到的,是中国文艺解释活动中经常出现的“超级元语言”问题。它不同于上文所提的“文化原型”。从理论上说,“文化原型”对种种文化问题的“元语言解释”或者“元意识解释”,不具强制性,最多只有定向意义上的限定性。对于一定社会、一定时代来说,这种“超级元语言”具有基础性,话语霸权性,甚至独断性,它自由出入各种场域。
首先要提的是“意识形态”。从上文对文艺元语言的强调可知,它直接对文艺行使元语言解释,显然是超级越界。超级越界的结果,可能就是对文艺的致命“暴力”。这里存在一个悖谬,它可以把所有文化形态都看成对象语言并对之进行元语言解释,而不允许对它进行解释 (于是成为唯一的“解释项”)。但是,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它本身并不能自我解释,于是,它又必须被某种文化形态作为对象语言来研究。另外,它也不是“基元或原初”意义上的元意识。因此,无论如何,它也不能对文艺直接行使这种意义上的元语言解释功能。如此看来,我们对一种具排他性的主流或核心文化的依赖或习惯,是可以从理论上进行反思的。
除了这种显性“超级元语言”外,还有许多隐性的“超级元语言”。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个人常常被抽象为“大众”或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形成了不少“民族文化”式的“集体元语言”。这种“语言”具有大众性、日常性,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大众日常意识形态”(取M·福柯对其理解的某些意义)。在我们看来,“性格决定命运”就属于这种隐性的“超级元语言”。我们用它解释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也用它来解释“作家人格 (性格)与作家创作关系”这个文艺问题。谈到“作家人格与作家创作”,其首要的解释元语言应该是文艺虚构。文艺虚构可以创造种种“虚拟作者”,他们的虚拟人格具有种种可能性。这样,从理论上说,从作家那里直接寻找其人格与其作品艺术表征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属于界域混乱。一方面,它直接把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人格”等同于其“创作人格”;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现实中人之性格与其社会遭遇的关系直接应用于解释作家“创作人格”与其作品艺术表征之间的关系,即“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性格也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表征”。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追问“性格决定命运”这种“超级元语言”自身的解释元语言。它无非是中国社会现实语境、深层文化结构。原来,国人的人格属于生活环境超常挤压的创伤之果——中国社会现实语境常常强制性地铸造了国人机械、被动顺应社会的性格。而对唯物主义哲学的粗俗理解、中国文化结构特有的“身体化”特性①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5-70页。,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从生理、遗传这些容易看见的现象来浅陋地理解人格。于是,国人性格之现实遭遇与人们的浅陋见识之间的恶性循环,合力塑造了“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这种“民族无意识”(“大众日常意识形态”)。然则,一个社会中居于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这种意识形态被整个社会反向“工具化”,即以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合法面具,使之成为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于是,国人练就了各式各样“皮里阳秋”式的人格——极端“面具化”。这种解读意在强调:中国社会中的“社会解释元语言”既有“受虐狂”,又有“施虐狂”,还有“妄想狂”——它实在喜欢越界;它严重窒息了国人的创造力,也钝化了我们对文艺活动自身的认知。由此来看,强调作家虚拟人格,既是对被苛求的作家的解放,也是文学内在本性的解放。
其实,上文所举的美学分析的例子,就是明显的隐性超级元语言在影响我们的研究。中国文化强调伦理过头,结果除了形成民族某种程度的伪善、面具人格外,更导致整个文化体系建构的“泛伦理化”。也就是说,伦理成为一切文化形态直接的基础元语言。我们可以问的是,善四处出击,美或艺术在哪里呢?过去文艺方面的种种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下去。如此看来,元语言或元意识,对于我们追问一些基本文艺问题,具有直接而基础的价值。说到这里,或许我们还可以作个提示:被我们一直奉为民族思维精髓的“诗性智慧”,或许应该兼收并蓄一点理性与逻辑,其中的混沌与模糊,使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呈现出“酱缸形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