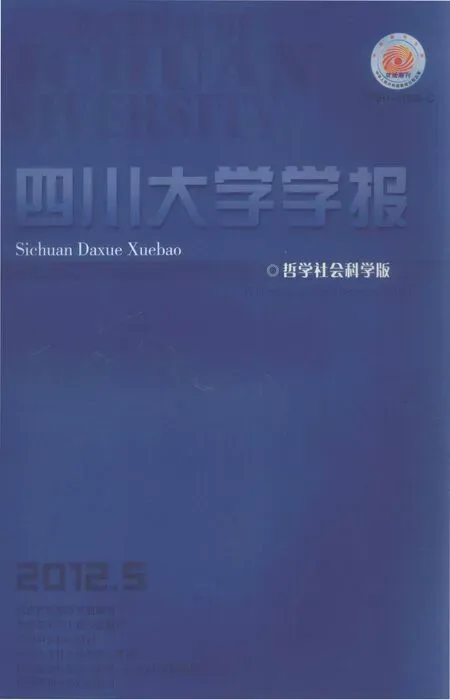老子“法律虚无观”辩析
曹鹏
(成都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长期以来,一论及老子的法律思想,便有不少研究者根据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和他那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名言,断定老子具有“法律虚无观”,“反对一切人定法”,认为“人为的法律制度只会加剧社会危机”。①例如多种《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甚至有的封面标为普通高教的国家级面向21世纪课程规划教材,均持此论。有的说 “(老子)否定法律,认为法律是人制定的,与无为政治相悖离。”有的说老子“反对一切人为制定的法律制度,甚至宣扬‘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修订)》(2007年版)在论及老子时,且以“国家、法律的虚无观”作其中之一小标题。此类论断几乎成为主流学术话语,至今少见应有的反驳。因其明显关涉对老子法律思想的基本评价,所以有必要对此做一辩析。
一、老子反对的是人定的恶法,而非“一切人为制定的法律制度”
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列国统治者私欲膨胀、肆意争夺,因而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时代,是一个诸多君王大臣、谋士们都自诩是爱国治民,而大肆蠢为、乱为,为所欲为,以致扰民、害民、祸国殃民的时代。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失序的现实提出的。他所讲的“无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诸侯君王,针砭以霸道征服天下的当权者的“有为”业绩,严厉抨击其“有为”的虐政。他认为当时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 (即“有为”),所奉行的是一种与“天之道”相违的“人之道”,不是“损有余以奉不足”,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只知满足自己的私欲,无所节制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他这样描绘当时专制剥削者的奢侈淫靡和世道的不公:“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老子》第53章,以下只注章数)朝政腐败已极,当权者无情地榨取,使得田园荒芜,仓库空虚,百姓无衣无食,而统治者却穿着奢华,身佩利剑,厌足美食,财货有余,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使老子忍不住愤怒抨击:“是谓盗夸,非道也哉!”更有甚者,统治者为了开疆拓土,图王称霸,还任意发动战争,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绝。 “师之所到,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30章)这哪里还有黎民们的活路!
而最使老子痛心疾首的是统治者不但如此胡作非为,而且以虚假的仁义道德欺骗人民,以血腥的酷法严刑镇压人民,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正是在这种专横霸道、暗无天日的历史背景下,老子才对当时的“仁义道德”和人定法一概加以否定。他毫不含糊地宣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8章)认为忠孝仁义之类道德规范的出现,都是大道废弃的结果,是社会病态的反映。老子之后的庄子对此说得更为明透:“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这些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统治者欺世盗名,用以愚弄人民,掩饰其罪恶的工具。至于当时的法律,更是旨在欺压和残害百姓,所以老子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统治者依照“人之道”制定的法令越多越彰明,人民就越贫困,盗贼也就越多,甚至法逼民反,使人民走上反抗之路。老子认为,到了这时即使施之以严刑峻法,也已丝毫无济于事,原因在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对于已不怕死的人民,法律的血腥,死亡的威逼,对他们已不起任何作用。否则,“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要是人民真的畏死的话,将其抓来杀了,杀一儆百,谁敢再碰这个刀口?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认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第72章)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一旦人民到了不惧威胁和死亡的地步时,统治者就将处于危险境地,遭遇严重威胁。而随着矛盾激化,力量对比还会彻底逆转,结果则是“柔弱胜刚强”,(第36章)原先弱势的一方必将战胜强势的一方,导致“强梁者不得其死”(第42章)的下场。
总之,对于压迫者的炽烈仇恨,对于灾难深重的人民的真挚同情,以及对于压迫人民、掠夺人民的社会政治制度必然崩溃的深刻信念——这些都是老子社会伦理学说中的主要特点。因之,老子认为统治者基于“人之道”制定的一切“有为”的政治措施和人定法,不但无裨于治,而且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在造成人民被大量屠戮的同时,也一定会加速促进统治者自身的灭亡。
我们知道,法应该被尊崇,甚至应该被信仰。但是,只有法是不够的,还要看法的性质,法的执行,而且要看整个政治状况。有时,许多不公和罪恶,也都是以法的名义加以推行。中外古今,此种实证都不胜枚举。因此,法有良恶之分。战国时的墨子即已明确指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法仪》) “恶法非法”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对法的善恶要进行不懈追问。法律如果丧失了应有的道义使命、价值承担,只是对民众一味剥夺而无保护之意,完全与人民的利益相背离,失去了正常情理的支撑,那么,人们不仅可以不再拘泥于这样的法律,而且有足够的理由抛弃它,废除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老子正是立足于以“天道”叩问“人道”,深刻认识了当时只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维护统治者利益,而对广大平民百姓进行强力的由上而下单向约束管制,甚至屠杀镇压的法律的罪恶本质,才得出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结论。毫无疑义,他否定的只是当时人定的恶法,而绝非持有“法律虚无观”,反对“一切人为制定的法律制度”。章太炎《国故论衡》在谈到《老子》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段话时,就反对“玄家以为老聃无所事法”之说,明确指出,老子的这些话是“明官府征令,不可亟易,非废法也。”并认为:“与众不适者,法令所不能治,治之益甚。”①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见庞石帚、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把《老子》的这番话解读为“明官府征令,不可亟易”,窃以为尚可商榷;但他肯定老子“非废法也”,并且认定违背大众之心的法律不能用以治世,硬要强力推行,效果只会适得其反的看法,却是独具慧眼,十分中肯的。
二、老子的法律思想
正如老子反对当时虚伪的仁义道德,却并不一概反对道德,一部《老子》其所以又名《道德经》,就是明白昭示其极力尊道贵德,自有其系统的道德倡导一样,老子不仅没有“法律虚无观”,并不一概反对所有人定法,而且只要细心研读《老子》全书,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反对诸多恶法,批判当时法律现实的同时,老子对于人定法的建构,也有一系列精辟见解和主张。《老子》以道论法的法律哲学思想异常深厚,是其以“道”为核心的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哲学思想除了包含以上所述内容,至少还可以从中抽绎出有关人定法建制的如下法律见解和主张。
(1)人定法必须在“道”的指导下设计和建制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观点,这已为不少研究者所认同。老子告诉我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道”,先天地而生,以自然为本,为万物之母,它周而复始,常动不息,创生了万物,也内涵着事物的规律性,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则,规制着万事万物的秩序,让万物自然和谐地生长变化。人要效法地,地应效法天,天要效法道,道则效法自然。“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无以正,将恐蹶。”侯王有了道才能使天下安定,没有道,则难免颠覆。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引林希逸注:“一者,道也。”又引严灵峰注:“一者,道之数。‘得一’犹言得道也。”顺带说明,本文对《老子》的解释,多依据陈鼓应先生的《注译》及王蒙先生《老子的帮助》(华夏出版社2009年8月版)二书,择善而从。统治者要想保持自己的统治,必须效法“道”的自然法则,按“道”的精神办事,使人间的秩序顺应自然之道的秩序规律,唯“道”是从,而不能背道而驰。法律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超越这种顺应自然的“道”的规则,理应在道的指导下设计和建制。“道”是立法的依据,也是评判一切人为规则之善恶的准绳。符合“道”的法制,才是良好的法制,才不会伤害天地、自然的本性,带来社会共同体应有的秩序与和谐;违背“天之道”的法律,则只会给人民带来灾殃,加剧社会的危机。
(2)法律及其执行必须公平公正
“道”具有公平公正的特质。老子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与老子一脉相承的庄子也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庄子·大宗师》)这都充分表明了“道”的公正无私。老子还着重指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7章)这就更充分体现了“道”的公平和正义。“道”既是一种高位法、理想法,是人定法的具体导向和终极根据,那么,能为人们所信仰、尊崇的法律必然应是“道”的内涵表现于命令、禁律的结果,必然应具有与“道”相一致的公平公正的资质;否则,便失去了法律的价值,丧失了法律应有的灵魂,成为一种应被否定和唾弃的恶法。
(3)法律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
老子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 (只会利人利物,而不致害人害物)”(第81章)。而且一再强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第39章)富贵者必须以卑贱者为根本,居高者必须以其下为基础。“是以圣人之欲上民,必以下言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66章)“圣人”,在《老子》中屡被提及,均指最能体悟“道”、掌握“道”的有道者,是老子及其道家的最高理想人物。这句话是说,有道的圣人要作为人民的领导,必定要心口一致地对人民谦下;想走在人民前面,成为人民的表率,必定先要把自身置于人民之后,顺随人民的愿望说话、做事。老子甚至还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第 49章)圣人没有自己的私心,而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想百姓之所想,以百姓的利益为利益。所以他提醒统治者必须“少私寡欲”,要懂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第44章)过份贪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过多的私藏必定会招致惨重的败亡。他分析了社会动乱的一个根本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正因为统治者无视人民利益,不顾人民死活,肆意妄为,横征暴敛,对自己奉养无限奢厚,才使得百姓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从而不再畏死,铤而走险。这就说明了,要减少犯罪,获得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重视“以百姓之心为心”,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懂得一切权力的使用以及立法定制、社会管理,都必须重视民意,利人利物,以保护百姓,维护百姓利益为出发点,否则便可能随时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与人民利益相背悖的法律,只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果。
(4)立法应当宽疏,简约,省刑,慎刑
在老子看来,自然的天道就是疏而不密的,宇宙世界似乎并无太多的禁忌,才充满了活力。老子以风箱为喻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之愈出。”(第5章)天地之间就像个羊皮风箱袋,其中看似空虚无物,保留有足够的空间,才源源不断地鼓动出使炉火熊熊的劲风。所以老子既谴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的恶法,也一再指出:“多言数穷”,(第5章)“希言自然”。(第23章)历来注家多以为《老子》所谓的“言”字均指声教法令;②历来注家多以为老子所谓“言”字均指“声教法令”之说,分别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的81页、131页、157页等多处有关注释。“多言”即政令繁苛。“数”与“速”通。多言数穷,即政令繁多,将会加速败亡。“希言自然”则是说少些声教法令,才符合自然之道,民众应有的自然权利才不会受到过多的侵害,法定的义务也不会多得让人难以承受。老子认为: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58章)因而他要求统治者“悠兮其贵言”,(第17章)节制于法令声教,不可轻易地发号施令。在立法定制时,必须“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不可逞强施暴,刑网过密,使人动辄得咎,要做到轻刑、省刑,坚决去除极端的、繁苛的、过度的措施。而只有在淳厚宽疏的法制环境下,百姓才能幸福无忧,重死爱生,敬畏法律,更好地遵纪守法。在此基础上,再对那些违法犯罪者进行打击,才能起到有效的儆戒作用。我以为,这也正是老子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73章)的道理所在。
老子还特别强调了慎刑的原则。他曾满怀仁道悲悯之心指出: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31章)而当不得已而用时,则只须达到制止祸乱的目的就行了,绝不能“乐杀人”,以杀人逞其淫威。老子断言:“夫乐杀人者,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第31章)乐杀人的人只会丧失天道人心,遭到天下人的唾弃。这里的“兵”,当然指的战争;但中国古代兵、刑同义,所谓“大刑用甲兵”即是。故“兵者”如此,刑亦同然,乃不得已而用之,尤其是杀人的死刑,更不能轻易使用,务须慎之又慎。
(5)法律不能只重惩罚,也要重视挽救
老子说:“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第22章)圣人“抱一” (遵守道的原则)以作天下人的范式、榜样,也设置有关规则 (当然包括法律)以治理天下。①“式”:既为范式,榜样,也为规定,规则。《周礼·大宰》记载:掌建“六典”(包括刑典)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的大宰,其“六典”中就有“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九赋敛财富”,“以九式均节财用”等等,显见“法”、“式”、“则”、“赋”,均指规则、法制。而《老子》“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的“式”,我以为即可解读为既作天下人的榜样,又以有关规则治理天下。老子又说: “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27章)善人可以作为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则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镜。不尊贵其师,不珍惜其借镜,聪明人也会变得糊涂。所以圣人善于助人、救人,世上乃没有被冷淡被抛弃的人。善于救物,也就没有被抛弃的废物。圣人治世既是如此,毫无疑义,在其依照“天之道”所制定的人间规则和律法中,也必然贯穿着这种救人救物的博大情怀,对于不善者,哪怕是违法犯罪的人,也会满怀仁心,在对其依法惩治的同时,绝不加以轻贱和鄙弃,而是重视对其教育、诱导、挽救、改造,既以其曾有的不善作为人们的鉴戒,也使之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竭力做到民胞物与,不弃一人,不弃一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三、结 语
对老子的法律思想和法制主张,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更多层面的概括;但仅从以上几点,已可看出老子法律思想的独特和要义,以及对当时的实在法的挑战性、颠覆性,甚而也不乏某些劝诫性。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不无有益的启迪。说他是“法律虚无主义”,断言他“否定一切人定法”,显然失之武断,必须予以辩析,以求对老子的法律思想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知。